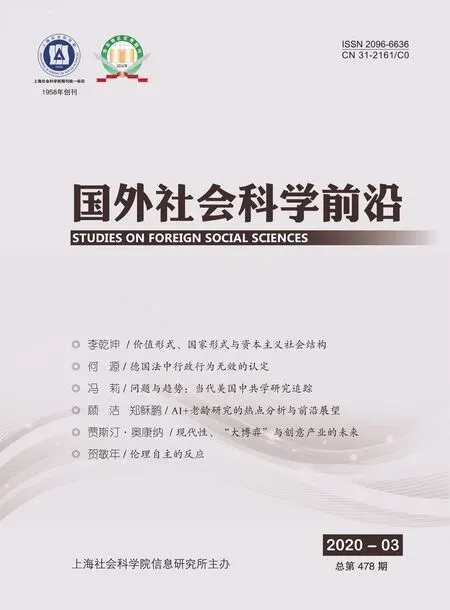伦理自主的反应
——从回返中走出的《于尔根·哈贝马斯》
贺敏年
内容提要 | 斯蒂芬·穆勒-多姆的《于尔根·哈贝马斯》1 [德]斯蒂芬·穆勒-多姆:《于尔根·哈贝马斯》,刘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年。本文正文中括号内标注的数字都是该书中译本的页码,如(1 页)。 力求突破单纯的时间次序与经验叙述,尝试深入生活史内部,重现个体实践与思想活动紧密相连的关键时刻。在此意图下,作者揭示出一种蛰伏于哈贝马斯生命线下的思想轨迹:关于人生的种种直觉激发出对生活的某种共性层面的思考,后者依赖一种源自语言交往的语义能量;同时,基于语言力量的交往行动促使社会生活导向某种广泛的象征化进程,其中潜藏着符号专权的暴力基因;进一步,这种交往压力又反向淬炼着个体人性的伦理品格,并吁求一种自主与依赖的深度平衡。基于上述重构,作者揭示了一种逻辑与伦理之间的深刻摆荡与理性调适,最终促成一种深沉持久的伦理反应。
“钻到肚子里东掘西挖”(618 页),这是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对《于尔根·哈贝马斯》的潜在反应,而在作者斯蒂芬·穆勒-多姆(Stefan Müller-Doohm)眼里,这无疑标志着开放与距离的平衡。从哈贝马斯的自我剖白中不难看出,贯穿这一平衡姿态的深意在于呈现一种埋藏在思想语流中的“生活历史情境”(1 页),这既是个体内在自反的写照,同时也是对交往理解的重新着色。问题在于,如何从这种已成为结果的平衡回返,以便重现思想在生活史中的咬合状态?这正是作者直面的难题。坚韧与脆弱合力在开放和距离之间筑起一道缓冲带,借此促成平衡的最终成形,但是否可以完全将这种缓冲作用归结于个体秉性或思想品格?作者指出,这里潜藏着一种“真实性”诱惑,即可以在一种时间次序的连缀中兼顾记叙的可信与周全。这是一种偏离“类伦理”(359 页)的智性幻觉。就塑造“人生唯一性与独特性的那个个体”而言,编制“一个非同寻常的励志故事”的诱惑近在眼前,而这将错过“那个个体”的真正力度。(2 页)对哈贝马斯而言,成就个体的恰恰在于“那个”,后者乃是生活、互动与交往的实践情境,而个体的实践本性则根植于某种深沉持久的理性调适,一种旨在平衡思想与行动、事实与规范、结构与关系的内在反应。潜藏在时间次序之下的,即是这种不断耦合又不停跃迁的反应秩序。因此,重点在于“描述行动,其次才是行动者”(3 页)。就此而言,《于尔根·哈贝马斯》无疑是对哈贝马斯哲学行动的一次文本反应。
一、直觉:“重要性”的崛起
纵观哈贝马斯生命线的铺陈与走向,很难捕捉到诸如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马 丁·海 德 格 尔(Martin Heidegger)、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托马斯·曼(Thomas Mann)、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君特·格拉斯(Günter Gaus)等这些同时代人身上那种清晰可辨的断裂或转折,他毋宁正在践行一个欧洲知识分子平缓而奔碌的命途。但是,一俟聚焦于掩盖在时间线下的种种横断面,就会发现在那些局部生活的褶皱里潜藏着大大小小的事件,它们在哲人独特的反应中被编织成一幅幅生动的剪影,而穆勒-多姆则以极佳的节奏使这些剪影悉数登场。于是,一部生活史的“风景画册”跃然成形。
诚然,事件是检测反应的试剂,灾变则是事件的极致。年轻的哈贝马斯需要面对个体生理与社会政治的双重灾变,二者在典型的“二九一代”(29 页)身上以某种特殊的形式相互缠绕。在此,作者有意规避或弱化了个体在灾难中的具体面相,无论是对自身语言缺陷的原初反应,还是与21 世纪欧洲灾难史上最黑暗一页的照面,真正重要的并不是个体当下一刻的应对行动,而是在一种迟滞与纠葛的反应中所迸发出的思想声纳。思想根植于生活史,而触发这一埋藏在生活土壤中的思想炸药的引信,就是直觉。这正是作者淡化个体经历的深层意图:对于哲学家尽人皆知的经历予以破土翻新的娱记式描画,无疑将在最大程度上错过那些直觉闪耀的时刻。这些直觉时刻都是智性成长不可或缺的养分,也是“生活经验和思想生成之间的铰链”,哈贝马斯甚至明言直觉是其思想的“坚硬内核”,它让“内心的声音萌发,形成思想”。(468 页)
表面的迥异根植于深度的依赖,这是哈贝马斯面对人生的首个直觉。在此,穆勒-多姆以近乎直白的方式给出了一个重要暗示:对于哈贝马斯,这种依赖不同于施莱尔马赫式那种以无可测度的方式流转于人生伦常的神秘依赖,它并不导向某种宗教超越,而是激发了对这种依赖根植其中的某种共性层面的思考。依赖依附于环境。在那些得以鉴识哈贝马斯思想特征的概念坐标中,无不隐含着这一环境依赖的基调:“理性”、“交往”、“对话”、“政治介入”、“公共领域”、“主体间性”、“欧洲”、“习俗”、“规范”等等。无论有意与否,穆勒-多姆都触发了一个解读哈贝马斯的重要符码:即不管主题与视野何等辽阔,哈贝马斯始终是一个局部思考者。习俗与宗教之间晦暗而固执的隔阂,在他那里已悄然转化为一种在开放与距离、自治与依赖之间寻求平衡的拯救与解放。思想一经启动,他便早已跨过马尔皮萨的鹅卵石。
对于共性的思考触发了另一个重要直觉,即“语言交往媒介作为共性的表层的重要性”,以及立足其上的“与他人交往的重要性”。(23 页)这一点在对政治灾难的反应中显露无遗。回望历史,罪责问题在战后十余年陷入某种奇特的怪圈:一方面,诚如纽伦堡审判所展示的,政治灾难的参与执行者通过强调个体行动与国家责任的脐带关系来进行自辩,审判纳粹战犯即是审判整个德国民众;另一方面,诚如托马斯·曼与雅斯贝斯所强调的,作为一个历史整体的德国理应肩负起一种“集体责任”,在战争反思问题上,区分纳粹分子与德国人民是“匪夷所思”的,即使参与主体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宣传与恐怖的受害者。这种反思失衡导致了两个截然相反的后果:战前成熟一代对灾难历史达成某种“交际性沉默”,而享有“晚生恩典”的年轻一代则在分寸感与敏感度的缓冲作用下背负起了一种“必须干预”的道德直觉。(28 页)哈贝马斯痛苦地看到,奥斯维辛的硝烟令自身历史中“所有最重要的方面不复原样”。面对罪恶遗留的阴霾,必须打破沉默,解剖历史,并在民主论辩的试剂中检测政治行动的合理性。当恐惧与忿懑落幕之际,“重要性”再度崛起。
二、语言:语义能量的补给
灾难是直觉的诱因,直觉是存在的闪现。某种意义上,任何直觉都依赖一个产生它的原点。对于哈贝马斯,这个原点究竟是什么?穆勒-多姆意识到,环境依赖与交往介入均付诸一种广泛的语言实践,“直觉不是真理”,为了能“长久存在下去,直觉必须被不断翻译成主体间相互可理解的理由”。(469 页)这种源自语言的巩固力正是哈贝马斯的直觉原点,他从中觉察到一种非强制的规定性在日常社会交往中促成某种“非强制性的共同意志”。人际间的规范性约束,“只能产生自以相互理解为取向并通向共识的言说,其中,一种言语行为的可接受性基于其内在的理性要求”。(180 页)他由此强调理性与语言的原始关联,这点使他一开始就与正统批判理论保持距离;不同于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将理性锚定在一种爱欲本能,哈贝马斯始终坚持“理性仅凭借语言而存在”。
但是,语言非强制的规定性究竟何以可能?作者为此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将语言规范性的建立与哈贝马斯的历史逻辑观紧密相连。对哈贝马斯而言,人类物种史与个体史之间存在某种结构同源性,在进化与发生之下掩埋着一种在“可合理重建的、越来越全面的结构层级”中的学习进程,后者在一种相互作用的社会环境中同时向事实与意识渗透。因此,学习构成了人类独特的规范基因,学习过程即是“一个自我生成的过程”。更重要的是,个体通过“适应他的生活世界的符号结构来学习”,在此过程中,“语言起着核心作用”。(205 页)个体通过语言交往存续自身,因此,语言的有效性就拥有一种普遍性,一种“先验的条件约束性”。穆勒-多姆的这一重构对于理解个体与社会、历史与逻辑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正是对语言交往之决定性力量的强调,促使哈贝马斯溢出经典马克思式劳动发展动力观,进而发展出一种建构性的社会动力论,即通过对个体学习潜能的吸收和制度化来调控和优化社会系统的层级结构。因此,“个体发生的学习进程就优先于社会进化的推动,社会只是在象征意义上学习,因为社会学习取决于社会成员的学习”。(205 页)
显然,对哈贝马斯来说,基于语言交往实践的学习过程将同时确保自我意识与社会团结,同时,学习的建构与创造力亦包含社会批判的关键符码。他指出,在历史的灾变中孕育着一种“提高觉悟的批判”,促使人们直面并参与具体社会政治事件,从而揭示“暴力侵入社会制度的程度”。但是,一当暴力被克服,“实践对话的结构就必定会萎缩”,因此,就需要一种本雅明式的、葆有一种“生命获得解放远景”的“拯救性批判”所提供的“语义能量的补给”。(193 页)自此,基于语言效能的学习与批判便构成交往实践的双闸,它们高擎理性,合力铸就良善生活的荣光。
在宽泛意义上,哈贝马斯对于语言效能的这种反应折射出19 世纪末便已有的一个共识:社会批判立足于一种语言批判。他始终坚持如下信念,语义的规范能量将在交往互动中转化为一种道义伦理,这是一种非强制的论辩力量。对于这一乐观愿景,穆勒-多姆未置可否,但他耐人寻味地引用了伊娃·黑瑟(Eva Hesse)对哈贝马斯“结构历史主义”的评论:历史是“一条魔鬼用破碎价值所铺设的迷人大道”。(206 页)这点似乎暗示着,交往行动借以穿透社会坚硬壁垒的语词光芒背后,总已蛰伏着某种深嵌在语言肌理的晦暗阴影。换言之,是否存在某种永久溢出语言批判的语言要素?
这是任何一个局部思考者必然遭遇的困境。为此,穆勒-多姆直至尾声才语焉不详地勾画了寥寥数笔,仿佛年迈的哈贝马斯在交往巨轮的残辙中喃喃自吟:“话语概念中保存着某种‘无条件的要素’,某种‘批判难以捕捉的绝对性’。”(469 页)这点关涉到一个始终缠绕在哈贝马斯智性生涯中的直觉:乐观的底色往往是沉郁的。这一直觉的原点即是潜存在这一绝对因素中的隐性压迫。话语实践的“有效性要求”试图通过承诺这种无条件的绝对因素,来获得关于社会结构与功能的直接说明。然而,这里实际上仅触及社会关系一个交往化的局部面相,它忽视了社会关系的流动性、自反性,以及虚拟性之间的复杂联动。诚如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质疑的,基于语言的“非强制性交往”概念“完全忽视了作为潜在因素内在于所有交往中的强制形式”。(351 页)质言之,在话语实践的规范界面上,对于社会关系只能提供一种间接说明,这无疑要求一种新的“语义能量的补给”。
三、暴力:主体的空白
“曾从里面爬出这个东西的子宫,依然能生养”(40 页),无论哈贝马斯是否读到过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这句台词,它都恰切地描画了晚生一代对黑暗暴力的集体感受。事实上,对政治暴力的敏感贯穿哈贝马斯整个生涯,穆勒-多姆为此不惜笔墨地通过或大或小的事件来重现哲学家对暴力的反应,并且着力展示出一个不断反抗的形象。在他笔下,直觉与语言在这种依稀可辨的抗争姿态中同时指向了暴力。如果说,产生直觉的种种原点本身就依附于一种从暴力阴影中的“否定的退却”,那么基于语言的理性交往就是一种直面暴力的“肯定的开启”。问题在于,除却揭示和批判的道义分量,在侦测潜伏在社会肌理的种种暴力基因时,哈贝马斯所释放出的思想能量是否足够坚实?
诚如作者所言,对暴力的敏感将哈贝马斯引向了哲学,并且决定性地影响了他和哲学的关系。其策略是在一种哲学史考察中揭示暴力权威性的哲学根源,首要任务是对“主体—意识”哲学传统的批判。其中关涉到两个重要人物:弗里德里希·谢林(Friedrich Schelling)和海德格尔。哈贝马斯在二者思想中发现了某种相似的轨迹,在克服主体—意识哲学的过程中又重陷其中。无论是自我同一性,还是存在历史性,最终都归因于一个“自身无根的非历史性的原初基底”。(53 页)这里潜伏着一种形而上学的理性狡计,理性的客观性依赖于某种前(非)理性的奠基,并且在主体—意识哲学话语中被转译为一种先验的主体客观性。哈贝马斯指出,正是这种主体客观性构成了某种“精神专权”,而政治暴力则是这一专权的社会投影。在他看来,若要解除狡计、挣脱暴力,就需寄望于一种基于“普遍—形式语用学”的“后形而上学”的思想力量。
宽泛而言,普遍—形式语用学是一个旨在为那种前理性的先验基底提供替代方案的解释系统,力图阐明以相互理解为取向的行动的一般性条件,其策略是将理解导向的言语行为与一种基于有效性要求的规范基础相耦合。于是,在此语用学视域下,先验实在的优先性就被一种行动能力及其完成时结构的有效性取代,这是一种后形而上学的奠基。实在(世界)依赖语言,“没有任何一条通向实在之路不以语言为媒介”,主体只能在语言中行动,并且“只能借助语言的理性形式建构世界”。(182 页)因此,主体性就在主体间的相互作用中转化为一种主体间性,“消失的先验主体并未留下空白”。(408 页)进一步,在替而代之的语言实践中发生了某种“精神位移”,这并非某种主客观之间基于“辩证可塑性”的摆荡,而是一种内在于精神自身的概念重构。穆勒-多姆指出,后形而上学立足于如下假定:精神是受规范调节的“主体之间的状态”,人的精神状态根植于主体间通过语言理性交往所达成的“三界”(180~181 页)协调。因此,精神并不是一种滋生暴力专权的主体环境,而是主体实现“内在超越”、形成相互承认与团结共识的道义动能。简言之,主体间性是精神性的。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穆勒-多姆所解析出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观念。
主体间性根植于精神,而精神又是基于“更佳论据的非强制的强制”的符号化交往中所达成的合理协调。由此,所谓主体间性以及立足其上的生活世界就是这种符号化的“理由空间”的象征性体现,它们臣服于一种逻各斯的规范性。于是,伴随精神的位移,主体性的精神专权便让渡于一种象征性的符号统治、一种行动者一旦据其社会身份进入交往游戏就必然要承受的“符号暴力”。语言自身就是一种统治形式,哈贝马斯对此是否有明确诊断不得而知,但是穆勒-多姆确乎捕捉到了一种隐秘的腾挪:对哈贝马斯来说,一种符号化的象征机制恰恰是抑制物质暴力的条件,面对可能发生的直接的现实暴力,他主张用一种“象征化的挑衅”替而代之。(168 页)但是,恰恰在符号统治的种种象征化运作中,社会成员往往会基于某些相同的诉求从而达成表面共识,其实质是一种旨在巩固交往利益的“误识”,后者实际上是对符号统治系统自身的一种强化和圣化,其后果则是符号暴力的不断增殖。就此而言,描述暴力本身即是暴力权威的来源,而描述这点本身又将触发新的暴力,此即符号暴力的动力内核。
承认基于承受,共识有赖误识。无论有意与否,这种吊诡在哈贝马斯的资本主义批判及其危机理论中获得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转喻。对哈贝马斯而言,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在于,国家主义与经济主义合力造成的社会秩序的失衡,即“生活世界的媒介化”与技术系统的物化扩张。其中,货币关系支配着社会世界,从而导致了日常生活的虚无和分裂。因此,危机的实质是一种“合法性危机”。(386~387 页)哈贝马斯由此强调一种民主合法性规范的“政治优先性”,力图阐明这些规范在社会实践中能够有效制约权力经济和政治支配的形成。但是,“只要我们进行言语行为,就处在一种固有力量的命令之下”(239 页),因此基于对话实践规范的民主政治同样无法挣脱那种象征化的符号统治。事实上,这种符号统治很大程度上构成社会实践的动能。诚如布尔迪厄所揭示的,资本在种种误识机制中逐渐突破狭义的经济范畴,在政治、社会与文化场域中转化为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符号资本”。由此,包括狭义经济关系在内的多元社会结构均需在一种符号化的实践逻辑中才能得到理解。根本而言,人们无法挣脱这一潜存于所有交往形式中的符号统治。正是这种压力促使哈贝马斯承认,“逃脱资本主义宇宙已无可能”,而平定和缓的“交往理性”到头来不过是一股担负抗争责任的“复仇的力量”。(391 页)历史的灾变本身就是一场硝烟密布的战争,那些硝烟即是从灾变的温床上蒸腾而起的种种符号暴力。填补主体空白的,从来就不是语词的温柔。
四、人性:伦理自主的罗盘
符号浪潮的普遍统辖是否意味着一幅人类未来史的黯淡图景?哈贝马斯看到,现代资本社会的发展表明,符号化的实践经济逻辑在社会关系中植入了一种象征化的真实性,借此在生活实践中塑造一种趋向未来的“生活形式的整体性”。(418 页)那么,这一符号逻辑指引下的整体导向性与交往理性规范下的行动凝聚力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同源性?对于哈贝马斯,绝无可能将交往行动还原为纯然的符号增殖与叠加,他抱定如下信念,一种基于“历史—逻辑”统一性的生活实践所蕴含的整体规范将为社会生活的趋向性与个体行动的自主性提供重要的平衡。在穆勒-多姆笔下,这一信念几乎贯穿于哈贝马斯的政治批判、国家理论、民族主张,乃至宗教辩护。问题在于,信念的依据究竟何在?
对此,作者指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线索,即生活实践的规范性根植于一种个体人性的生命伦理。哈贝马斯认识到,符号化与言语行为之间并非构成单纯的转化关系。某种程度上,屈从于更佳论据的非强性力量的对话实践依赖于一种溢出对话视阈的象征呈现,后者构成了一个越过理由空间从而“延伸到意义沉淀物外围”(362 页)的意义空间。简言之,存在一种符号化同时又是非对话的象征交往形式,并非一切皆对话,而对话始终只是“实践之海中的一座岛屿”(286 页)。正是基于此,哈贝马斯才在社会关系中洞察到一种依赖于个体发生和认同的象征性的学习机制。他由此将个体化和自主性的建立与一种源于社会化过程的理性认同的规范性紧密相连。
哈贝马斯强调,符号化是一个构造自然基质的过程,而人作为一种符号构造体,始终都是个体的外在自然。囿于交往理性与对话伦理的“非强制的强制性”,哈贝马斯侧重于蕴含在符号化中的互动潜能,基于此,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将一种互动角色感的价值取向内在化。因此,个体化和自主性就体现为一种语言、认知与角色的交叠特征。作为一种“符号的自我组织”,个体化是在一个内在自然与外在自然相互界定的系统中发生的。其中,内在自然在融入交往结构的过程中学习“自反性地理解自我,从而形成自我认同;自我同时学习保持自我统一性,即符合人格跨时空的一致性要求”(436 页)。个体化源于对话式交互关系,而认同表现为一种“自我负责的人生经历的连续性”,“只有接受自己生活史的人,才能直面自己经历中的认同形式”(439 页)。因此,个体化与自主性依赖一种人际承认的道义尊严。正是在这种基于交往互动的自我理解中,自然存在物逐渐成为个体和被赋予了理性的人。人必须成为自身,这既是一种“类伦理的诫命”,也是技术时代人性之不可支配性的根源。
更进一步,在个体的反思与互动中,亦蕴含着意志自由的合理化证成。哈贝马斯指出,意志自由是“意志基于合理理由的自我关联方式”;作为一种存在方式,意志自由始终是一种有条件的自由,取决于具有象征结构的强制性理由空间。基于此,哈贝马斯为“自由—决定论”这一古老的二律背反提供了新的理解,自由同时受制于个体人性与社会生活,二者在理由及其交互作用所构成的“逻辑空间”中耦合为一种成熟的理性自主。穆勒-多姆在此觉察到哈贝马斯自由概念的某种激进性,自由根植于共同体的交往结构,后者确保了一种内在的制衡,“若非所有人都享有自由,个体不可能真正自由;若非所有人都享有同等的自由,所有人都不可能真正自由。”(257 页)
正是在此自由镜像中,作者暗示出一种重新读解那道哈贝马斯致命符咒的可能,即根植于语言深处的那种“无条件的绝对性”。在一种自然主义的符号化还原中,这种绝对性打破一切深藏于理性的脆弱平衡,肆任权力蔓延至主体失语的空白,最终在种种符号暴力的淬炼中将自身巩固为一种统治程序。然而,正是在此惨淡的匍伏中,酝酿着一种人性深处“最后的勇敢”(179 页),它教导人们,唯有脆弱的交往才能抵御普遍的脆弱。借此人性的道义光照,哈贝马斯展示了一种蛰伏在理性涓流下的内敛与绽出,一种烙刻在心性基石上的回返与走出,它们共同促成了一种深沉持久的伦理反应。毫无疑问,在穆勒-多姆眼里,这同样也是鉴识哈贝马斯精神飞翔的轨迹。借此伦理罗盘的指引,他穿越种种形色仓皇的激流,倾力捕捉那“生活在沉重与危险中的令人动容的气息”(37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