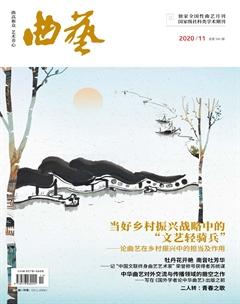曲艺助力乡村振兴 不妨用好互联网
夕君
乡村振兴是国家战略、时代主题,在其丰富的内涵里和实施的过程中,文艺占有重要的位置。文艺对于乡村振兴的功能价值,简单说,一是给予,二是激活。
所谓“给予”,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基层文艺演出。文艺有润物细无声、以文化“化”人的作用,而曲艺是“文艺轻骑兵”,其形式灵活多样,内容轻快幽默,对社会上的事件、国家的方针政策,能够快速及时地反映,并通过带有自身特色的艺术作品进行传播普及。据笔者观察,乡村、农民对于文艺有迫切需求,戏曲(尤其是小戏、名段)、歌曲、曲艺(尤其是短平快、通俗易懂、风趣幽默的作品),最能演到农民的心里。历史上,用曲艺作品宣传新政策、新思想的成功案例,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在信息传播相对来说不如城市便捷的乡村,承载着新知识、新思路、新理念的曲艺作品,大有用武之地,农民顺利地接受了节目,节目传达的理念或精神才有发挥作用的空间。不妨联想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谈及报纸作用时的论述,他认为,报纸实现了不同地区的读者知晓、关注同样事件的“共时性”,由此形成凝聚力、参与感与认同感,报纸对19世纪民族国家兴起、公民意识形成起到关键作用。文艺尤其是曲艺之于乡村振兴,承担的是类似的使命,在社会发展快、变化快的当下,尤其如此。
很多年来,向乡村输送文化已经发生由“送”到“种”的变化。同理,文艺之于乡村,给予是初级阶段,关键在于激活。所谓“激活”,不仅是在乡村培育文艺爱好者、曲艺爱好者,为当下和未来培养观众、积累观众,形成文艺、曲艺发展所必须依赖的“群众基础”;而且在于通过文艺作品、曲艺演出提升乡村的文化品位和农民的素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体和主力军是农民,农民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效果,用经过文化武装的头脑和眼光重新看待乡村,其民俗资源、文化资源、旅游资源、产业资源等,可能都会焕发不同的光彩,对风俗习惯、人际关系等问题的看法与处理也会不同。以文艺、文化在乡村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诚实守信的市场环境和淳朴友爱的人文环境,是让乡村以及所有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切实受益的——这就是激活。所谓扶贫在于扶“志”与扶“智”,就是类似的意思与诉求。
当然,文艺、曲艺与乡村的关系并不是单向度的,乡村基层鲜活的人物、故事,面对面为老乡演出的经历等,对文艺创作、丰富演员的舞台经验来说,非常有益。有关部委提出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等倡议号召,也都是希望文艺能够从乡村、从基层获得灵感、获得滋养。
实际上,基层演出、送艺下乡等,都已经坚持实践了许多年,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文艺尤其是曲艺对于乡村振兴的功能价值,已经在实践中被证明、被检验。只不过,文艺、文化对一片土地和那里的人们产生影响和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长期、反复、高频率的输出与熏陶。以全国乡村的数量来看,要想实现长期、高频率覆盖并不容易。因此,文艺的功能、曲艺的价值如何巧妙地落地、实现,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互联网是一个值得重视和思考的渠道。
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已经给艺术的创作、传播带来非常大的改变,尤其是当5G逐渐铺开,移动互联网还将进一步释放潜力。疫情期间,线下演出停摆,互联网的作用被又一次强调和凸显。目前,有的乡村可能交通还不便利、道路还不宽阔,更没有像样的剧场、舞台,但是只要有网络,这里就能与外界发生密切的联系。据笔者了解,网络直播、短视频,譬如“某手”“某音”等,就深受基层群众尤其是年轻人的欢迎。
那么,广受欢迎的短视频等网络平台,是否能为推广普及曲艺所用呢?是否能为曲艺助力乡村振兴所用呢?
互联网平台的便捷、强大,是显而易见的,但其碎片化、快餐化、去深度化的倾向,同样是显而易见的。就拿相声来说,铺平垫稳、三番四抖,讲述故事、塑造人物,体现的是语言、逻辑、艺术的智慧与魅力。然而,在短视频平台上,显然不具备铺平垫稳、三番四抖的条件,在极为有限的时间内,几乎所有包袱都是“直给”,包袱皮薄,甚至根本没有包袱,仅仅是以出洋相、出怪态的方式博人一笑,这其中已经没有什么艺术价值可言。这种娱乐、搞笑的方式对专业的从业者、研究者来说,必定难以接受。
然而,从传播的角度,从曲艺助力乡村振兴,乃至在更广阔的空间内发挥文艺、曲艺的作用的角度,曲艺与互联网的关系,可能还是需要慎重考量,适当加以利用。
仍以相声为例,历史上看,从撂地到园子,从园子到广播、电视,相声的内容、结构、形式都发生着变化,演出的场域、媒介必然会对创作、演法等产生影响。今天的短视频平台与过去的广播、电视同理,不过是一种新的媒介,这种媒介可能不适合演传统作品,那么,具有与时俱进能力的相声,能否根据新媒介的特点和要求,创作相應的作品,或者对已有作品做以调整呢?从传递价值、理念的角度,作品时长未必是最关键的因素,况且,以短小精悍的作品吸引住观众,把曲艺先送进广大乡村,再逐步将乡村受众领进大门,登堂入室,欣赏长作品、传统作品,也不失为一个办法。没有人会认为,短视频平台能够打造艺术家,能够成为艺术的主流平台,艺术的生命仍是在舞台、在剧场,舞台、剧场的价值不可能被短视频平台取代,二者的关系是互为补充,而非“你死我活”,大可不必用对立的眼光看待。短视频平台仅仅是一种手段——一种如今看来十分必要的手段。
之所以说短视频平台是曲艺助力乡村、曲艺走向更广阔天地的必要手段,是基于对技术发展、技术价值的观照和判断。通常来说,普通观众对艺术作品的接受并不是那么理性的,他们通常不会细致分析作品的立意、主题、结构,不过是觉得有趣或者看得多了,作品及其承载的知识和价值,也就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毕竟,互联网、短视频平台,都只是一种工具和媒介,人对工具和媒介的要求一般总是越来越便利、越来越不受时间空间限制,且工具与媒介形成的路径依赖既具有一定的代际特点,又具有相当的“破圈”能力,很多年纪稍长的人士,也对短视频等新生事物很感兴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尤其是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正常现象,并且是不可逆的。试想,当简化字通行多年,谁愿意改为书写金文、小篆呢?并且,工具及媒介的迭代,不能也不必做道德评判,曲艺拥抱新技术,不必有什么负担,工具不是任何人天然的朋友或敌人,关键在于怎么用。互联网这种工具和媒介已经拥有了非凡的传播力和覆盖面,正能量不去利用,就可能被负能量利用,曲艺艺术如果不利用新兴工具对接乡村文化,那么其他内容就有可能“乘虚而入”。
不过,据了解,目前已有的曲艺“上网”的尝试,并不是都能取得理想的效果,所谓“云端曲艺”有些比较冷清。这令笔者想起此前对“云端戏曲”的探讨,二者或有共通之处。当人们提出“云端某某”效果不好这一命题,其逻辑前提似乎预判了,问题出在“云端”。事实上,某些艺术形式的线下演出,效果也不一定好,观众也不一定多,这其中的关键问题并不在于云端,而在于创作本身。不妨自问:作品是不是具有文学性、艺术性;或者说,作品在着眼于重大主题、教化功能的同时,是不是做到了好听、好看。眼下的问题是,艺术创作常常对思想内容、社会价值强调充分,而对艺术表现、审美趣味却轻轻放下了,殊不知,如果没有后者之精湛,前者的价值也将被遮蔽,作品价值的实现、艺术表演的完成必须在观演关系中实现,而不可能是单方面的一厢情愿,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
曲艺深度拥抱互联网,可能会带来对一个理论问题、本体性问题的追问,即什么是曲艺。任何艺术形式都会因为传播媒介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但同时,任何艺术形式也都有自己的本体属性,一旦突破乃至颠覆了这个本体属性,该艺术形式也就发生了质变——变成了其他东西,甚至不复存在。因此,在曲艺“上网”,通过互联网通向乡村、通向更广泛的受众的过程中,哪些方面需要适应新媒体的生产和传播规律,哪些方面需要坚守艺术的本体与价值,坚守与适应的尺度、界线、临界点在哪里,是一个需要在实践过程中长期关注和探讨的课题。
实际上,互联网不仅是曲艺走进乡村、走进更广阔的天地的渠道,互联网及相关的事物、人,也可以成为创作的素材,比如直播、网红、网友“奔现”等话题,都有笑料和值得思考、批判的东西可以提炼。过去,我们觉得互联网是虚拟世界,而现在,它早已成为现实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有谁离得开微信呢?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微信绑定了人们大部分甚至全部社会关系,互联网已经深入地参与了人们的生活。因此,文艺创作体验生活应该包含“上网”这个环节。曲艺和互联网的关系,与曲艺和乡村的关系一样,应该是双向度的。在曲艺助力乡村建设的过程中,不妨用好互联网。
(责任编辑/邓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