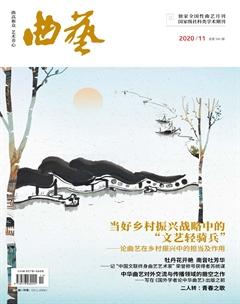关于苏州评话“唐三国”创造学的随感
众家说演法
《唐耿良说演本长篇苏州评话〈三国〉》问世。7 年时光悠悠而去,苏州评话“唐三国”纸上定格。2019 年年初以来,在唐力行教授的用心指导下,我走上了一程悉心品赏苏州评话“500+7”的难忘之路。500 天中,我始终相伴着“唐三国”100 回评点、150 万字苏州方言文本整理。在100 回书目的7 轮多反复聆听、欣赏、景仰的过程中,我肺腑热腔。
长篇苏州评话《三国》说金戈铁马、家国情怀,说英雄人杰、文化乡愁。《唐耿良说演本长篇苏州评话〈三国〉》以其巨著的质量、非遗的传世、经典的内容,铭刻下苏州评话《三国》的优秀人文遗存,推抬出唐耿良苏州评话体系的审美艺术化石。立足400 年苏州评话艺术共同体,来观照苏州评话说演手法系统,有以下几类:曹汉昌的《岳传》深植于传统领域的一丝不苟,老派到位;金声伯的《包公》走向了时代精神的巧口洗炼、精准细微;张鸿声的《英烈》启迪自海派风格的书路开放、贴近听众;吴子安的《说唐》细致在故事叙述,书艺提高;唐耿良的《三国》(习称“唐三国”)浸透着人文气质的显露性情、心理细致等等说演手法。
读《唐耿良说演本长篇苏州评话〈三国〉》,读法显然要有别于《三国演义》。读“唐三国”文本,在泛读、通读的基础上,再下足细读、精读的工夫,才能透读、深读这部民间草根巨著。经苏州评话艺术家迭代积淀而致、由唐耿良总结升华而成的既富苏州评话艺术特色,又突出了唐耿良个人风格的说演手法,我们在此不妨将其归结为——广识“熟悉的老熟人”,特致“熟悉的陌生人”之法。“唐三国”主要人物谱系,除了刘备、关羽、曹操、周瑜、鲁肃、黄盖都是我们广为悉识的“熟悉的老熟人”,诸葛亮、张飞、赵云同时被改造为一般鉴赏经验之外,让人感觉面目一新、富有情趣的“熟悉的陌生人”。
唐力行“三问”
唐耿良12岁拜师学书,13岁“小矮凳说书”①,86年来,随着苏州评话艺术跨越着历史,以当代中国社会正在不断加大的文化自信力度、切实重视非遗文化建设的现代化理念来回眸“唐三国”原生态的本土艺术追求,那么,唐耿良是一个从“說书小道童”成长为保护江南文化乡愁“种气”的先行者。
唐耿良长篇苏州评话“三国”艺术特质完全恰合于唐力行苏州评弹研究“三问”理论(唐力行《关于苏州评弹三个终极问题的理论探索》,见《苏州评话弹词史补编》一书),“唐三国”与“唐力行三问”已经从艺术实践和理论研究双重层面,为苏州评弹非遗文化基础建设奠定了不可移挪的重要地位。唐力行“三问”提出了3个问题,即:苏州评弹是什么,苏州评弹从哪里来,苏州评弹到哪里去。
首先,《唐耿良说演本长篇苏州评话〈三国〉》是什么?它是苏州评话艺术的经典、非遗文化的标杆,它说噱谈评综、语味趣细奇、灵情深广正,而其中,说、噱、谈、评、综所蕴涵的文化美学意义,在今天来看显得特别重要,它不啻为苏州评弹非遗文化试金石,同时它也在为苏州评话艺术审美本体特征做出“说噱谈评综”的最新概括,提供了文艺社会学依据和美学思想原型。其次,《唐耿良说演本长篇苏州评话〈三国〉》从哪里来?它从江南文化钟灵毓秀深处而来,它从苏州评话艺术深厚的积淀而来,它从唐耿良一生创造学深入而来。《唐耿良说演本长篇苏州评话〈三国〉》到哪里去?它已经成为“大家”而自立于中国说书共同体的优秀之林,它还在贡献“自家”而顾答着苏州评话新时代的涅槃召唤,它应该回归“娘家”,走到基层群众喜闻乐见的书场里去。
广义创造学
纵横家国的题材,通俗史诗的寥廓,性情挥洒的乡愁,把根留住的创造。一部“唐三国”,狭义上,它是苏州评话艺术传世作品的经典,广义上,它是非遗文化创造工作的基础建设。说“唐三国”书情,读“唐三国”文本,听“唐三国”演绎,最基本的艺术审美共鸣点就是生活意蕴的广益、文化乡愁的真谛。唐耿良所献身的苏州评话艺术非遗文化基础建设,就是为生活原生态的反映提升,就是对乡愁体温计的观察记录。他是研究基于传统的创造学的后辈们的榜样。
哲学与科学,标识“唐三国”的艺术境界。《马跃檀溪》一书中,刘备走投无路,水镜先生司马徽“贴心细无声”,烘托了民间草根的哲学智慧。此时此刻的刘备,最需要会战略设计的向导和懂政治博弈的领航。因为经过水镜庄夜的沉默,刘备政治战略的意识被民间哲学思想唤觉出来,通过司马徽“拖”的哲学,刘备从零开始的干劲被草根智慧重新鼓动起来。诸葛亮《草船借箭》,达到“唐三国”科学文化存在形态的智慧高点,因为诸葛亮的“神仙”高蹈内有着同侪旁人所不及的科学思维。夫唱妇随,无独有偶,诸葛亮夫人黄氏也是一位古代科学女性。
文学和美学,点睛“唐三国”的艺术创作。同样是在《马跃檀溪》这一回书,刘备文心萌起,田园的图景、唯美的诗心,点睛了“唐三国”含而不露、节制有度的文学气韵,照亮了“唐三国”藏而不举、微以显著的美学创境。《三顾茅庐》一书,刘备心境似水、思绪如腾,正是卧龙岗山村美景的疏朗萧散,才将中国传统文化中景语即情语、美境即美心、人情即人格的高超境界,悄无声息地播扬在“唐三国”的精彩书情与审美天地中。《横槊赋诗》中,曹操的文学走到前台,巧妙的是,“唐三国”中,曹操经历的最大悲剧“火烧赤壁”却是由他著名的诗歌《短歌行》吹了哨。《王德报信》中,英杰赵云与平民王德有了交集,王德悲惨难逃而又善良之极,该回展现出了王德的恐惧心态但崇高的人格,我们很少能见到美学是这样在苏州评话共同体呈现的,我们很难想到文学是这样在苏州评话共同体中升华的,我们很难知道创造学何时才能像“唐三国”这样,艺术价值恒久地在苏州评话共同体中得以新生。
语言学,文献学浸润“唐三国”的非遗净土。《聚铁山》一回,我们读到了100年前苏州评话语言艺术的文化保守主义,为此,我们自然会惊叹不已:作为“中国说书”共同体领头羊之一,唐耿良在1980年代为我们“保守”住了一块非遗文化的净土。同时,我们又在真心地释怀,原来唐耿良始终秉持与时俱进的光烛,只有这与时俱进的光烛,才能亮色时代精神的华彩,只有这与时俱进的光烛,才会旁涉文化传统的生态,只有这与时俱进的光烛,才可发挥艺术辩证的优势。唐耿良身为文化保守的民间说书,却又是与时俱进的文化先锋,他通过《聚铁山》加诸“唐三国”的审美凝聚,为苏州方言这道靓丽的非遗文化风景,留下了第一手文献学原始资料以及比文献学意义还要珍贵许多的精神光华。
管理学、社会学突出“唐三国”的艺术进化。苏州评话文化讲座《三国用人之道》,曾经让老派资深的说书家唐耿良成为20世纪80年代在文化界风行一时的“三国热”的始作俑者。管理学,这是唐耿良苏州评话艺术与他人说书相区别的机关。“三闯辕门”系列中,诸葛亮这个“总经理”那么铁面无私,赵云这个“总台助理”那么精灵乖巧,张飞这个“戆大莽汉”那么求救无告,刘备这个“董事长”那么束手无策,关羽这个“大董事”那么白急无助,苏州评话艺术把政治管理韬略课、军事威权指挥课、赏罚奖惩绩效课,说演得有声有色、栩栩如生,真可以成为管理学的教科书。《救主回长坂》一回中,唐耿良转身成了社会学的教授,“刘备摔阿斗,收买人心”——这是近乎标本的《三国演义》的内容,“唐三国”却敢于强调刘备没有摔阿斗。说书家应该就是社会学家,因为他天天都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他就应该能够成为大众社会心理的发言人。刘备摔阿斗,毕竟违背正常的人伦义理。20世纪说书家毕竟再也不是道学先生。
历史学考古“唐三国”的乡愁寄托。说历史风云,读历史演义,听历史故事,“唐三国”告诉我们:历史是乡愁的底板和记录。《说退陆绩》一回中,唐耿良“以身说法”,对于二十四孝他是有所微词的;《借东风》一回中,对于道教文化他是有积极态度的;《草船借箭》一回中,对古代科技和科学幻想他是有所创造发挥的。唐耿良对于已经淹没在了历史遗存中的文化乡愁,有取舍姿态,有矛盾之处,有破立见解,对此我们要以“同情的理解”,来揭示、分析、研究唐耿良蕴藏在苏州评话艺术文化乡愁及其肌理中的沉湎与寄托。
升级版张飞
心理学登临“唐三国”的艺术高峰。关于“唐三国”的心理学风流,我们已经在前文中多有表述。然则,“唐三国”让我喜欢到了骨子里的那条“心理汉子”、喜剧人物张飞才真正有型、够格来最后上演压台戏。张飞在《三国演义》中总是刻板化的“莽汉”形象——这么一个原本概念化的“熟悉的老熟人”难题如何破解?唐耿良运用颠覆之法,让“戆大”张飞在规定情境中心理化,有智慧。“戇+N”新创造、新形象、新意味的升级版张飞,便由此而生。
唐耿良说张飞的“戆”,算得上一门有趣的学问。一部“唐三国”,张飞正是经过“戆+N”的喜剧性创造,达到了质的飞跃,跃居于“唐三国”第一等喜剧人物、第一等“心理汉子”、第一等“熟悉的陌生人”之行列。
一是“戆+误会”的匠心总领。张飞的“戆”总引起喜剧性的误会、夸张,这是唐耿良喜剧创造的匠心之所在。误会中的张飞“瞎胡闹”,《古城相会》《斩蔡阳》两回书中,几乎“胡闹”掉了关羽的性命,逼得关羽差一点“痛不欲生、死了拉倒”。这一波“戆+误会”高潮,张飞的“戆”来自于他“莽汉”性格主导下的重视兄弟感情、错受孙乾误导、不信两位皇嫂、兴奋豪饮醉酒。以后,张飞误会赵子龙变节“投主”,一直要草蛇灰线到《救主回长坂》一回,说书家才一步一步地把张飞的“莽汉”性格推向极致。通过凸显“夕阳西下等赵云”的那个“熟悉的陌生人”,让张飞的“莽汉”性格得到了喜剧性的自我革命。一个从“戆+误会”起步的张飞,脱胎换骨成了一个“戆+爱心”的张飞,表现在他催着赵子龙饮食和喂马;一个“戆+细心”的张飞,表现在他约定赵子龙返程的凯旋;一个“戆+贴心”的张飞,表现在他在夕阳西下时等着赵子龙回营。
二是“戆+张力”的精心对比。如果说,《怒打蔡瑁》一回中,张飞一门心思要痛打蔡瑁,与他直言声称要保卫刘表,还只是形成了平面时空中的叙事性张力,那么,“熟悉的陌生人”张飞与诸葛亮之间反差巨大的灵魂碰撞,则为张飞改写了他与诸葛亮之间——从三顾茅庐而起的“戆+冒犯”,进而“戆+冲撞”,因违反军纪受严惩,继而“戆+归顺”却迫不及待要拜师——360°的大冲击、大对比、大逆转、大飞跃、大张力。
三是“戆+用计”的细心落地。张飞这个“熟悉的陌生人”,我们“熟悉的”当然是他的“戆”,至于“陌生人”就要提到他的“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了。到了“战樊城”,“戆大”张飞的“用计”可是来了劲。唐耿良独具匠心,他把张飞“拆锦囊”分解成了10个心理活动细节,应该说,也正是这一段心理喜剧的神来妙笔,可谓写就了不同于先前那个“莽汉”的第一等“心理汉子”张飞。“唐三国”《战樊城》这回书,不仅位列苏州评话艺术的优秀经典,而且它已经成为“中国说书”共同体喜剧创作的典范个案。张飞拆锦囊,不过是一连串“小动作”的细节组合。锦囊拆开来,说书家却是“大作特作其精细文章,尽表特表其喜剧心理”。短短300字不到,唐耿良却将“张飞拆锦囊”喜剧情境之下的“心态之定、意态之细、言态之憨、形态之萌、情态之急、真态之怕”,表现得淋漓尽致、精彩之极。
1981年10月,全国中长篇曲艺研讨会在江苏扬州召开。会议期间举行了几场晚会,由名演员作示范演出,唐耿良演出的书目正是《战樊城》。20世纪80年代,唐耿良和苏州弹词艺术大师蒋月泉、杨振雄等应邀为苏州评弹学校学员授课时,唐耿良就是携《战樊城》这回经典书目向苏州评弹新生代展示了“唐三国”精湛风流的艺术情致。
微妙法术势
最后,我还应当为“心理汉子”张飞咬牙切齿的微妙语境多说几句话。听《怒打蔡瑁》及此后相关书情,围绕着“恶贼”蔡瑁而起的“咬牙切齿”语境,竟然生动了唐耿良苏州评话艺术的微妙法术势。张飞的咬牙切齿于蔡瑁是书情当下的微妙行为流露,蔡瑁的咬牙切齿于刘备是荆州交恶的微妙细节安排,赵云的咬牙切齿于蔡瑁是居高临下的微妙感情表现,魏延的咬牙切齿于蔡瑁是英雄末路的微妙心理突破。有意思的是,刘备根本就没有表露过对蔡瑁任何一点物理形态的咬牙切齿,可是,刘备在蔡瑁面前一次次不得已地哀求,貌似低三下四,反而在更大程度上表现出唐耿良真正将刘备事实上藏匿在心“不出声”的咬牙切齿做到了家。这种种微妙的艺术感染力,可能会促使我们通过张飞咬牙切齿的微妙语境而去深刻地明晓唐耿良的苏州评话艺术——那非凡精彩的“法术势”。
注释:
①张进:《从“小矮凳说书”说起》,《曲艺》,2019年第10期。
(责任编辑/朱庭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