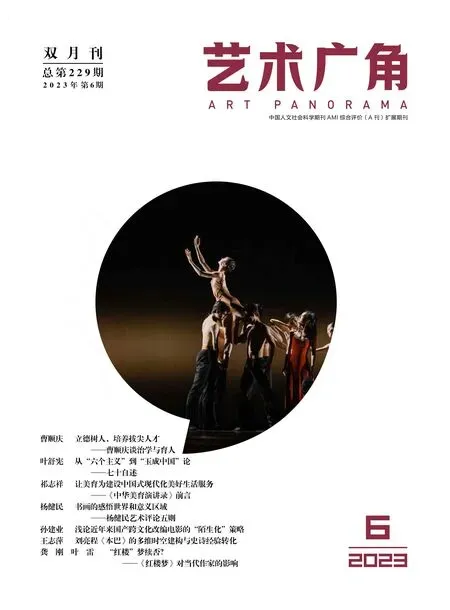立德树人,培养拔尖人才
——曹顺庆谈治学与育人
曹顺庆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在高校工作也已整整40 年。回望我的学术之路,主要有三点体会:一是中西贯通,打好中西学问根底;二是转益多师,继承大师学术风范;三是积极探索,勇于锤炼创新思维。我用这三个方法在比较文学、文艺学等领域做出了一些成果,但更重要的是,我把自己的求学之路所积累的经验凝练、总结、传递下来,应用在教书育人上,培养出了300 多位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立德树人是一件千秋万代、久久为功的伟大事业。在此,我简单分享我的治学与育人经验,希望能够在国家拔尖人才培养之事业上有所助益。
一、中西贯通,打好中西学问根底
毫无疑问,近年来我们的高等教育取得长足进步。尽管我们的高校学生数量数一数二,但是拔尖人才、杰出人才比例仍然偏低,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体现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对文学领域而言,半个多世纪来,基本没有产生与王国维、鲁迅、钱锺书、季羡林等相媲美的学术大师,以至于钱锺书在当代中国成为“文化昆仑”,广大青年学生对其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学识佩服得五体投地。钱学森之问隐含的一个现象,就是学生基础不扎实、过于浮躁。因此,只有对症下药,研究生培养才能够有的放矢。具体来说,对我们比较文学学科而言,基础不牢就体现为“不中”“不西”,既不博古,也不通今;既不通中,也不贯西。
我希望通过教学改革,培养更多人文素养好、出类拔萃的青年学子,为造就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学术人才打下基础。对于硕士生、博士生,我总是要求他们踏踏实实做真学问,心存高远做大学问,激励他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从学生选拔到人才培养,我都践行博古通今、扎根原典的原则。针对基础不扎实问题,我要求研究生精研原典,背诵名篇。博士生必须系统学习十三经,必须经过这种严格的古文功底训练。我主张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入学考试时,都要考中国古代文学典籍,范围包括“经、史、子、集”,题型多样,涵盖面极广。试题中既有大量的填空、古文断句、翻译等客观题,又有相当数量的简答、分析、论述等主观题,让考生叫苦不已。没有全面深入地学习第一手文献,是不可能心存侥幸、蒙混过关的。每年在这门专业课上败走麦城的考生数量,常常与在英语考试上失利的考生不相上下,甚至更多。
入门严,选拔公正,这就保证了每一位研究生的基本素质。当然这还只是一个开始。每一位研究生入学后,都要求系统学习十三经,而且采用的教材是中华书局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阮元校注繁体字版本,不使用白话译本。我培养的研究生,应该能直接阅读古代典籍原著,以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打下深厚的古文基础。研究生从《周易》《诗经》《尚书》《周礼》《仪记》《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春秋左氏传》《孝经》《尔雅》《论语》《孟子》等一部部学下来,可切切实实、原汁原味地近距离领略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经典。
经过严格的原典训练后,研究生紧接着要迎接更大的挑战,这也是我每一届学生最难忘的学习体验——背诵古代经典文论。无论是从心理上还是身体上,这都是一种“魔鬼般的训练”。每位同学在课堂上要当堂背诵包括《文心雕龙》里面的至少十篇、陆机《文赋》、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严羽《沧浪诗话》、李贽《童心说》等古代文论文本。相信每一位了解古代文论的人都知道,对这些古代文论,能理解就很不错了,更别说要一字不漏地全文背诵。但我坚持此举,不容通融。我的用心,就是试图做一个教学改革尝试,让同学们能读到原汁原味的东西,获得实实在在的知识与智慧,而不是大讲空论。
为了使学生也能够做到中西贯通,打好中西学问根底,从根本上培养优秀人才,我聚焦课本、课程、课堂等关键环节的教学改革。我认为,培养人才绝不是知识的简单传授,而是一种研究视野的学术锤炼。因此,对于课程设置,我打破常规,精心安排。一般是白天上西方文论课,当天下午或者晚上讲授中国古代文论,每次学生们抱着两本厚厚的《十三经注疏》走在校园里,总能赚足超高的回头率。一天之内,从西方文化到中国古代文化,这个跨越如此之大,对教师和学生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挑战。这不仅需要教师自身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还要求学生真正沉下心来,刻苦钻研。
最让学生“胆战心惊”的是中外文论课。这门课分上下节,上半节课是中国古代文论,主要涉及《毛诗序》《文赋》《文心雕龙》《诗品序》《二十四诗品》《沧浪诗话》等,要求学生必须将这些文论著作和文章全部或部分背诵出来,随机点名学生起来背诵一段,然后打断,再抽点下一位同学接上。如此,每个同学每节课都会有至少两次机会被叫起来背诵,只有平时功夫做足,才可以处变不惊,否则当场出洋相、挨批评。下半节课的当代西方文论课,教材用的是英国理论名家特雷·伊格尔顿的英文原著,两者对照合读,中西碰撞,既有趣味,又能拓宽学生视野。如在用英文教材讲授西方文论阐释学(hermeneutics),分析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言意观时,我要求学生将之与中国古代的“言不尽意”等言意观进行对接。讲海德格尔时,也与中国元素结合起来。海德格尔和萧师毅一起翻译过《老子》,认为自己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是重新开启(re-open)了存在问题(the question of being),然而是什么东西导致了海德格尔认为自己重新开启了存在问题?海德格尔认为,存在者自身的存在不是存在者,虚无是存在的特征,这是受到了老子“虚实相生”观点的影响。这种转换虽然难度颇大,一开始让学生们叫苦不迭,但是在严格的要求与督促下,最终达到了预期效果。学生们经过高强度学术训练,基本上能够做到在中西文化中自如地遨游,获益匪浅。我认为,这样安排是由比较文学的学科特点决定的。比较文学要求学生掌握至少两门以上的语言,熟悉两国以上的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地进行中西文化与文学的比较研究,做出真正有价值的成果。
在我指导的博士生中,最常见的两种情形是:一些学外语出身的学生,不熟悉中国古代的东西;而中文系出身的学生,往往外语又不是太好。因此,很难真正做到将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纯正的西方文化进行对比,也就很难产生真正有震撼力的研究成果,遑论得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造成这种后果的根源,就是不重视基础,对中国的东西没学好,对西方的东西又没真正吃透,所以创新乏力,只能去跟风模仿。这也就是我曾撰文批评过的令人痛心的中国文论“失语症”现象。痛定思痛,因此我培养博士生时特别强调“中西打通”,设置“全盘西化”的英文理论与“彻底复古”的古代文论两门课程,并且故意将两门课程安排在同一天进行,以期让学生在这两种完全异质的文化世界内能迅速转换、快速适应。这样的教学理念,不仅要求学生能用西方文论来阐释中国文学理论,也要能运用中国古典文论来阐释西方的理论,在两种完全异质的文化圈中进行比较文学研究。我在2021 年出版的著作《中西诗学对话》,就是国内第一部用中国古代文论阐释当代西方文论的成果,也是我带领学生开展中西视野锤炼教学改革的成果。
二、转益多师,继承大师学术风范
培养拔尖人才,首先要打好中西学问根底,把基础扎牢。基础扎牢之后,就要跳起来摘桃子,虚心学习,尤其是向大师学习,勇攀学术高峰,让学生迅速走上学术前沿。我有两个具体体会:第一,名师出高徒,严师出人才。老师要对学生循循善诱,激发学生研究动力,深入开展创新锤炼,学生也要主动和老师交流,获取创新源泉。第二,转益多师是吾师。鼓励学生主动请教其他名师,博采众长,万取一收,融汇创新。这是我的学术之路,也是我的育人之路。
1977 年我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当时复旦大学的校长是陈望道,中文系系主任是朱东润,都是鼎鼎大名的学者。中文系有许多名师,例如郭绍虞、刘大杰。给我们授课的老师有蒋孔阳、王运熙、顾易生、王水照、李庆甲、张培恒、陈允洁,等等。我记得同学们学习起来跟疯了似的,复旦大学图书馆的大门常常被我们挤破,当时我真的觉得复旦太好了,图书馆的开架书库竟然可以随便进入,我常常在里面一泡就是一天,看了很多书,西方的、中国的,理科的、文科的,现代的、古代的,我都如饥似渴地读。在复旦,我写了一篇学术论文《略论孔子的美学思想》。我将这篇稚嫩的习作交给蒋孔阳教授和王运熙教授,请他们批评指教。两位恩师非常认真,给我仔细修改,直到现在我还珍藏着老师的修改稿。最后这篇论文发表在《复旦大学学生学术论文集》中,这是我的处女作,对我鼓舞极大。从复旦大学毕业后,1980 年我考上四川大学杨明照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论及古代文献研究,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更被公认为取得了划时代的成果,其本人亦被誉为“龙学泰斗”。在杨先生言传身教下,我发奋努力,浸渍于中国古代文论,打好自己的学术功底。我深受恩师影响,杨先生上《文心雕龙》课,首先给同学们背一遍原文,然后再逐句讲解。我的原典阅读课,就是学习先生的方法。杨先生的书桌上,永远放着《十三经注疏》。先生博大精深的学识,炉火纯青的研究,深深激励了我。1984 年,硕士毕业后我继续追随杨明照先生攻读博士学位,1987 年毕业,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第一个博士,被学术界称为“学科大师兄”。
除了跟随吾师,还转益多师。为了深入西学根底与研究实践,达到学通中西目标,我决定去欧美访问游学,亲身体会一下西方社会文化氛围,深入理解西方文学与文论。很幸运,我受到美国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等校的邀请。1992 年初春,我告别妻子及幼女,飞到了大洋彼岸,先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比较文学系、哈佛大学东亚系和比较文学系做访问学者。哈佛大学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是我前行路上的国际大师级知音,他既是哈佛大学东亚系系主任,也是比较文学系教授,更是我的良师。在康奈尔大学,我与国际著名文论家、康奈尔大学教授艾布拉姆斯(M.H.Abrams)常常往来,受益良多。1994 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我还访问了夏志清教授。在交谈中,夏教授告诉我,他对中国文学史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将当时大陆学者不重视的张爱玲、钱锺书写进了现代文学史。多年以后,历史证明了夏志清先生的远见卓识。两年多的异域生活与访学,使我对西方文化与文学有了更深入的体会与理解。在哈佛大学和康奈尔大学图书馆,我查阅到许多宝贵的资料,汲取了大量学术信息,弥补了我的西学功底。
除了向本学科的国际大师学习,我还向其他学科的大师学习,我请教的第一位跨学科大师级人物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文心雕龙〉中的灵感论》受到钱学森呼吁建立灵感学的启发而写成,这是一个当时没有人写过的创新性问题,我斗胆将此文寄给钱学森,没想到很快收到回信。该文在郭绍虞主编的《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6 辑上发表后,引起了古典文论研究界的普遍关注与好评。
季羡林先生是我前行路上的大师级导师。1987 年9 月进行博士论文答辩,杨师明照先生亲自主持,当时的答辩委员会有徐中玉、王运熙、张文勋等著名教授,评审专家有季羡林、杨周翰、张松如、钱仲联、周来祥等著名学者,他们对我的博士论文给予高度评价。季羡林先生对我博士论文评审道:“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篇非常精彩的论文。中西文论的比较研究之重要性现在几乎尽人皆知。全面认真而系统地钻研探讨的文章或专著还很少见到。原因是,这种比较研究工作难度极大。倘若对中西两方面的文论没有比较扎实、比较系统的理解,实在难以完成这一件工作。中西文论(诗学)都有极长的历史,著作之多汗牛充栋,钻研起来,十分吃力。其次,想进行中西文论的比较研究,必须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没有宏观,则易为中西两方面的繁琐的文笔现象而束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没有微观,则又容易流于空泛,不能真正谈到点子上,不能真正搔着痒处。这样就只见森林,不见树木。”这一评价,也是对扎根中西学问知识的认可。
1991 年春,我专程赴京拜访了季羡林先生,邀请先生担任《东方文论选》名誉主编。季先生与我交谈后非常支持,并推荐我去约请著名梵语文学家金克木先生。我与金先生长谈了几次,受益匪浅。金克木先生不但答应参与编写,还推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黄宝生研究员、伊宏研究员参加印度文论与阿拉伯文论的编写工作。此外,季羡林先生还亲自约请了北京大学波斯文学专家负责波斯文论的编译。该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年正式出版,这部70 万字的《东方文论选》,绝大部分材料是第一次译成中文,填补了学术界的一个重要空白。季羡林先生担任名誉主编并挥笔作序,认为:“读此一书,东西兼通。有识有志之士定能‘沉浸浓郁,含英明华’,融会东西,以东为主,创建出新的文艺理论体系,把中国文艺理论的研究水平,东方的文艺理论的研究水平和世界的文艺理论的研究水平,大大地提高一步,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和水平上。”除了季羡林先生,学术界其他同仁也予以高度评价。王向远教授认为,《东方文论选》“填补了我国东方文论译介与研究的一个空白”。刘介民教授认为,“曹顺庆主编的《东方文论选》,是一部东方文艺的‘开山纲领’性的著作”。郁龙余教授认为,“像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一样,曹顺庆主编的《东方文论选》在中国文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钱锺书先生也是我的学术良师。我编写了《中西比较美学文学论文集》,向钱锺书先生请教“神韵”问题。我认为,虽然《沧浪诗话》是王渔洋“神韵说”的理论渊源之一,但严羽在《沧浪诗话》里并没有正式提及“神韵”一词。钱锺书在《谈艺录》和《管锥编》两书中多处征引严羽所谓“诗之有神韵者”“沧浪独以神许李杜”等,从文献上考证,此乃子虚乌有,是误引。但令人遗憾的是,学界已经出现了以讹传讹的现象。由于钱锺书在学界的权威地位,有些研究者未加辨别就直接引述了钱锺书的错误观点。事实上,严羽的诗论主张与“神韵说”确有着密切联系,但“神韵”这一概念范畴在严羽所处的南宋尚未出现,钱锺书在《谈艺录》和《管锥编》两书中论述“神韵”的相关内容,则是混淆了“神韵”的提法和它的理论渊源。我斗胆写信告知钱锺书先生,希望《谈艺录》和《管锥编》再版时能够更改过来。信发出去后,我非常忐忑,几天没有睡好觉。没想到先生很快回信,承认确实有误,并极为谦虚地引用陶渊明的诗句“所云多谬误,君当恕醉人”来表示其诚意,由此可见大师的风范。这也为我的学术之路和育人之路做了很好的示范。
正确认识师承关系,是立德树人的关键问题。我认为,老师传授的不仅是知识和能力,更是一种文明的学脉,老师和学生是学术命运共同体,超越时间与空间,动态铸就民族之根和文化之魂。人类文明源远流长、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数千年的学术实践证明,学术传承最直接、最重要的是师承关系。正是因为有学术上的师承关系,才有一个又一个学派,才生成了一个个话语体系。从古希腊苏格拉底到其学生柏拉图,再到其学生亚里士多德,造就了古希腊学术的黄金时代。中国的孔子与学生共同建构了儒家学派,由孔子的学生编撰的《论语》就是明证。现当代德国的胡塞尔及其学生海德格尔、学生的学生伽达默尔,共同建构了现象学、阐释学等重要学术理论话语。有鉴于此,我携学生共同研究与提出了中国文论话语建构与比较文学变异学等重要学术话语理论,力图解决人才培养如何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时代背景下,在教学与科研中推动师生学术传承中的思想融合,鼓励学生积极进行理论创新,以培育能够进行理论创新与话语构建的拔尖人才的问题。
总之,我十分鼓励学生志存高远,探访名家,转益多师,开拓眼界。我指导的研究生近年来有数位获得国家公派访学奖学金,前往比利时鲁汶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等名校访学。针对研究生培养的具体问题,我邀请海外专家到中国授课。譬如,对于英文学术写作能力的训练,很多大学教育是缺乏的。我有意在培养我的学生时创造此类机会。2019 年夏天,我邀请了韩国成均馆大学的加拿大藉学者西蒙·埃斯托克(Simon Estok)教授来到四川大学上英文学术论文写作课程。西蒙教授是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也是权威英文刊物的主编。课程取得了卓越的成效,参加课程的几位学生不少都发表了高质量的英文学术论文。我深知,只有用心用情培养学生,才能够成就学术流派,成就学术大师。导师不仅是在“传道授业解惑”,还承载着赓续文明学脉的历史担当和初心使命。作为学生也必须明白,读书是要成为可堪大任的人才,要弘扬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在国际上树立文化自信。这就是人才培养的初心和基本立场,也是立德树人的思想锤炼。
三、积极探索,勇于锤炼创新思维
除了课堂上背诵原典、读外文原版文献等严格要求,我培养学生,还要求他们要有批判质疑精神,要有争锋相辩的思维习惯,要有勇于探索的创新锤炼。思维方式特别重要,这是“授之以渔”的学术训练。为什么要磨砺思维?第一,因为当下我们的学术研究太缺乏创新思维。理论话语基本上是跟别人走,不断“跟着讲”“照着讲”,就是不能“自己讲”“对着讲”,盲目相信老师,相信权威,相信西方,造成中国理论“失语症”。第二,学生缺乏对话与论辩训练。研究生不敢有自己的想法,不敢提出创新观点,不敢与老师和权威论辩,不敢大胆设想、小心求证,害怕犯错误,害怕被批评。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就是要求我们敢于学术争论。思想的火花总是在碰撞中产生的,没有科学的论辩,没有承认错误的勇气,学术则不可能进步。
针对这个问题,我的博士生课程就注重加强讨论争辩,磨炼学生的批判思维。我引导组织博士生每周定期进行集体讨论,先要求每位博士生按顺序按主题写一篇小论文,然后由其他博士生来分析批评,每周评点一位博士生的文章。我上课要求同学们分成反方和正方进行辩论,要设法找出别人的问题,横挑鼻子竖挑眼,预先告知不准生气。每次讨论,我都会安排两位学生做“刀客”,由他们负责“主攻”,专门挑论文的刺,丝毫不能手软留情面,批评得越尖锐越好。其他学生负责“协攻”,每人都要找出一两点论文的不足,找不到问题的学生就要被批评。由于这种压力,大家都抛开了学术讨论常见的那种虚伪客套,各显神通,对本周提供论文的同学进行火力猛烈的集中“攻击”。我向所有的同学声明,被评点的那位同学,届时无论被怎样批评,都不能生气。虽然有言在先,但是由于论争时场面火爆,一方咄咄紧逼,尤以两位“主攻手”为甚,一方使出浑身解数,尽力应战招架,往往让被批评者脸红耳赤,甚至真的又气又急。当然,等到下次他成为“刀客”,自然也不会客气。课堂上这种热火朝天,有效锻炼了同学们的学术思辨能力。这种学术争鸣的气氛,让人既紧张又兴奋,成为大家每周期待的学术盛宴。通过这种讨论,一学年下来,学生的学术敏感性增强,知识面大大拓宽,论辩能力增强,写出来的论文有理有据、逻辑严密。更为难得的是,大家每周一聚,切磋交流,在论辩中促进了友情,懂得了合作。
我用我的学术研究案例教育我的研究生:学术研究都是问题导向,都是跟着问题走的,找不到问题,就不可能有好的选题。我从《文心雕龙》研究,到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到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研究,到“失语症”研究,到重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研究,到中国古代文论的中国化研究,再到比较文学变异学、比较文学阐释学研究……一路走来,都奉行“入门须正、立志须高”的宗旨。具体地说,我给我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的四项基本原则是:(1)立志要高,不拾人唾余,要做天下第一篇;(2)现实意义要强,要攻坚克难,解决学术界重要问题;(3)要量身裁衣,扬长避短;(4)材料要丰富,思路要清晰。“入门须正、立志须高”,意味着选题必须有创新性,已经有人做过的题目,原则上不能够再选,论文要做天下第一篇。例如,杨师明照先生之后,《文心雕龙》研究还能不能够再出天下第一篇?当然可以,创新无止境,实践无止境。我指导刘颖博士写出《英语世界的〈文心雕龙〉研究》,就是学术界第一部研究《文心雕龙》在西方英语世界的译介传播和阐释问题的著作。又如,我的博士生陈蜀玉是学法语出身的,法语非常好,我了解到当时还没有法语全译本的《文心雕龙》后,就鼓励她把《文心雕龙》全部译为法语,并且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组成部分,展开深入研究,最后写出博士学位论文《〈文心雕龙〉法语全译及其研究》,大获成功。因为单凭她把《文心雕龙》全文译成法语,就填补了世界法译《文心雕龙》空白,就非常有价值,成为全世界《文心雕龙》第一个法译本,这就是天下第一了。
我主张:学位论文选题既要尊重研究生个人的研究兴趣,还要结合学术前沿;既要单兵作战,也要集团化作战;既要有个体成果,也要有成体系、成建制、有规划效应的成果。通过这样的培育,我的研究生很多都拿到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重点或一般项目,获得教育部和省级社科优秀成果重要奖项,不少人已经成长为知名学者和学科骨干。
在启发问题意识的同时,我还注重学风的锤炼。严谨务实的学风,是我培养研究生的底线和红线,也是研究生毕业后从事学术研究的生命线,只有基于优秀的学风和治学态度,才可能源源不断做出优秀的学术成果。具体来说,我的要求就是:(1)严禁抄袭!全文抄袭、观点抄袭、变相抄袭,任何有抄袭性质的现象都不行,一票否决。我自从教以来就对此保持“零容忍”态度,要求学生坚决不准出现,把问题处理在萌芽状态。(2)注释要严谨。防止二手注释、假注释,尽量不要用转引文献,必须看第一手文献,引用第一手资料。(3)注意细节规范。从大的逻辑框架到小的语言表述,从篇章体系到标点符号,从当页注释到参考文献,都要尽可能做到细节层面的精准规范。
回看我指导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基本上都符合这些要求,目前没有出现任何学术不端现象,因为学生们知道这是我的红线,踩不得。严谨的学风,必须体现在细节之中,研究生正值年富力强、思维活跃之时,应把握机会将每一次写作当作立身之著来完成,务必精益求精。我也一再要求学生,治学没有捷径,必须坐冷板凳,十年甚至几十年磨一剑。厚积薄发、规范严谨,要写就写学界第一篇,要敢于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别人写过的坚决不写,学术价值、现实意义不足的坚决不写。正是在学风方面的严格要求,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已逐渐形成了几个颇具特色的毕业论文研究方向与模式,而且做出了很多扎实的学术成果。
目前,我指导的博士分别在全国122 所高校任教,其中有教授123 人,副教授81 人,博士生导师59 人;有高校校长4 人,副校长2 人,学院院长、副院长27 人,部分学生已成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国家级教学名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一流大学资深教授、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获奖者等各类杰出人才,他们活跃在国内外教学研究一线。这些已经证明行之有效的教学改革模式,是我从40 年教学实践中得来的一笔珍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