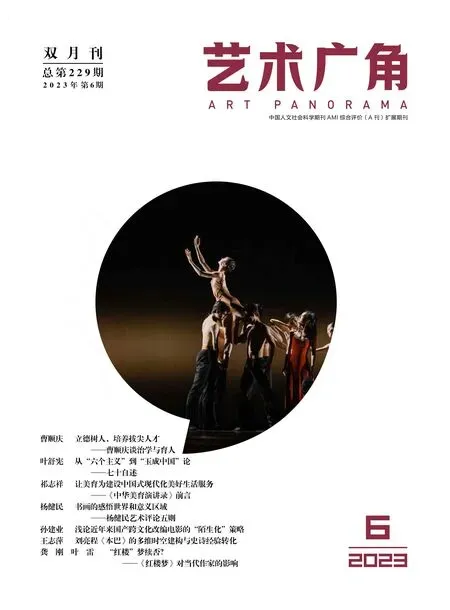集体主义视域下“十七年”电影中的金钱话语研究
秦凤华
金钱,是电影作品中常见的叙事元素,创作者常常借助它设置情节、制造冲突、刻画人物、凸显主题。比如,在德国影片《罗拉快跑》中,创作者将救助男友所需的10 万马克设置为主人公罗拉直接的戏剧性需求,情节由此展开;国产片《老炮儿》中,为营救儿子需要筹集的10万块现金将主人公六爷推入了困境,故事也因此得以启动。纵观中外电影发展史,甚至有不少作品直接以“金钱”命名并围绕金钱展开叙事。如《金钱梦》(1981)、《金钱帝国》(2009)、《金钱世界》(2017)等。银幕上也因此形成了经久不衰的金钱叙事。
金钱也是“十七年”电影在故事讲述中的常见元素。但在新中国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独特的文化语境的规约下,“十七年”电影创作者对“金钱”采取了非常规的诠释视角,创造了不同于其他历史时期的金钱话语表述方式与内涵。“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1]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136 页。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集体主义价值观逐渐被确立为国家思想文化发展的主导性原则。通过叙事对集体主义价值观进行宣传与建构也因此成为包括电影在内的文艺作品的重要使命。“十七年”电影金钱话语的显著特点正在于,创作者将其与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表述紧密挂钩,通过对金钱元素的程式化处理来彰显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合理性、正当性。
“十七年”电影中的金钱话语,主要表现为以讴歌工农兵人物大公无私、舍私为公为正面引导和以鞭笞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官兵自私自利、唯利是图为反面批判两大类别。即在以工农兵为代表的正面人物手中,金钱是合理的、纯洁的,在以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官兵为代表的反面人物手中,金钱则是丑陋的、肮脏的。同时,“金钱”所引发的戏剧性动作在反派人物身上也截然相反。工农兵人物追求的是怎样把钱交给党或送给同志,实现金钱的利他性价值;而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人物孜孜以求的则是如何获取金钱、满足私利。创作者通过对前者的讴歌、对后者的批判,从正反两个角度抒写了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正确性与合理性。
一、正面引导:讴歌工农兵人物大公无私、舍私为公
1.歌颂共产党员一心交党费
在“十七年”电影中,工农兵等正面人物手中的钱,总是被赋予纯洁的色彩,用途上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共产党员上交给党的党费。
“党费”走进电影,源于“共产党员”这一崭新人物形象在中国银幕上的登场。虽然早在民国时期党就领导并参与了左翼电影(20 世纪30 年代)和进步电影(20 世纪40 年代)的创作,但受制于当时的社会环境,电影作品中未能有共产党员形象的真正出场。创作者们只在一些影片中设置了诸如“革命者”或“革命进步青年”(如《女性的呐喊》中的少英、《三个摩登女性》中的周淑贞、《八千里路云和月》中的汪玲玉、《希望在人间》中的雨生)等比较隐晦的角色。1949 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共产党员”登上大银幕的合法性得以确立。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1949)中,便出现了厂长和电炉组长两位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形象从此光明正大现身于大银幕,并成为“十七年”电影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形象。
共产党员形象一经登场,便成为先进与模范的代表,展现出各种各样的优秀品格。银幕上,他们意志坚强,英勇无畏;他们大公无私,心胸坦荡;他们爱憎分明、立场坚定。最重要的是,他们拥有一颗对党无限忠诚的心。以艺术人物的忠诚来激发观影群众对党的忠诚,将其询唤为拥护党、追随党的主体,是“十七年”文艺作品面临的重要课题。因此,在共产党员的诸种优秀品格中凸显其对党的赤胆忠心,成为“十七年”电影的常规表达。一些与共产党员光辉形象相关的桥段便被设计出来,如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拒不出卖组织,就义之时昂首挺胸视死如归,都令观众耳熟能详。此外,展现共产党员在特殊场合下执着地“交党费”,也是一些作品塑造共产党员爱党品格时在情节设置上的共同选择。这使得“十七年”电影中出现了别有意味的党费叙事。
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董存瑞》(1955),是较早描写交党费情节的一部影片。创作者设计了两位交党费的人物:区委书记王平和青年战士董存瑞。王平交党费的行为发生在他中弹牺牲之际,他把党费交给董存瑞,委托他转交给组织。这一场景的设置主要是为董存瑞的精神成长服务。王平是董存瑞革命道路上的引路人和八路军的榜样,他在生命的终点还没忘记交党费,这使董存瑞亲眼见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德,这对他坚定革命信念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同时,这一情节的设置也向观众呈现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高大形象。如果说王平交党费是在一种悲剧气氛中完成的,董存瑞交党费则带有喜剧性。他还没入党,却要交党费,将党费和入党申请书同时交给连长。接续“蘑菇”“摔跤”等情节,“交党费”再次展现了董存瑞执拗的性格和急脾气。同时,交党费这一环节的设计,意味着董存瑞在思想境界上实现了跨越,为他以后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尤其是舍身炸碉堡的情节做下了铺垫。
1958 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另一部关涉党费叙事的影片《党的女儿》。该片改编自王愿坚小说《党费》。小说中呼应题意的情节是,主人公黄新在不能正常交党费的情况下,与村里的其他党员一起,腌制了一筐咸菜,作为党费。原小说篇幅短小,改编成电影时创作者对情节进行了扩充和改造,但腌制咸菜交党费的内容被原封不动地搬了进来:得知山上队伍缺盐,玉梅、秀英、惠珍三位女党员准备了一筐咸菜作为党费;当敌人包围村庄,玉梅嘱咐联络员小程,一定要把她们的这筐“党费”带走;敌人来到,指着咸菜筐问里面是什么,玉梅骄傲地回答:党费。一筐咸菜所代表的“党费”,成为影片高潮段落推进情节、深化主题的核心元素。此外,故事结尾处,玉梅牺牲后,留给亲人的遗物是一个小纸包,里面是党证中间夹着两块洋钱。显然,这是玉梅嘱托亲人替她上交的党费。正如影片片名所显示的,三位女共产党员是“党的女儿”,用作党费的一筐咸菜和两块洋钱是她们对党一往情深的象征物。
将党费设置为一个共产党员牺牲之际留给党的礼物,也出现在谢晋“十七年”时期最重要的影片《红色娘子军》(1961)中。故事里,承担党费叙事功能的是贯穿情节始终的“四个银元”。起初,党代表洪常青把吴琼花从地主南天霸手中救出,分别时他送给她四个银元作为生活费;吴琼花加入红色娘子军,她从洪常青口中得知她的入党申请已得到批准,于是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当初洪常青赠送给她的四个银元,作为第一笔党费;洪常青牺牲后,吴琼花来到洪常青最后抗击敌人的山头,无意中发现了他埋藏在土层下面的公文包。这是洪常青留下的遗物,其中包括四个银元和她得到批复的入党申请书。而这四个银元,正是她此前交给他的党费。“四个银元”三易其主的“旅行记”,包含着一个丰富的意义系统:洪常青将四个银元送给吴琼花,不单单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关心,洪常青拥有党代表的身份,他送给吴琼花的这份钱,从更高的意义上象征了中国共产党对穷苦大众的关怀;吴琼花没舍得用掉这四个银元,并在加入党组织后将其作为党费上交给洪常青,显示了吴琼花对党的忠诚与敬仰;洪常青用心保存着这四个银元,在生命的最后仍然想办法保存着这笔钱,同样表达了一个革命者对党的热血丹心。
党费,可以说是“十七年”影像世界里最神圣的钱。“金钱”这样一种物质符号,在革命战斗的特殊环境中被建构成共产党员与党联系的精神纽带。创作者借助党费叙事,首先表达了共产党员对党的深厚情感;同时,党是集体的化身,爱党就是爱集体,不忘交党费、一心交党费的情节呈现,也凸显了共产党员的集体主义意识和品格。
2.赞美军民不计金钱、互助互爱
军民一家亲,也是“十七年”电影适应主流话语的表述需求予以凸显的内容。诸如红军战士帮老乡挑水打柴、老乡为解放军队伍缝衣做鞋之类的情节在银幕上时常可见。此外,“十七年”影片还常常通过描绘革命军人与老乡之间赠予金钱的行为来赞美军民一家、互助互爱。这也是“十七年”电影涉及工农兵人物的另一类金钱叙事。
《新儿女英雄传》(1951)中,老乡自愿给八路军送柴火,八路军执意塞钱给老乡;《万水千山》(1959)中,藏族老乡送马给红军,红军要出钱,老乡不收,最后只留下一枚银元当作纪念。与党费叙事一样,这些与金钱元素相关的情节,出发点都是“给予”,而不是“获取”。要么是同志将钱留给老乡,要么是老乡将钱还给同志,以此来讴歌军民之间的鱼水深情,以及工农兵人物大公无私的高尚品德。
在“十七年”电影中,工农兵正面人物并不热衷于与金钱打交道,他们参与革命或建设活动不是为了钱,一旦手上得到了钱,他们通常会想方设法将钱运用到党和集体需要的地方。一句话,工农兵人物对待金钱的态度始终是无私的、利他的。创作者通过描绘工农兵人物毫不利己、一心为公的金钱话语图景,从正面彰显了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正确性与合理性。
二、反面批判:鞭笞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官兵的自私自利、唯利是图
与展现工农兵人物手中金钱的纯洁性相反,在“十七年”电影中,当与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官兵等反面人物相关联时,金钱元素被赋予的则是肮脏、腐化的特性。叙事动作也由“给予”变为了“获取”。如果说正面人物追求的是金钱的利他价值,反面人物追求的则是金钱的私利目的。创作者通过描写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军官等反面人物追求金钱的丑恶行径,严厉批判了利己主义和私欲观念,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正确与合理。
1.讽刺资产阶级爱财如命
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资产阶级人物,通常是“十七年”电影批判的对象。“十七年”电影在批判资产阶级人物时(主要包括资本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深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普通百姓),往往选择从金钱情节入手。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适应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代潮流,电影界拍摄了一批以资本家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影片,如《夫妻进行曲》(1951)、《不夜城》(1957)。《夫妻进行曲》着力描绘资产阶级人物经过改造实现了思想认识的转变,其中,金钱观的转变尤为重要。主人公陈启元在新中国成立前是洋行职员,报酬丰厚,新中国成立后,洋行倒闭,他加入国营机械厂做了工程师。虽然挣钱不多,但意义不同。从人民政府领到第一份薪水后,陈启元深刻认识到,这钱“比什么都宝贵,都值得骄傲”。影片通过陈启元的自我改造和对金钱的重新认识,实现了这样一种潜台词的表达:只有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获取的报酬,才真正具有价值。创作者同时还设置了陈启元妻子葛丽娜作为反面人物与其进行对照。为了继续过住洋房、雇保姆的舒服日子,葛丽娜将陈启元从银行拿到的遣散费偷偷交给投机商人放息和投资,结果自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葛丽娜赚钱目的是保住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资产阶级生活,赚钱方式是通过买进卖出、投机倒把,影片既批判了为个人享乐追求金钱的行为,也批判了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不夜城》的故事模式与《夫妻进行曲》不尽相同,该片创作的出发点是完成上级拟定的“反映我国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之任务”[1]熊坤静:《电影〈不夜城〉创作的台前幕后》,《福建党史月刊》2011 年第5 期。,影片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对公私合营的宣扬缝合在一起。其中,前者主要体现在对以张伯韩为首的资本家过度贪婪金钱的描绘上。比如,国家给他们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空间,他们却乘机钻空子,搞“五毒”赚黑钱。唯钱是举、唯利是图被描绘成资本家的本性,并成为影片鞭挞的重要内容。
《千万不能忘记》(1964)和《青松岭》(1965)两部影片则将批判的对象指向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老百姓。《千万不要忘记》中,人物多次说出“钱”字,镜头画面多次聚焦于“钱”,是谈钱密集、金钱镜头出现频率颇高的一部影片。片中关于金钱的线索围绕反面人物姚母展开。姚母被塑造成一个爱财如命的形象。首先,她满口是钱,处处谈钱,比如,“人家里头穿着一套二百多块的西服,外边还套着一件毛料的风衣,就连那皮鞋都是出口。”“我可不跟你们到厂子里挑榆木袋去,一斤才几分钱,还不够买盒烟抽的。”“少纯啊,有奖金吗?”其次,为了得到钱、赚取好处,姚母主意很多。亲戚托少纯修鼓风机,少纯说了不要钱,她却偷偷把钱收了;工厂的会计老刘给友良送来50块的补助费,被友良拒绝,姚母以借互助费的形式把50 块强行借走;为了给少纯买料子服和补借互助费的亏空,她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动少纯去打野鸭子卖钱。创作者特意设置了姚母曾为鲜货铺子老板娘的身份,以此证明她的金钱思想有其阶级性根源。“千万不要忘记”,就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只不过这部影片阶级斗争的对象不是搞政治破坏的坏分子,而是被资产阶级金钱观严重腐蚀的姚母。
《青松岭》与《千万不要忘记》可谓殊途同归,高唱阶级斗争,痛批资产阶级。故事同样设置了一位满身资产阶级习气的反面角色:车把式钱广。他身上的资产阶级特质也是通过“爱钱”体现出来的。利用赶车之便,钱广替村民们往自由市场卖山货,并鼓动其他村民从集体劳动中旷工,去山上捡榛子卖钱。他口中最具煽动性的一句话就是“吃饭靠集体,发财靠自己”。为了保住手中这根把马车朝资本主义道儿上赶的鞭子,钱广靠小恩小惠拉拢村民。他还暗中与坐过牢的钱老顺勾搭,合谋私利。总之,钱广被塑造成一个满腹“钱经”、唯“钱”是图的形象。为了强化对这位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人物的揶揄和讽刺效果,创造者干脆让他姓“钱”。而全名“钱广”,则暗喻了他“广收钱财”的卑劣的人生目标。
2.揭露上层阶级对底层阶级的压迫和剥削
揭露底层劳苦大众在旧社会被压迫、被剥削的悲惨命运,是“十七年”电影另一常规主题。压迫和剥削的施动者包括地主、资本家、反动官僚和帝国主义侵略者,受动者则包括农民、工人、小知识分子等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各行各业的劳苦大众。压迫和剥削的主要形式,便是经济上的压榨,“十七年”电影由此形成了揭露阶级压迫和剥削的金钱话语内涵。
通过金钱元素来凸显剥削阶级对劳苦大众的压迫和掠夺,在“十七年”电影中很多见。如,杨白劳在大年三十去给地主黄世仁交利钱(《白毛女》),工人王正庭一家在年关把孩子卖给林老板的二姨太(《三个母亲》),卖艺女月红和春花被迫将赚得的包银分给班主阿鑫(《舞台姐妹》)。《我这一辈子》(1950)中的一组画面尤具代表性:商铺里,官老爷秦先生带着胖太太在买50 块一瓶的日本香水,镜头一转,一只戴着戒指的手把几摞大洋放到桌子上,伴随着“一十、二十、三十,你卖不卖”的声音,原来,这是孙元家正在卖孩子。导演石挥运用对比蒙太奇将两个场景进行并置,其意图不言而喻:当官的,买瓶香水就花掉50 块;穷人家,一个孩子才卖30 块。影片对阶级剥削的揭露一针见血。
受压迫的不单是以工人、农民、底层艺人为代表的无产者,“十七年”电影还呈现了小工商业者遭受压迫的图景。《方珍珠》(1952)和《林家铺子》(1959)在这方面颇具代表性。两部影片均按照主人公一步步被钱逼向绝境的思路来组织情节,凸显阶级压迫的主题。《方珍珠》中,民间艺人“破风筝”在抗战结束后带着一家四口返回北京,为了生计,决定重操旧业开办戏院。谁知事业未起,向他勒索钱财的瘟神一个个接踵而至。先是曾经给他写唱词的孟先生,问他要过去八年里的唱词费,接着是宪兵班长登上门,要求他兑支票。破风筝好不容易应付过去,更卑劣无耻的搜刮还在后面:园子开张在即,小官僚狮子大开口索要门票,警察局的小警察以不发执照为威胁伸手要钱。破风筝被刮了个精光,连开张所需基本物品都没法置办了。义女珍珠拿出生父留下的项链,破风筝典当了项链,才勉强让戏园子如期开张。哪知客人未到“爷”先至,巡警以“厕所不干净”为由又揩了一把油。破风筝就这样被一遍遍“洗劫”,直至最后彻底破产。与此相似,《林家铺子》将情节建立在林老板被“钱”逼到死角的过程中。为了能继续销售日货,林老板不得不拿出400 元贿赂商会会长;八折甩卖,好不容易让生意热闹了一回,又被商会会长逼迫打点上面的局长;时局大变,日军进攻上海,上海客人登门索要欠账,本想从钱庄换钱,却被经理扣了庄票顶了债;上海难民的到来,仿似使林源记的生意发生了转机,凭借“一元货”的热卖,林老板总算大赚了一把,但“林源记”并没有绝地逢生,而是走向穷途末路。作者意图通过林老板的处境“表现出从前的工商业者大鱼吃小鱼,自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的命运掌握在官僚手里”[1]钟桂松:《批判电影〈林家铺子〉始末》,《茅盾研究——第七届年会论文集》,新华出版社,2003 年版,第517 页。。在这个阶级社会的金字塔里,林老板处在中间地带,是“小鱼”,位于他上面的是腐朽官员,在他之下,还有更小的个体经营者和更广大的农民。影片不仅表现了林老板被上层官员榨取,还展示了他如何在经济上剥削比他更弱小的人。尤其是他的逃跑,使得朱三太、张寡妇等人的钱打了水漂,他作为“小鱼”,是有“原罪”的。影片出色地将各色人生汇集到金钱的链条上,既描绘了一个小人物求钱路上的悲哀,又大手笔勾勒了一幅阶级社会的“金钱图”,将阶层间垂直存在的压榨与剥削刻画得入木三分。
3.批判国民党官兵腐朽堕落
“十七年”时期,银幕上的国民党官兵“基本上是一群草包”[2]章柏青、贾磊磊:《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上册),文化艺术版社,2006 年版,第239 页。。他们自私自利、贪生怕死,与共产党人形成鲜明对比。
金钱是人格的试金石。在“十七年”电影中,国民党军人的卑劣本性,典型地体现在他们对金钱的态度上。正如党费叙事张扬了共产党员的高洁忠贞,围绕国民党军官的金钱叙事则揭露了他们的腐朽堕落。国民党军官的生活空间,常常被描绘成纸醉金迷、花天酒地的堕落世界。他们跳舞、喝红酒、勾搭女人。对待金钱,更是一种贪得无厌的态度。《钢铁战士》(1950)中,敌师长向下属交代寻找兵工厂和粮食的任务后,特意加了一句“要查到了,还有相当大的一笔奖金”。暗喻金钱就是他们最大的动力。在“十七年”影片中,共产党队伍休闲娱乐的方式主要是讲故事(如《南岛风云》《渡江侦察记》)、说快板(如《小兵张嘎》)、唱歌(如《万水千山》),而国民党的娱乐活动通常只有两种:跳舞、打牌赌博。而打牌赌博就涉及到赌资。《大地重光》(1950)、《胜利重逢》(1951)、《冲破黎明前的黑暗》(1956)等影片都呈现了与国民党官兵打牌赌博相关的金钱叙事情节。《战火中的青春》(1959)里的一个场景令人印象深刻。我方军队乘夜色潜入,偷袭敌人营部。映在窗户纸上的是国民党军官们聚会、抽烟的身影,屋子里隐隐传来搓洗麻将牌的声音。队伍冲进去,敌人被打得七零八落。在一个缓缓拉开的镜头中,一名死去的国民党军官趴在桌子上,讽刺的是,他脸枕在一堆钞票上,手中还攥着一沓。镜头继续拉开,钞票、酒瓶和香烟盒,满桌狼藉。可以说,这一桌“内容”代表的,正是国民党官兵所追求的金钱世界。别有深意的是,接下来的画面中,我方排长雷振林和副排长高山就坐在这张堆满钞票的桌子边,进行了一场关于“英雄主义”的思想交锋。他们“毫不客气”地抽了敌人留下的烟,却丝毫没动桌子上的钱。“钱桌”以局部画面的形式间歇性地一再出现,然而雷振林和高山始终对其视而不见。最后一个镜头,高山拿起桌上的枪和手电筒,随雷振林一起离开去执行任务,桌上的钱依然原封不动。金钱在革命者眼中俨然就是粪土。导演通过对国共两军对待金钱的对比描绘,二者相互映照,使得敌军的“丑”和我军的“美”都得到了强化。
三、结语
综上,在“十七年”的影像世界里,与工农兵正面人物对待金钱的高风亮节、无私奉献截然相反,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官兵等反面人物面对金钱,无一不是一副贪婪无耻、腐朽堕落的嘴脸。根源在于,正面人物信奉的是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反面人物追随的是只为个人的利己主义。影片通过对反面人物爱钱贪钱的描绘及其批评,从另一个角度抒写了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总之,在“十七年”电影中,新政权对金钱话语进行了全新的改造,总的倾向便是讴歌集体主义价值观引导下的金钱付出,批判个人利益驱动下的金钱获取与消费。金钱只有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国家和集体利益存在,才是合理的、纯洁的、可接受的;反之,则是丑陋的、堕落的、令人不齿的。一句话,金钱的取得与支出,必须与国家、党、集体的利益相关,与崇高的精神价值相关联。这是因为,在新中国的价值体系里,“金钱”可谓天然地带有“原罪”。新中国作为以国家主义、集体主义为立国之本的新型社会主义国家,必然在价值观层面倡导轻物质、重精神与轻金钱、重道德的理想坚守,批判个人主义基础上的金钱追求和物欲享受,以防止人与人之间变成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资产阶级式的“赤裸裸的利害关系”[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第30 页,第40 页。和“纯粹的金钱关系”[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第30 页,第4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