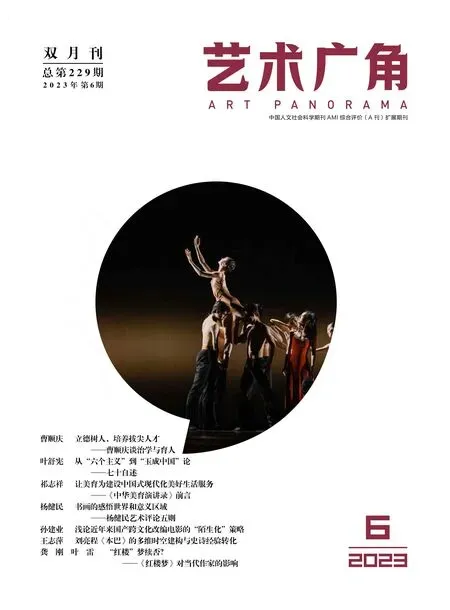书画的感悟世界和意义区域
——杨健民艺术评论五则
杨健民
一、登翰墨象的感悟世界
大约是许多年前,无意中看到刘登翰的一幅书法作品,当时就觉得要说几句,又不知从何说起。他与我共事多年,当过我的领导。作为学者,他的学问相当好,所以要对他的书法说点什么,我多少有些踌躇和犹豫。我喜欢阅读书法作品,但对书法的修养十分薄弱。后来看到三册《登翰墨象》书法集,那些以水墨赋形的作品不断地打动着我。
这大半年来,对于登翰的书法,我一直没有发动思想的引擎,原因在于各种想法随机地涌现,显得有些嘈杂。他的书法究竟属于哪一路呢?或者说该归于哪一种风格?其实他的作品是无法给予一个准确的归属的。这是他的任性。
任性的作品一定有它的独到之处——我想。
登翰在中国台湾举办过书法作品展览,被中国台湾的艺术家称为“水墨书法”。既然是水墨,必定讲究墨韵。登翰的书法让墨韵在书法的线条上舞蹈,这种默契肯定是存在的。
从书法的本源意义上看,登翰书法的章法并无过于强烈的变轨,即便是行草,他的每一个字的结构依然是勾画凝重、顿挫分明的。但是我注意到一点:腾挪。腾挪是形式感的一种表现,它是打滑地进入登翰笔下的感觉世界的。登翰对每一个字的把握,无疑是充分自由的“游戏”。不拘泥于笔画的枝蔓,而是如同秋日丛林中变化无尽的枝条的分割,其最终要诉诸的就是水与墨的一种意象赋形。尽管如此,似乎也不能把登翰书法归入现代性一极。在我看来,登翰书法的艺术策略就在于,他果断地抛弃在书法大片的沃土上种植出什么,恰恰相反,他在一片荒芜的沙漠和戈壁上种植出了属于他的苹果。
对于登翰书法,确乎没有必要调集一批晦涩的术语,“书法是快乐的游戏”——这一直是登翰津津乐道的。把它说得简单一些,这肯定更符合登翰书法的本意。游戏就是纸上的一种“游走”,游走的意义不在于别的什么,而在于书法的诗境和异趣空间。这才是登翰书法的意义区域。置身于他的书法作品面前,我深感骇异——这些还是汉字吗?它们时而如危岩奇崛奔突,时而如枯藤婆娑起舞,无论是笔势的尖叫,还是泼墨的率性,都在以一种惊人的活跃告诉人们,书法的无逾矩之形一定包含了某种强烈的表述欲望。
登翰的另一个身份是诗人,诗的意象和书法的墨象的完美聚合,造就了他的独特的书法形态。在这里,我不想运用诸如象征和隐喻等概念,将他笔下的那些墨象艰难地泅渡到意义的彼岸。书法不是猜谜,那满纸奔走的,无论是千头万绪,还是欲说还休,都在作品本身的谜面上,一个自然的谜底其实就跃然纸上。“书中有画,画中有书”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观,在登翰书法中是否发挥得淋漓尽致?这肯定不是一个伪命题。也许,我们可以将登翰想象为一个逆行的象征性姿态,而不必在乎他如何用墨及用笔。我想这样可能会有趣得许多。倘若在登翰书法面前,像一个无知的幼童那样去面对一个高深的智者,这样就很难熄灭种种自以为是的形而上学冲动。
作为一位诗人和学者的水墨感悟,登翰在更多的时候以那一管笔呼风唤雨,将笔墨的意象转化为一种天姿卓绝,不可言喻。他的作品时常让人看到千山万水,看到引而不发的弯弓,甚至看到乱石穿空的欲飞之势。比如他的“山”字写得如山峰之形,细看一下,却似乎有万水在奔流。一切是如此的灵动和诡异,书法的结体和笔触隐含了无穷的变幻方向。造型的无羁可能瓦解或者融化传统书法的某些法则。一切造型都可能在他笔下出没,一切也都可能在他心里莫测地孕育。登翰说:“我喜欢毛笔在宣纸上游走时,水墨的互相浸融、渗透、晕染,在浓淡枯润中显出异趣。”对此,我似乎更愿意如此想象:他的那些以种种曲线和墨色变幻起伏而提供的幻象,随时可能聚集他的多少往事或心事。
显然,不能就此说明登翰书法就是一种师法自然。师法自然并不是完全搁置主体,而是让人看到一种对话的姿态。这样,他笔下的“山”字就不是自然意义上的山,也许是夜深人静时的孤灯一枚;他笔下的“水”字也不是自然意义上的水,也许是一群掠过街头的尖啸少年。庄子说过,道无所不在。一个有趣的书法家并不在乎他笔下点染的是一只蚂蚁、一溜小涧或者一茎风中的稗草,重要的是他的纵横恣意画出了哪些不同寻常。
这么说,登翰书法显现了某种离经叛道吗?对此,我想暂时屏蔽一个常用的概念:“非理性”。我从来不认为登翰书法是一种“非理性”的冲动。事实上,在笔和墨的上方,时刻高悬一双有着充分的艺术感觉和艺术自觉的眼睛。无论是以水画墨的大幅,还是以墨赋形的行书笔意,在线条的狂放流动中,都形成缤纷殊异的墨象。他最近书写的一幅竖式长卷,让人看到如同一枚叶子在风中盘旋地落下的轨迹,这些轨迹的来龙去脉无迹可求,具有传统绘画的丰富墨韵在书法线条上舞蹈的感觉。对此,我愿意猜想,这可能就是一种妙手偶得,或许可以说是一种回归原型。
原型是埋藏在世俗的日常经验背后的东西,是无声无息的。当我们的视野风平浪静的时候,登翰书法出场了,那些有点奇异的墨象,突如其来地暴露出一个“幽深的渊薮”,令人震撼。然而,我必须负责地重返这个尖锐的问题——墨象的意义。无可否认,以墨为象的书法美学观念,一定是登翰胸中的千山万水。他已经在自身的意义区域里,形成了自己的书法语言风格和感悟世界。在那里,森林有可能是一片流水潺潺,修竹有可能是丰腴多姿的,山峰有可能是混沌妖魅的……如此丰富的笔墨意象,就像古老的神话传说中那个一半是美女、一半是鸟或者鱼的形象,其中所包含的奇诡的魔力,已经颠覆了我们对于自然的一如既往的想象方式。
所以说,登翰书法既是视觉的,也是思想的。
2015.3.9
二、贤谋画石
多年前,我写过一篇《贤谋玩水》。其实,有许多画家我是不敢触碰的,因为他们太过于“正”。而对于花鸟画名家曾贤谋,我却有些忍不住。贤谋很早就对我说,画画属于雅玩。在雅玩之中蕴含一些生命的内容,无论花草,还是鸟兽,无论水,还是石头——这,就是贤谋的绘画之道。
这就说到石头了。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句话一直被人津津乐道。石头是宁静的,但又是令人敬畏的,它表达了世界的一种感动。在我的感觉里,画家钟情于石头,必定有灵性上的相互映照:因为恒定,因为稳重,更是因为某种意义而来。生命存在的意义是“严重”的,石头存在的意义也是“严重”的。画家就是这个“严重”的世界的“特别的在场”,他们所有经验生命的方式,就是在物象世界里寄寓了“自己的思想”。这样,即使是一块沉寂的石头,它也是最热烈的,借用一句话来说,就是“静谧的激情”。
中国历代画石的画家大有人在,从徐渭、黄宾虹到潘天寿,都是画石的高手。石头在花鸟画中的出现,一方面起到了稳定画面的作用,另一方面调节了画面的墨色,使画面的节奏感和韵律感有一种飞跃的律动。潘天寿以石头为基础构建他的画面,就是充分利用石头的空间造型,形成独特的语言形式,从而被誉为“潘公石”——我想,这是属于潘天寿的美学形式。
贤谋呢?“绘画是快乐的游戏”——这是贤谋所向往的一种“玩石”的境界,我想这样可能更符合他的本意。贤谋“玩石”的目的不在于别的,而在于某种诗境和意义区域。置身于他的石头画作品面前,我深感骇异——无论是危岩奇崛,还是枯石奔突,无论是行走的笔势,还是率性的泼墨,那些石头都以一种惊人的活跃告诉人们,石头之形一定包含了某种强烈的表述欲望。
从作品的实际来看,写意花鸟画与山水画中石头的画法可能有所不同。前者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存在,所占的分量有时很重,而后者往往作为单元局部出现,去配合画面的整体感觉。古代画家讲“石分三面”,在于为了表现石头的总体实感。或以浓墨勾皴,绘出大形,甚至可以将石头根部虚写;或以大笔蘸墨,顺势皴擦,显露石头的质感;或在转折处点苔,使得笔墨有些变化。
贤谋以往的花鸟画也配以石头,但基本上出于烘托画面的整体气氛和稳重感。近来他独以石头入画,其中一部分为太湖石,着力表现太湖石“瘦”“漏”“透”“皱”的质感特点。在技法上焦墨与泼墨并用,中锋与侧锋互渗,皴擦与点苔结合,将太湖石的洞窍性特征点染出来。
从绘画的本源性来看,贤谋画石并无过于强烈的技艺上的变轨,其画面结构依然是勾画凝重、顿挫分明的,然而令人产生兴趣的还是跃动。跃动与书法腾挪一样,都是形式感的表现,这种形式感是如何进入贤谋画石的感觉世界呢?在我看来,贤谋对于笔势的一再追求,如同春山里那些正在萌发绿意的苔石那样,蕴含着变化无尽的生命消息,其最终要诉诸的,还是墨韵的一种意象赋形。贤谋的艺术策略就在于,他只凭借自己的艺术感觉,以“玩水”不羁的技法优势,将皴擦氤氲出一种强烈的隐喻效果。
贤谋画石不属于“非理性”的即兴表演,他的奇崛之处,在于穿刺般地攫取自然界石头的内在秘密。无论是大幅泼墨,还是皴擦笔意,他在对石头外形线条的渲染中,都以一种具象的墨象落下笔触的轨迹。我们无须去追寻这些轨迹的来龙去脉,便可以感受到那种丰富的墨韵在画面上舞蹈的感觉。妙手偶得也好,回归原型也罢,对此,我都愿意以一种属于贤谋的意义区域去猜想。在这里,我可能过多地从哲学层面上阐释贤谋画石的空间意义,但我必须从这个类似“幽深的渊薮”,负责地重返一个重要的问题——石头的意象。无论如何,石头的原型是埋藏在日常经验里的东西,而在贤谋眼里,它们就是千山万水,就是自然的风暴。毋庸置疑,贤谋已经在自身的意义区域里,形成了自己对于石头的感悟世界。其丰富的笔墨意象、奇诡的精神魅力,似乎已经颠覆了我们对于石头的一如既往的想象方式。
所以,倘若简单地以“象征”“想象”等概念,去表述贤谋笔下那些石头墨象,估计难以泅渡到美学意义的彼岸。贤谋画石表征了一位画家独特的审美观,以及某种逆行的象征性姿态。中国画的精神魅力在于一种水墨感悟,无论用墨还是用水,画家都必须将笔墨意象转化为天姿卓绝,同时需要有灵动甚至诡异。贤谋笔下的石头多具无穷的变幻方向,但绝非那种一般性的形而上学冲动,造型的无羁可能是贤谋画石的强烈的主体意识。所有石头的造型都可能在他笔下出没,无论浓淡枯润,都尽力显示出某种异趣。因此,我似乎更愿意如此想象:贤谋画石的那些以种种墨韵造就的幻象,随时可能涌动出他与石头对话的姿态。这样,他笔下的石头就不仅仅是自然意义上的石头了,或许是高天滚滚的一声惊雷,或许是奔流到海的一个漩涡。一位纵横恣意的画家给予我们的,一定是不同寻常的独特气场。贤谋并不离经叛道,他依然匍匐在中国画的原点,以一双高悬着的充满艺术自觉的眼睛,进入他的石头画的感觉世界。
可以肯定,贤谋画石是一种寄存于内心的艺术,无始无终,却有大山般的恒定。
2019.1.9
三、吴信的画
站在吴信的中国画作品面前,一切都渐渐明朗。我确乎不能无动于衷。一个庄子用过的词——目击道存,已经足够表达我的感觉。
但我似乎还在追索那里面隐藏着的笔墨的全部姿态。这些姿态被囚禁在画作的肌理中,它们的终极命题是什么呢?
每一位画家都是独立的个体,相同的笔墨与相异的观念,就会产生画家们各不相同的活跃及表述的欲望。吴信如何?他的笔墨可能不止于“文人画”——宁静与奔放、内敛与张扬、收纳与勃发,这些使得他笔下腾挪的,无论拔地而起,还是奔窜腾跃,无论婆娑起舞,还是迎风长啸,都在验证着自然和日常的精髓。在他眼里,所有的山水、花鸟、人物的姿态均已潜藏于日常之中,他的任务除了绘就,又不止于绘就——这可能就是画家的意图。
尽管如此,也不要试图从吴信的画作里寻找到太多的象征、隐喻或者寓言,我目光所及的那些作品,具象的此岸很快就可以泅渡到意义的彼岸——因为它们简约而明朗,一切源于师法自然,但一切又不止于师法自然,它们的主体没有被完全搁置起来。那么这个主体是什么呢?
吴信说他是“亦道亦儒亦佛”的。他16 岁拜国画大师李耕的高足周秀廷为师,在莆田县巷蛰居了20 多年,潜心习画。对于他的运墨、用水、皴染、点擦等技巧,本来就是一个“道可道,非常道”的问题,不需要过多地用繁复的理论或叠床架屋的概念去辩难,因为那样必定会诱惑艺术家远离自然。画家就是画家,他的所有技巧都在他的生命力之中,无论崇儒、礼佛还是信道,都可以将他想象为一个象征性姿态,而不必在乎他怎么画、画出什么。在他笔下,袅袅轻烟、树丛、云团、水流、人影,甚至一枚在风中盘旋落下的叶子,都是他的意义区域。
数月前,我在莆田跟吴信有一次交集,并参观了他的工作室。交谈之中,才知道他的老家离我老家仅一箭之遥。他那副酷似弘一法师的模样,让我看到一种返璞归真的意义。他一定是虔诚的——至少,我们没有必要去想象,他遵循的那些“道”是神秘而高超的,因为这里没有什么运行在遥远天际的东西。等待画家顶礼膜拜的,依然是那些不同寻常的日常。
自然始终停留在画家手边——这个观念一直被作为评判一位画家的积极因素。然而,我积极地谈论吴信的原因,却在于他的作品颠覆了艺术家对于自然一如既往的想象方式。
一位成熟的画家,有属于他自己的稳定的表意语言。胸中贮藏了千山万水,才能在纸上呼风唤雨。吴信无疑是一位积极的孜孜以求的画家,他在实现自己的主题及风格的语言符号过程中,已经将稳定的表意语言化为主体的意识,并合理地组织于他笔下的意义区域。在他那里,山峰是俊俏的,石头是柔软的,水流是缓慢的,花草是随风的,老树是伤感的,枯枝是怀念的,人物是佛性的……这些无不浸透了他埋藏在世俗日常经验背后的渊薮,我甚至由此想到了八大山人的残山剩水。
所以,我对吴信画作的理解,没有清除他的主体的一切痕迹,我所期待的还是那个被主体意识覆盖了的“现实主义”风格。“自然的再现”或是“如何再现自然”——一直是让画家深感纠结的难题。在吴信笔下,我能看到的是那种“山隐藏在山里”“水消失在水中”的景象。或许,还可以用“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去提撕他的作品。但我以为,艺术家对于“道”所表现出来的特殊的迷恋,至少有助于熄灭种种形而上学的冲动。这样,他就获得了一种自由和自如的创作心态。
吴信的山水大都笔墨雄浑,而那些写意小品则趋于节制。无论大制,还是小品,他都把握住一个准绳:顺道而为。“尘不染尘,水不洗水”,他没有勒紧主体想象的缰绳,从而使得那些匍匐在大自然面前的生命的样式,在再度返回自然的途中依然被想象力还原——树还是树,但却是另一棵树了。这里面没有赤裸的哲学花边,而只有被“顺道而为”的主体想象呼唤出来的一片天机纵横。
我曾经和莆田的一位诗人萧然讨论过吴信的作品。萧然觉得吴信确立了“文人画”格局,在某种程度上又突破了“文人画”格局——这个观念颇有意思。吴信突破“文人画”的格局,在于有效地克服了“文人画”的某些缺陷。然而,如我前面所述,吴信的笔墨不止于“文人画”,“亦道亦儒亦佛”的观念使得他撬开了主体意识的大门,从而有了一种不同寻常的表意风格。必须承认,我们今天对于自然的感受较之古人逊色了许多,其原因之一就是缺乏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主体性介入,陶渊明的所思即是他的所见,感觉即是理性。所以我觉得,无论是“率性而行”,还是“适情而止”,吴信都没有放弃他的主体意识。真正的“顺道而为”的观念,不是被动的行为,而是如同里尔克所说:“接住自己抛出的东西只是工匠之技,真正的艺术家必须接住命运女神抛出的东西。”那么,吴信接住了吗?
“才想无一物,尘埃即已现。”吴信就是吴信,他没有冒失登场,而是以他的姿势接住了他该接住的东西,继续他的长途跋涉。
2021.1 1.25
四、鉴赏家的表情——序沈英艺《艺苑集珍》
我时常被鉴赏家所折服,觉得他们能够像巫师阐释世界那样,对一件艺术品品头论足、娓娓道来,指出其真假优劣。目击道存——庄子用过的这个词,大概可以用来形容鉴赏家的表情,因为我对他们的见解的震惊始终始于所有艺术术语之前。
这里要提到的是沈英艺先生。英艺长期服役于军队新闻单位,自20 世纪80 年代初开始热衷于书画收藏和鉴赏。90 年代初,在曾贤谋的画室里我结识了英艺,得知他是福建诏安人。
诏安历史上书画之风炽盛,源远流长,素有“书画之乡”之称。唐代以来,丹青耀眼,翰墨飘香,名家佳作层出不穷,至明代已达鼎盛时期。特别是清代,著名画家沈锦洲及其弟子开创了“诏安画派”,使诏安书画以其独特的风格屹立于中国书画艺术之林,代表性书画家有康瑞、沈大成、沈瑶池、谢琯樵、沈攸、沈丹青、沈宝善等,现代则有沈福文、沈耀初、沈锡纯、沈柔坚等。这些人物的全部姿态,就是以惊人的灵动与活跃在风中飞扬。
英艺自小熏染于诏安浓厚的书画氛围中,他以主体的全部介入,去感受运行在遥远天际的书画之“道”——“道可道,非常道”——对于这样一位鉴赏家来说,他的象征性姿态不在于他说过什么,而在于他专注聆听的是来自艺术内部的声音。
由此,我对于“沈英艺”这个名字有了莫大的兴趣。“沈”——一个字就足以代表诏安画派的所有精髓,“英艺”两个字则无需多说。每每和他交流书画艺术时,他总是两眼放光,脸上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表情:时而奔走踊跃,时而凝重如山。话语之间,时而细若游丝,时而波澜激越,犹如墨迹浓淡枯腴,运笔顿挫缓急。我和英艺的交集,就像一个熟稔的老友不由分说地闯了进去,用一个艺术术语说来就是——“不隔”。
20 世纪90 年代,我有一些机会在曾贤谋的画室里看画家作画,听艺术评论家鉴艺品评。这其中就有英艺。在众多鉴赏家中,英艺的表情最为丰富,时而蹙眉沉思,不轻易发表见解;时而拍手叫好,禁不住为一幅精品力作称快。他虽出身行伍,却有细说的本事,对于作品的每一个细节都有见解,比如墨晕应该染在何处,笔锋当从哪里逸出,等等。
英艺多才多艺,收藏、鉴赏字画之余,兼写笔墨。书画创作就是一种“纸上的江湖”,那里有平平仄仄的笔墨风月;而鉴赏则是“别有池塘一种幽”,其中隐含了必要的美学经验。如果说书画艺术家的创作擅长呼风唤雨,那么鉴赏家的胸中一定是贮藏了千山万水。这一切都表明他们各有自己实现的目标:创作的主题和鉴赏的经验。
艺术鉴赏属于接受美学,需要有相当的艺术启悟。英艺的启悟在哪里呢?就在于他意识到书画艺术的另一个谱系——并非肥马轻裘,浮靡炫耀,而是修身养性,清风遣怀。在这里,没有什么高大上的“宇宙大道”,只有“把酒话桑麻”的日常气息。倘若借用《诗经》里的一句诗来说,就是“彼泽之陂,有蒲与荷”。鉴赏家的全部奥秘,其实就在这里。
艺术是有生命的。在一位富有艺术经验的鉴赏家眼里,书画家的主体观念、作品的内容与艺术形式这三者之间,究竟实现了怎样的隐秘交汇——这一定是一个有趣而又难以回避的思考线路。为什么那些作品会打动他——因为它们在一个特别的意义区域里,表现了艺术家异乎寻常的对于自然一如既往的想象方式。这种想象方式既是视觉的,也是思想的。
于是,我在英艺这一册《艺苑集珍》里,看到他所读解的书画作品内在的来龙去脉以及有迹可循,也看到一位鉴赏家的文化体验和精神维度。这本“集珍”谈及作者长达半个世纪的艺术收藏经历,鉴介了80 件书画作品,涉及福建近现代的林则徐、沈葆桢、严复、萨镇冰、林纾、陈衍、何振岱、陈子奋、沈耀初、宋省予、沈柔坚、李耕、郑乃珖、罗丹、潘主兰、杨启舆、曾贤谋等的作品,横跨近二百年的历史,提供了福建近代书画文脉的一些重要侧面。作者以带着生命体温的艺术笔触,讲述了那些动人亦动情的故事,有些甚至是鲜为人知的。他对于林则徐“重镇风清开四扇,崇朝云起岳三峰”对联“三胞胎”的鉴识,对于陈子奋作品失之交臂、失而复得的孜孜不倦的寻求,对于林纾《王琳练剑图》的赏读,对于李霞《麻姑献寿》揽出的艺誉的赞赏,对于谢琯樵墨竹《筛风弄月》静候30 年终于到手的收藏经历,等等,都隐含着变化莫测的收藏、鉴赏轨迹。那些隐藏其中的奇闻轶事,对于多数人的知识图谱和艺术想象是一种莫大的精神滋养。因为它们包含着强烈的表述欲望和美学传统,每一件作品都隐藏着幽深的艺术渊薮。
鉴赏家的表情代表了艺术品鉴和收藏的语言谱系。尤其是收藏,怀揣着一点蛛丝马迹,带着一线希望,走街串巷,等到一扇门“吱呀”打开了,步入某一位书画家或藏者家中,苦口婆心,巧舌如簧,直至搔首弄姿,摸一摸口袋里还差着一些银两,不禁倒抽一口冷气,胸中有不尽之意;但痴心不改,无怨无悔,一而再再而三地奔赴,直至凯旋,那种情景如同“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开怀。所以说,鉴赏和收藏就是一个放置心情的空间,那些快乐不减的操作,丝毫不亚于立地成佛的神往。
作为鉴赏家,英艺对于艺术家具有一种无比深厚的亦师亦友的尊重,其间蕴含着珍贵的超凡脱俗的情感。他视罗丹为“忘年交”,每年元宵节,家中客厅一定要挂上罗丹书写的《送友人》,借以表达一份深情和一种无法忘却的纪念。他带着老乡画家沈锡纯的便条去拜见潘主兰,潘先生居然对他说:“我们也熟嘛,不用沈老写介绍信。”随后他递上一对只花十块钱买的石章,请潘老篆刻,潘老一口应允。他1978 年就认识曾贤谋,我是1992 年才认识这位大画家,于是曾先生就成为我们共同的朋友,我们都为他的卓绝的水墨技巧所击掌。
英艺对于艺术品的痴迷,如同德国诗人里尔克所说的,“接住命运女神抛出的东西”。无论如何,这是一种特殊的迷恋。在许多作品面前,英艺看到的,不止是一条游鱼,一枝黄玫瑰或者一座紫薇中的小院,重要的是他看出了艺术的不同寻常——这就是“道”。命运女神的眷顾,让他具有一种特别的“爱”——这种爱的表情,不仅散发在他所钟意的艺术作品中,而且深深地烙印在他那刻骨铭心的女儿身上。
在不久前的一个场合,我见到了英艺的女儿。20 年不见,她活脱脱地长成了一个大姑娘。我想起当年见到她时,还只是个四五岁的小女孩。那天,英艺买了个不知是变形金刚还是类似今天的乐高积木的玩具,摆弄了半天,就是拼不起来,女儿急得大叫。英艺无奈,一直看着女儿哭闹,嘴里不住嘟哝着:“这该咋办,咋办呢?”他的脸上却挂满着欣赏的表情。我知道他深爱女儿,把女儿当作他最得意的作品、最永恒的经典,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他心目中最稳定的表意语言。女儿终究是他心灵深处的奇特精灵。玩具始终没有拼起来,女儿的阵阵哭喊却成为他的恣意纵横的笔墨点点。无论是女儿,还是艺术品,就像大地和凡·高的太阳,都是充满着不可遏止的生活激情——这就是英艺,爱艺术更爱女儿的英艺。
英艺是坚守的。从此以后,他要继续面对一件件熟悉的或陌生的作品,这个既有的表情和意义区域依然是属于他的,并且具有了相对稳定的艺术秩序。当然,艺术的发展空间是层出不穷的,并且在不断地产生新的秘密。如何持续地承传鉴赏和收藏艺术水平,无疑将具有许多偶然和随机的艺术转向,这不是随意可以预料到的。不管英艺的艺术鉴赏和收藏的意义区域的版图将如何变化,我愿意相信,他已经取得的那些成功,将成为他有效地提升鉴赏和收藏水平的一个不竭的动力。
是为序。
2022.1 2.16
五、卢清“玩线”
卢清是个杂家,玩法很多。玩速写,玩插图,玩名片设计,玩现代挂盘,还玩黑板报,玩幽默笑话。他最得意的应该是玩线描艺术——我称之为“玩线”。
多年前,卢清送我一册《名片设计精品500例》,被一家伙借去,他拿着这本书去名片店,要求照瓢画葫芦印制一名片。名片送来了,他的“顾问”头衔被印成“顾门”,一通电话过去,说少了一个“口”。老板答应重印,第二次送来时,他差点气背过去——“口”倒是加上了,却变成了“顾门口”。
数日前,在“卢清线描精品展”即将撤展之际,我匆匆赶去观摩。目击道存——我的感觉逐渐活跃,囚禁在线条深处的那些精灵都被解放出来。一根纤细的线,呼啸刮过的是什么风,能把一堆意象勾勒出来?
让我深感骇异的,还是那些奔窜腾跃、婆娑起舞的线条。全部的奔放、勃发、张扬与热烈,不止是一根奇特的曲线,而是惊人的活跃,以及蕴含在这些活跃里的表述欲望。
将卢清简单地视为线条的“造物主”,显然是把主体想象的缰绳勒得太紧。在卢清的感觉里,所有在风中飞扬的姿态均已潜藏于线条之中,他的任务不过是把它们显示出来,他的操作无非“抽象”而已——将他的视界匍匐在想象力面前,在那些团团转转、层层叠叠、盘丝缠绕的纹理中,破壁出一条神奇的曲线和这条曲线所构造的生命秩序。
卢清的创作是否可以暂时屏蔽一个常用的概念——“非理性”?那些流淌的、变幻的线条书写刺穿了“元宇宙”的秘密,线条在不停地荡漾,影子般轻盈地飘过。有时候,我盯住其中的某段线条,跟随着千回百转的曲线,一片天机纵横的感觉飘拂,如同一茎风中的稗草翻卷回旋,突然就打乱了我原有的知识图谱。
我感觉卢清是在“玩线”了。它们为什么能打动我?仅仅用“妙不可言”四个字去形容,我总觉得有些不够。那些线条的存在看起来是随机的,也没有什么理由,一会儿是袅袅轻烟,一会儿是云团、海岸线、河流、螺旋、木纹,以及伸缩的火苗,一枚叶子在风中盘旋落下的轨迹……其实它们就是自然万物,就是日常,就是我们眼里的“道”和“器”,就是我们的“绝对精神”——这是卢清的“感觉”和“理性”,它们和谐而单纯,明朗而具有天真无邪的特性。
卢清的线描作品单纯到极致,丝丝入扣。“线”的本原在于“描”,在于以春蚕吐丝般的线条表达符号的象征,在于用天姿卓绝的曲线创造流逸宛转的图像体系。在卢清笔下,那些线条结构犹如稳定的表意语言,呼风唤雨,胸中所贮藏的千山万水,实现了属于自己的主题。在这里,隐藏在各种意义区域里的线条结像,已经妥帖地组织于人类幽深的渊薮。
卢清“玩线”,尺幅都不算大,然而那里面有象征,有隐喻和寓言,还有那些“道可道,非常道”“恍兮惚兮”的艺术架构及神秘的幻象。看完展览,我觉得卢清那些绵延不断的线条,已经使他陷入一种孤独的深渊之境。卢清说:“我这些画都是由成千上万的线条组成,笔随心智,心随线走,常是一气呵成。”线条的无止境的组合,让我看到的是一种对话的姿态:时而可以将人们从线与线之间的牵连中吊起,去感受一场艰难的视觉突围;时而可以将人们在一道门与另一道门之间穿越,穿刺般地攫取生活日常的秘密。线条的组织流畅与否,取决于他的艺术语言之中每一个精神符号的绵延。所以说,卢清的创作不属于即兴表演,他可以千姿百态,但一定是深度模式。
艺术家总是在一天一天地成熟,由此形成了一种交替的双重带动的“元叙述”体系——历史的叙述与叙述的历史。卢清的线描艺术并非一种时髦的活跃的画类,但他肯定是用一批极其活跃的线条,敞开了一种历史叙述的空间。那些一如既往的想象方式,大多数以山川草木或花鸟鱼虫作为主要素材。质而言之,他不是完全虚拟的,而是努力将自然景象始终停留在手边,从而了然于心——这也正是我积极谈论卢清线描艺术的原因。
无论是清晰的具象,还是混沌的抽象,卢清线描的构图没有什么固定的条律,在灵动和诡异的线条走墨中,隐含了无穷的变幻方向,无迹可求,甚至消弭于无形——我猜想,这就是卢清线描艺术奇诡的魔力。
解读卢清线描艺术的入口在哪里呢?倘若用某种稳定的标识或定型的准则去框定卢清,可能无法聆听到卢清线描艺术的神秘的回响。那些也许是我们所熟悉的景象,在卢清笔下并不是冒冒失失地登场的。在这里,我愿意接受的解释是,卢清笔下那些奇幻的曲线随时可以摧毁任何定位的参照物,并且随时可以颠覆既有的传统秩序,他的线描作品已经顽强地说出自然和生活日常的另一些秘密——这可能是我们理解卢清线描艺术的一个重要入口。
我认识卢清已有多年,其间交集并不多,但我时常会关注到他的一些纸面的笔墨。有时我以为,他的随和、随性的性格与他那些桀骜不驯的创作个性并不相容或者相通,然而正是这种表面上的不兼容,引爆了他独特的内心境遇和美学经验,完成一根线条所组织出来的艺术品相,由此形成一种和谐共生。
用一个“玩”字去解释卢清的线描艺术,也许言不达意,但我愿意相信:卢清“玩”的不是心跳,他对于线描的“把玩”,完全出自他的美学理念。一根自始至终、从一而终的线条,不间断地牵引着笔墨,形成了成千上万的线条组织,走向作品的内核。一根线的完成可以延续数个小时,并且线条的粗细一致,线与线的间距也是一致的。我曾经告诉卢清,他的线描具有一种极强的包围感,而且具有鲜明的主体意志。作品中的石头,不仅仅是一块石头,而是由一根线包围着的石头的纹理;一棵树不仅仅是一棵树,而是由一根线缠绕着的树的枝干;一条鱼也不仅仅是一条鱼,而是由一根线镶嵌着的鱼的形体或者骨架。
一根线条,从卢清的视野之中自然而然地滑了出去,他笔下的艺术书写和历史叙述从此也拐入另一辙的艺术冲动。此刻,我们是将他想象为一个逆行的象征性姿态,还是被他“玩”的那一根线继续牢牢牵绊住了呢?
2023.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