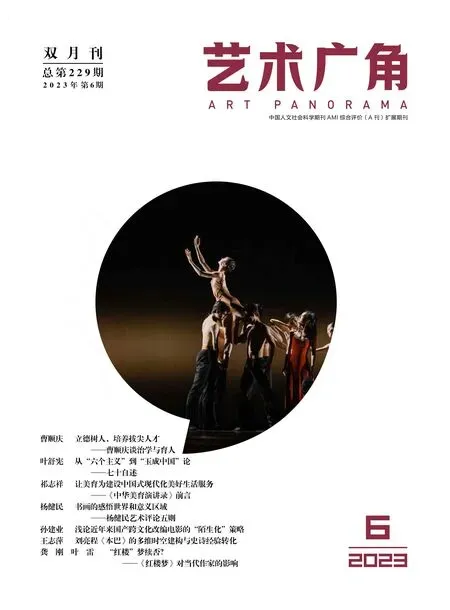刘亮程《本巴》的多维时空建构与史诗经验转化
王志萍
史诗是人类古老的文学样式,即钟敬文先生所说的“是民间叙事体长诗中一种规模比较宏大的古老作品”[1]钟敬文:《民间文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版,第204 页。。众所周知,《荷马史诗》是西方叙事文学的源头,在精神内容、人物塑造、叙事结构和艺术手法等各方面均给后世带来深刻影响,成为西方文学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在我国的文学传统中,汉民族的叙事诗并不发达,但是少数民族却有着丰富的史诗资源,最著名的当然是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另外还有像苗族的《亚鲁王》、壮族的《莫一大王》,等等。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各民族的史诗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但是将这些史诗的叙事经验转化为当代文学创作资源的努力才刚刚开始。
流传于新疆阿尔泰山一带的卫拉特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由数十部长诗构成,在“并列复合”[2]〔荷兰〕米尼克·希珀:《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史诗与英雄》,尹虎彬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9 页。的情节结构中,描绘了一个万古长青的理想国宝木巴,张扬着强悍的英雄主义精神。著名散文家刘亮程2022 年1 月出版的新作长篇小说《本巴》[3]刘亮程:《本巴》,译林出版社,2022 年版。本文所有原著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一一注明。取材于《江格尔》,却以诡谲的想象完全改写了《江格尔》的英雄故事,“在古人想象停驻的地方往前展开作家自己无边无际的冥想”[4]黄茜:《刘亮程谈〈本巴〉:在史诗中寻找心灵往事》,《南方都市报》2022 年4 月24 日。,以梦呓的方式,将读者带到一个超验的多维时空。《本巴》没有拘泥于史诗故事框架,而是将史诗作为精神和艺术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为当代文学探求新的发展道路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
一、多维时空的建构
前现代时期的史诗《江格尔》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创作并流传,由数十部作品集合而成,并没有一以贯之的时间线索和情节线索,但每一部作品的故事有着各自的叙事完整性。在这些故事的说唱过程中,民族远古时代的生存经验和历史记忆得以存续。刘亮程创作《本巴》,以他“乡村哲学家”的思维方式创造了一个交织着历史与现实、梦里与梦外、经验与超验的自足世界。如果说作家之前的小说《虚土》是“受俄罗斯套娃的启发”来结构全书[1]姜广平:《我不慌不忙地叙述着人类久违的自然生存——与刘亮程对话》,《莽原》2011 年第2 期。,那么《本巴》更像受到了现代物理学多维空间概念的影响,在不断曲折变形的时空维度中将读者带入到一个令人眩晕的世界。
小说第三章第三节《做梦》写到人物之间多层次的梦与被梦的关系:在第一层面(拉玛国的日常生活),贾登嫉妒阔登比自己力气大,妻子漂亮,牛羊多;第二层面(贾登的梦),阔登被贾登雇用,阔登的妻子和牛羊都属于贾登;第三层面(巴登的梦),贾登为巴登做梦,为巴登微笑和幸福;在第四层面(哈日王的梦):所有人都在“一个单调白天和一个枯燥黑夜里,玩做梦梦游戏”;在第五个层面(小说的主叙事层),上述各层的人和事都发生在齐的说唱之中。所有这些层面的事件是共时发生的,但这五个层面的故事并不是俄罗斯套娃式的简单嵌套。在齐说唱的故事中觉悟过来的史诗人物赫兰穿梭于各层之间,就像多维空间中的绝对隐身,三维空间中的人是无法看到他的。他的线性时间将五层事件的平行时空串在一起,使各层之间不再有缝隙,层层叠叠的故事连缀成浑然一体的小宇宙,由此展示了世界的无限复杂性与可能性。
刘亮程说:“我想在《本巴》中把时间作为一个本质,而非手段去写,写出时间的面貌。”[2]何冬健:《刘亮程长篇〈本巴〉面世》,《浙江日报》2022 年3 月4 日。时间是人类所能感知的四维世界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维度。正常情形下,时间就是一条从小到大,从生到死,只能顺序前进,不能停止和倒退的线性轴。然而小说中的时间显然不是这样一条轴线。[3]王晴飞:《把重的事往轻里说——刘亮程的〈本巴〉》,《当代作家评论》2022 年第3 期。本文注意到《本巴》中的时间与现代科学中“单向,匀速,抽象”的时间观念的不同。
它可以跳跃快进:摔跤手萨布尔“两天走完二十年的路”。赫兰把盘在身上的守边老人的百岁光阴抛向锁住洪古尔的脚链颈链,铁链便瞬间老化锈蚀而断。洪古尔喝下熬制多年的奶茶,就转瞬由幼童跨越从未经历的青年直达老年。老年洪古尔的一壶奶茶,就能让季节急速流转,改换无数天日。二十五岁的阿盖夫人在喝下老年洪古尔递来的奶茶后,眨眼功夫就变成了老夫人。本巴草原的女人们在阿盖说出“活在老年”这句话的时候,就开始纷纷变老。
它可以堆积停滞:整个本巴国“一年年的时间摞在眼前,顶到了天”。先出生三十年的策吉在二十五岁的时间上等待与江格尔和众勇士们相聚。大肚英雄贡布“已经在二十五岁里待了七年”。洪古尔因为恋乳一直留在幼年。哈日王因为恐惧而长久留在母腹。守边老人的夫人把七十年的光阴都煮在一碗酽茶里。草原上的牛粪、羊粪、马粪可以压住时间,草丛、树林、远山可以藏住时间。
它也可以折叠倒转:江格尔“隔着十三年的距离”拉住阿盖夫人的手。摔跤手萨布尔在二十三岁时还能“掉转身跑回到童年,把小时候赢了他的一个伙伴摔倒,扔出去七年远”。每个人都能在搬家家游戏中重返童年。忽闪带领的莽古斯大军跟着年幼的赫兰来到年老的洪古尔面前,错过了二十五岁的青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要在童年和老年间来回地奔走,想寻找到自己二十五岁的青春”。
上述时间的种种特性,只有在四维以上的高维度时空中才能实现。四维时空中时间的维度让人类生存的静态三维空间走向动态,但时间依然是与空间有着不同度量方式的线性向前的维度。刘亮程却努力以空间的度量方式来描述时间,使其具有与长宽高三个维度同等的价值。《本巴》一开篇就让时间呈现出空间形式,人们以空间中的行走方式穿行在时间里:策吉“每日站在班布来宫殿的瞭望塔上,往几十年远的路程上眺望”;老谋士能够“看见三年远的路上、五年八年远的路上,扬起冲天尘土,四面八方的烟尘在朝本巴围拢过来”。甚至赫兰能把拉玛国守边老人的岁数像盘绳子一样盘起来带在身上。时间的长度被以空间的远近来计量,最后我们看到,英雄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分别呈现于日日宴饮的班布来宫、冰天雪地的茫茫归途和雕像耸立的广场,时间凝固于空间中,成为象征性的存在。
与时间的空间化互为犄角的是空间的时间化。《本巴》第一章,洪古尔出征来到两国交界处,拉玛国守边老人为了向他渲染拉玛汗国王宫之大,先介绍自己这样一个最贫穷的放羊老汉的毡房:
你问我的毡房有多大?告诉你,掀开外三层里三层的绣花门帘,就得花三年。迈过老桦木的门槛又得三年。从门口到中间的炕桌,骑马要走三七二十一年。爬上炕得三年,步行走到炕桌边得四七二十八年,手伸到茶壶边得三年,端起壶边的茶碗又三年。
这里完全没有大家通常所用到的公里、里、米、尺、寸这样一些长度单位,用以丈量空间距离的是时间。60 多年的时间能够走过的路程有多长,我们还能够想象,但是,对近在咫尺的老牧羊人,洪古尔举刀砍下却要用七七四十九年,以至于举起落下间,他的金刚石宝刀就“锈成碎片,连镶嵌黄金宝石的刀柄,也在手里腐朽成一把灰”。这里的空间与时间完全错叠在一起,读者只能无限延伸自己的想象力,在一个卷成筒状的高维度世界才能理解它。正是因为空间距离不是三维世界里线性的距离,路程的长短转变成时间的远近,所有的人和事好像并非从空间中,而是从时间中走来。在《本巴》的世界里,空间如同时间一样,也是可以高度压缩的。再远的距离都可以被压缩到洪古尔和赫兰的一个念头之间,甚至整个二十五岁的本巴国也只是江格尔的一个想法,哈日王更能穿越梦境和历史,把自己的游戏讲入史诗。仍然借用多维时空的量子物理模型推论,洪古尔、赫兰、江格尔、哈日王都有依靠“时空虫洞”“抄近道”的本领。时空瞬移在科学家那里被认为是“数学伎俩”[1]韩秉宸:《“虫洞”假设的意义》,《人民日报》2015 年3 月20 日。,在刘亮程这里却成为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文学想象。
当读者在多维时空的叙事迷宫中艰难索解之际,刘亮程笔锋一转,让赫兰带领大家进入柳暗花明的当下——一个充满现代气息的新的“本巴”:“这里的游牧转场早停了,已经没有人放牧,牧民都定居在村庄里。”骏马背载盛满水的宝瓶在草原飞驰只是游戏,班布来宫矗立在广场上,众勇士成了凝固不动的冰凉雕塑,哈日王转世成为说唱者齐,《江格尔》还在代代传唱,江格尔小学传承着英雄的史诗。本巴宿敌哈日王如今成为说唱东归史事的哈日齐,虚构的史诗借由装扮12 英雄的12 勇士与东归的历史事迹联为一体,又借由说唱中的疼痛体验将当下与死去的先人联系到一起,再次实现了想象时空与现实时空、历史时空与当下时空的并置。
根据科学家的推论,五维时空中就会出现无数条时间线,四维时空中的任何一点出发都会生发出无限种趋势。在更高维度的时空中,通过上一维度时空的折叠,时间就会像空间一样缩短、延长、扭转、往复。如果以多维时空的概念阅读《本巴》故事,小说中洪古尔在出生前就看到过如今在拉玛国守边的老人,又能用搬家家游戏把现世的老人送回到童年;前世的花脸公蛇和母蛇可以轮回到现世再续姻缘,而前世与今世拯救或侵犯本巴的英雄赫兰和莽古斯哈日王却在来世变身为史诗说唱人齐——凡此种种,就都不难理解了。因为在高维度的时空中,人或蛇,都理所当然可以看到过去、现在、未来的自己。点与点、线与线、面与面的立体化相交方式,使世界在时空的折叠交错中不断生成新的维度。刘亮程成功地在各种时空的交错中拓展了文学的想象空间和所能表达的哲学内蕴。
二、史诗经验的转化
中国新文学自五四开始,不断追求“现代性”,西方理论和创作资源的影响超过了本土传统文化的影响。20 世纪90 年代以来,随着文学制度、市场环境、传播媒介等多方面因素的改变,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当代文学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和诱惑,如何找到内在的生长机制,保持其发展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有必要重新回到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文学传统中去,在源头处汲取养料,涵养当代文学新的创作活力。
《本巴》出版之后,受到高度评价。评论家何向阳认为,这部小说就是刘亮程作为当代说唱者“齐”讲给我们的史诗,“他的过往是整个人类天真的、童话的、史诗的、原初的、古典的童年”[1]高丹:《刘亮程〈本巴〉:史诗之外,创生无垠的时间》,澎湃新闻·文化课,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713321,2022 年9 月3 日。。刘亮程因工作之便很早就阅读了《江格尔》并参与相关文化活动,对史诗故事和说唱方式谙熟于胸,自述《本巴》是感受着蒙古族英雄史诗的魅力,试图从《江格尔》出发,创造一部“写给自己的童年史诗”[2]刘亮程、南子:《〈本巴〉是我写给自己的童年史诗》,《新疆日报》2022 年3 月18 日。并“追寻人类逝去的童年”[3]杨雅莲:《长篇小说〈本巴〉追寻人类逝去的童年》,《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2 年9 月7 日。。因此,他对史诗资源的转化利用是自觉的。《本巴》“重返人类童年”带给当代文学创作的启示至少有三个方面。
其一,提升关于当代社会的整体性哲学思辨能力,力求在创作中反映“一种民族精神的全部世界观和客观存在”[4]〔德〕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美学》,寇鹏程编译,重庆出版社,2016 年版,第406 页,第407 页,第410 页。。黑格尔认为,写作史诗的时代,“民族信仰和个人信仰还未分裂,意志和情感也还未分裂”[5]〔德〕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美学》,寇鹏程编译,重庆出版社,2016 年版,第406 页,第407 页,第410 页。,他最为推崇的荷马史诗为后世作品难以企及之处正在于表现了“民族世界观的整体”[6]〔德〕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美学》,寇鹏程编译,重庆出版社,2016 年版,第406 页,第407 页,第410 页。。也就是说,史诗的魅力首先来源于个人与群体圆融一体而形成的精神意识,是对时代与民族本质的整体表现,作品中无我而我即在其中。刘亮程曾有“乡村哲学家”的称号,他的散文作品即在个人、村庄、自然、社会诸层面的浑然交融中表现对人类生存的抽象思考。他所创作的小说《虚土》《捎话》《凿空》,无论是现实题材还是历史题材,总是能够超越具体的人和事,最终达到对历史与现实本质特征和意义的把握。《本巴》更是受史诗文学的启悟,对人类日常生活的繁琐和部族征战的残酷都进行了化繁就简的处理,而对人类生存的时间空间、相互关系、来路归途等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命题进行了深度思考,有对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普遍的精神迷茫和追求的整体性关照。
其二,形成回望传统以探求未来的文化历史视野,在传承和创新中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文学。这里的“传统”当然指包括史诗在内的多民族文学文化传统。当代之所以还需要史诗,首先是因为“史诗有助于我们回顾历史”[1]汪政、晓华:《有关“史诗”的理论务虚——读黑格尔、卢卡契》,《文艺评论》1994 年第3 期。。回顾历史不仅是为了怀旧,而是要站在历史宏阔背景中眺望未来。马克思论及希腊文学和史诗时说:“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着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转引自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下册),春风文艺出版社,1982 年版,第912 页。史诗中所表现出的人类童年时代的纯真天性将不断重复出现在每一个时代,文艺“真实再现”“复活”出这种“固有性格”才能获得“永久的魅力”。《本巴》的故事源出于《江格尔》,却把成人英雄的征战创造性地转化为三个幼童的游戏,既回到人类的童年,也回到个人的童年。个人与世界、我者与他者之间的紧张关系被弱化,史诗时代的“本巴”和现代化的社会之间由一条“牧游之路”联结在一起,民族文化血脉在不断转世的“齐”的语言建构中绵延不息,未来与传统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其三,自觉融汇古典与现代的诗艺追求,建构当代文学的史诗性品格。黑格尔与卢卡契都看到了史诗中抽象本质与感性具体两者完美的交融,即史诗同时蕴含着深刻的整体时代本质、民族精神、人类精神和丰富的具体自然风物、人文景观、民俗风情,他们充分肯定史诗人物性格的深广度和典型性,叙事结构的立体性和多维性,尤其推崇史诗庄严、崇高、壮美的风格气象。因此,从美学意义上讲,每个时代的作家都可以创作属于自己时代的史诗。《本巴》不仅直接植入史诗《江格尔》的片断,而且在叙事上,采用了“梦呓”的方式,使之产生了“齐”说唱传奇故事的艺术效果,同时娴熟运用繁复的现代套层叙事技巧,以超群绝伦的文学想象建构了一个人类无法感知、科学尚在建模的多维时空,不仅在苍茫时空的孤独感中把一个民族的史诗写成了人类的史诗,而且以近乎科幻的笔法写出了未知宇宙的无尽可能性。
刘亮程将《江格尔》中成人英雄的征战转化为《本巴》中洪古尔、赫兰、哈日王三个幼童间的游戏,以最天真的方式书写个体的童年记忆和人类的童年记忆,四两拨千金般地把疼痛、苦难、恐惧、死亡等经验进行淡化处理,在无始无终的内循环密闭时空中颠覆了史诗中的理想家园,以失乐园和虚化现实的方式消弥理想与现实的鸿沟。同时,《本巴》延续了刘亮程所有作品的“精神返乡”主题,在“一个梦里知道去哪,醒来便想不起来在哪”的“故乡”的牵引下,作者在返乡之路的寻觅中从容接受了“人在归途”的宿命,体现出悦纳整个世界的超然旷达的人生态度。
——新一代江格尔奇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