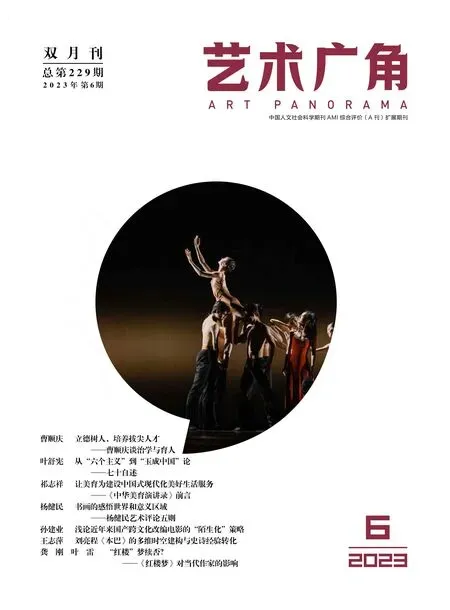唤醒与激荡
——20 世纪20 年代现代设计运动先锋性分析与价值凝练
苏欣 贾效田
一、从观念走向实践:学派、风格与主义
从社会学的经典三段式社会结构“微观—中观—宏观”[1]彭华民、杨心恒:《社会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第43 页。来看,学派、风格与主义贯穿微观本体到中观视角,分别对应以社会组织为核心、以作品为核心和以观念为核心。学派、风格与主义都是现代设计启蒙运动中的核心部分——学派指向社会组织,风格指向作品,主义指向思想,将三者结合能够较好地还原当时的时代风貌。马里内蒂、马列维奇、利西茨基三者在艺术实践上具有连续性的范式转变,由过分激情洋溢的未来主义转向艺术哲学的至上主义,再逐步走向社会实践的叙事实验。他们在维捷布斯克会师[2]〔美〕维克多·马格林:《设计,为乌托邦而奋斗:罗德琴科、利西茨基和莫霍利-纳吉(1917—1946)》,张馥玫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14 页,第5 页。,后来都影响了呼捷玛斯和包豪斯的教学。他们是现代设计的先驱,也是马格林笔下欧洲大陆较早的“艺术-社会先锋派”[3]〔美〕维克多·马格林:《设计,为乌托邦而奋斗:罗德琴科、利西茨基和莫霍利-纳吉(1917—1946)》,张馥玫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14 页,第5 页。,他们的实践转向对研究现代设计启蒙发展,补全现代设计的“两个来源”[4]Bokov,Anna.Avant-Garde As Method: Vkhutemas and the Pedagogy of Space,1920-1930. Zurich:ParkBooks,2020: 20.弗兰普顿在序言中提到了呼捷玛斯是现代设计和先锋艺术的观念发展中被严重忽视的一个源头。有着重要参考价值,同时也是研究现代设计观念谱系的重要一环。
1.空想社会主义、未来主义与大众艺术文化研究院
“先锋性”一词的提出最早是在圣西门的《对话:实业家、艺术家与科学家》中,其将艺术家、科学家和实业家称为“引领社会前进的三巨头”[5]〔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顾爱彬、李瑞华译,译林出版社,2015 年版,第102 页。,这就是先锋性在社会学上最早的意义——引领社会前进,推动时代进步。而这种先锋性贯穿在现代设计启蒙运动的方方面面,体现在拉斯金的《建筑的七盏明灯》中,也体现在莫里斯的红屋中,更体现在包豪斯校舍和第聂伯河水电站中。从19 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充满矛盾与混沌的社会阴霾在这里被激荡和驱散——反对一切旧社会的体系,提倡与一切旧势力斗争。马里内蒂在《未来主义宣言》中更为激进地赞美了工业时代的技术与机器美学。他的观念带动了一批先锋艺术家进行激进的社会实践与艺术创作,马列维奇也是在其深刻影响下作出改变的艺术家之一。
20 世纪注定是一个变革的世纪,累积的矛盾与阴霾最终以世界大战的形式爆发,不仅加速了国际格局的动荡,也推动了国家内部利益集团的重构。为探索能够代表国家形象的新的艺术形式,苏维埃在维捷布斯克设立了新的大众艺术文化研究院,马克·夏加尔由于其知名民族艺术家身份被人民教育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委任为艺术委员,并领导维捷布斯克的大众艺术文化研究院,引导学生开创现代的新的民族风格。马列维奇与利西茨基亦是受夏加尔邀请而来,在这一阶段,利西茨基创作了《用红色楔子楔入白色》,以及后来奠定他视觉叙事逻辑的《关于两个方块的故事》。
马列维奇在大众艺术文化研究院中组建了自己的至上主义团体“宇诺维斯”(UNOVIS),意为“新艺术的确立者”,开始以更加主动的姿态投身艺术的社会实践,并进行了一系列相关的设计,从舞台美术到公共场所,从瓶碗柜壶到服装面料,都进行了大范围的归属至上主义的应用实验。
2.苏俄先锋设计师的社会实践——呼捷玛斯
不只是未来主义者,传统的新古典主义者和老艺术家在革命后也有着高涨的改造社会的激情与美好愿景,希望能够在新的社会建立一个新学派,泽被后世。随着1920 年苏俄国内战争的基本结束及新经济政策的推行,苏俄政府试图通过院校重组来重新建立一所为人民、国家和大工业生产服务的艺术学校。1920 年12月19 日,人民教育委员会将斯特罗加诺夫工艺美术学校与莫斯科绘画雕塑与建筑学校(此前于1918 年9 月已经改组为国立第一、第二自由艺术工作室)合并,组成莫斯科国立高等艺术与技术工作室,简称“呼捷玛斯”。呼捷玛斯是融合了俄国现代建筑教育、美术教育、设计教育的大熔炉,不仅熔炼着新兴工业社会的文化,也在不断地将能量辐射至欧洲大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同时组建了以佐尔托夫斯基与舒舍夫为核心的莫斯科国家建筑公司,以便组织大规模建设。
二、社会改造的高歌猛进:新旧风格的矛盾、国家计划与图像叙事
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提到审美与政治、社会体制的关系,两者互相渗透、互相呼应,政治路线的探讨会在艺术上得到表现,艺术观念的分歧也会对政治和社会体制产生影响,即文化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当时社会环境复杂,在艺术和设计上体现为风格主义之争,艺术家开始更加积极主动地投身于社会实践与教育。
令人十分疑惑的是,原本在实现工业化之后,应当随着工业化进程而逐步确立国际主义的观念,在现实中却有着相反的结果——民族意识的觉醒。而作为民族意识的审美表现,装饰与现代工业生产的效率却格格不入。是更新审美观念迎合技术,还是利用技术还原传统审美观念,这一对矛盾贯穿了现代设计运动的始终,而在20世纪20年代,终于有了新的突破——风格、民族国家与技术的统一。这也是确立现代主体性的重要一环,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1.拉多夫斯基的理性主义探索
在拉多夫斯基进入莫斯科绘画雕塑与建筑学校之前和离开呼捷玛斯之后,均未留下多少可考的历史,而他任教时创立的理性主义建筑学教学体系,却是设计教育上的创新性成果,也是莫斯科现代建筑设计教育的源流之一。他将二维的传统古典建筑学习方式延伸到三维的空间建构方式,由此去理解建筑和结构。学生只被允许创造新元素和从三维世界中建构设计原型,由此替代传统的“学院派”二维临摹作画的技法积累,并仅以将概念在现实世界建造出来作为设计的目标,即提出实用性(落地性)的强烈要求。[1]韩林飞、康贺阳:《苏联构成主义“现代建筑教育”创始人——拉多夫斯基思想探究》,《世界建筑》2020年第7 期。为了帮助学生掌握空间感,他专门设计了一款暗房,内有可穿戴的带有灯泡的设备和帮助感知距离的设备。
拉多夫斯基倡导理性主义与现代工业材料的广泛运用,可以说是从新古典主义与构成主义各取其长,形成了自己的拉多夫斯基学派,并持续影响了后来苏联理性主义的建筑设计及设计教育直到今天。
2.罗德琴科与塔特林的构成主义实践
作为驴尾巴画派的同僚,又曾同为呼捷玛斯的教员,罗德琴科与塔特林这两位构成主义大师,一个注重平面元素的构成,一个侧重现实材料的构成,将运动势能、机械美学、形式美法则综合运用于社会生产。罗德琴科认为艺术最大的未来在于生产,在生产中实现艺术的价值,即生产艺术和总体艺术,传统架上绘画已经没有新的可能性,新的艺术家是工程师、科学家,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社会实践。作为呼捷玛斯基础教学部(预科班)的教员,罗德琴科在基础课程的设计上不仅体现了个人对新的应用艺术的理解,也体现了呼捷玛斯对新的设计教育的偏向。
罗德琴科创新地将自己的构成观念贯彻到了两年制的预科教育中,将所有的物象全部分解为最简单的形状——三角形、矩形和圆形,并通过平面、色彩、空间三类构图课将基础图形一步一步地进行架构,并最终形成建筑的雏形[2]Bokov,Anna.Avant-Garde As Method: Vkhutemas and the Pedagogy of Space,1920-1930. Zurich:ParkBooks,2020: 26-28.拉文多夫·亚历山德罗在序言中提及了罗德琴科的构成教学方法。——这是与在包豪斯任教的大艺术家康定斯基、色彩课前任教员伊顿所不同的,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是最接近物象的本质的。
塔特林最初与马列维奇一同处于至上主义的队伍中,他深受毕加索立体主义和未来主义的影响,后在艺术的最终目标上与马列维奇产生强烈分歧,并分道扬镳——艺术是为自身形而上的至高无上,还是作为具体落实在客观物象上的指导?作为对这两个方面的回应,他们一个走向了至上主义和表现主义,一个则走向了构成主义生产艺术的美学观念。马列维奇甚至开始在思想上与道家的“无”有了相似的境界,而塔特林走向了应用,并在第三国际纪念碑的设计中将共产主义理想、新兴工业技术与基督教巴别塔的典故相结合,虽然当时并未真实投产,但作为一种理想主义的化身,其深深地震撼了当时的欧洲设计师、艺术家和人民群众。
3.新古典主义巨匠——佐尔托夫斯基与舒舍夫
佐尔托夫斯基(又译作若尔托夫斯基、诺尔托夫斯)出生于1867 年,曾是拉多夫斯基的导师,也是俄国新文艺复兴时期的新古典主义巨匠。他在呼捷玛斯成立前的莫斯科绘画雕塑与建筑学校教授建筑,并在学校合并后进入呼捷玛斯,教授新古典主义建筑设计。后与舒舍夫共同领导了莫斯科国家建筑公司,旨在推动莫斯科的战后重建和住房问题的解决,并配合“一五”计划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佐尔托夫斯基对建筑设计与教育充满热情,影响了相当一部分构成主义者向新古典主义转型;而舒舍夫则在7 天内完成列宁墓的设计并赢得了竞标。以他们二人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及其学生拉多夫斯基共同推进了新古典主义学派与构成主义生产美学的结合。
4.构成主义者的社会实践——现代建筑师协会(OSA)与第聂伯河水电站
现代建筑师协会更像是一个职业的构成主义建筑师的行会,他们遵循着构成主义的基本原则,定期进行交流与项目合作,主张“创造崭新的、大型工业中心区的现代建筑风格”[1]刘文豹:《苏联“构成主义”建筑运动的旗手:维斯宁兄弟》,《建筑师》2012 年第4 期。,并以维斯宁和金斯堡为领导(柯布西耶也曾参加过OSA 且深受影响)。
维斯宁兄弟是建筑史上少有的家族建筑师组合,三人合作实现了工业与艺术、技术与美学在建筑上的统一,后被誉为“构成主义的旗手”[2]〔美〕维克多·马格林:《设计,为乌托邦而奋斗:罗德琴科、利西茨基和莫霍利-纳吉(1917—1946)》,张馥玫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230 页。,而其代表作第聂伯河水电站的室内设计竞标,不仅仅是苏联“一五”计划最伟大的水利工程的一部分,也是构成主义风格集大成的作品代表。考虑到发电机的移动性和空间自由度,维斯宁三兄弟领衔设计的内部建筑结构,既保障了功能性,又使室内空间整洁干净,与同时竞标的佐尔托夫斯基充满华丽装饰的新古典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3]〔美〕维克多·马格林:《设计,为乌托邦而奋斗:罗德琴科、利西茨基和莫霍利-纳吉(1917—1946)》,张馥玫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230 页。它不仅是苏联的“三峡工程”,而且由于水电站建设计划,专门成立了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和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配合、推动了国家上层建筑的革新,还促成了与美国威尔逊大坝的建设负责人修·林肯·库博的技术指导合作。它是当时联盟内部加盟共和国之间规模最大的合作工程,对于国家复兴和发展的意义,远远超出它在技术美学和工程技术上的地位。
利西茨基把第聂伯河水电站落成的全过程素材排版后发表在1932 年第10 期《苏联建设》上,为当时的西方世界提供了走出大萧条的经典案例,有力地宣传了国家形象。
三、理想的互渗:包豪斯由新行会到先锋实验场的转变
1.从通往天堂的高塔到直面工业化和机械化
1919 年,格罗皮乌斯接任威尔德,将魏玛工艺美术学校与魏玛艺术学院重组为国立建筑学校,即“包豪斯”,还发表了《包豪斯宣言》,强调建筑家、雕塑家、画家共同合作,回归手工艺,建立新的艺术殿堂。此时格罗皮乌斯仍然有着“回归中世纪”的传统精英主义的浪漫怀旧心理,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他,认识到机器作为战争工具的巨大破坏性。因此,在早期的设计教育中仍然保留着一些手工艺传统。但是,工业化背景下的机器将会碾压绝大部分小作坊的手工艺形式,个体作业必不可能在规模与效率上超越群体的通力合作。而至于建筑设计教育,格罗皮乌斯在任期内未成立建筑系,所有与学校合作的建筑设计订单都要经过格罗皮乌斯之手。
20 世纪20 年代的苏德关系十分微妙,两国都被新建立的国际秩序所排斥,在被孤立的状态下不得不走向合作。在此背景下,苏联的“生产艺术”“构成主义”等先锋艺术观念通过苏德之间的合作项目,以文化交流的形式来到德国。呼捷玛斯正式成立后,利西茨基受命试图建立“苏德艺术联盟”,与格罗皮乌斯、杜斯伯格、密斯会面,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格罗皮乌斯的设计观。1923 年5 月,全校参观柏林凡迪门美术馆的苏联新艺术展后,格罗皮乌斯在8 月15 日的讲演中进一步提出“直面这个工业化和机械化的时代,像毕加索、新俄罗斯和匈牙利的学校们,施莱默、克利等,因此就要将这两者都放进到设计中去,进行艺术和技术——新的结合”[1]〔德〕沃尔特·格罗皮乌斯:《说明》,张云亭:《被误解的包豪斯》,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62 页。。自此,格罗皮乌斯逐步抛弃对手工艺小生产者的过度同情,更加主动地拥抱工业生产,同时修改培养计划,选择了他的后继者,同时也是包豪斯整个建校时期争议最大的建筑师——汉内斯·迈耶。
2.现代设计学校的艰难探索
直到1927 年汉内斯·迈耶上任,包豪斯德绍校区建立,包豪斯才拥有真正意义上的建筑系。在苏联构成主义的影响下,格罗皮乌斯邀请大众艺术文化研究院原院长康定斯基、对呼捷玛斯的培养模式有一定了解的莫霍利-纳吉,以及呼捷玛斯的一些教员进行交流活动。马列维奇的《无物象的世界》是由莫霍利-纳吉在包豪斯帮助出版的,利西茨基、罗德琴科等教员都来过包豪斯进行短期访学交流,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包豪斯厘清自己的实践方向,夯实了与呼捷玛斯比肩的“现代主义双生子”[2]韩林飞:《纪念呼捷玛斯一百年(1920—2020):呼捷玛斯在苏俄前卫艺术运动中的地位与贡献》,《世界建筑导报》2020 年第6 期。的地位。
迈耶上任后对格罗皮乌斯绕过学校接建筑设计订单的行为表达过反对,认为“建筑应当全校师生共同参与”[3]周向力:《“事与愿违”——汉内斯·迈耶事迹与“包豪斯”的关系研究》,中国美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21 年。。他的这一观点表现出作为一名信仰社会主义者与传统社会精英在价值观上的冲突。但最重要的是,迈耶在包豪斯的教学上增加了除美术史以外的人文学科的教学,包括设计的社会责任、马克思主义教育……至此,包豪斯在真正意义上转变为有社会意义的学校,迈耶也据此推动建筑系逐步走上轨道,虽然与克利关系不是非常融洽,但是除去政治问题之外他们还是能互相包容的。[4]周向力:《“事与愿违”——汉内斯·迈耶事迹与“包豪斯”的关系研究》,中国美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21 年。
虽然迈耶自称“科学的社会主义者”,但也抵不过国内形势的急转直下。1930 年8 月迈耶在日趋激化的政治矛盾中主动“立即辞职”[5]〔德〕包豪斯档案馆、〔德〕玛格达莱娜·德罗斯特:《包豪斯:1919—1933》,丁梦月、胡一可译,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 年版,第199 页。,而包豪斯的先锋性在短短几年的斗争中宛如昙花一现,继任的密斯也十分低调,只是使即将分崩离析的包豪斯又苟延残喘了两年。
四、理想的碰壁:现实的矛盾与和解
1.构成主义理想乌托邦与现实的矛盾
从弗兰普顿“批判的地域主义”[6]〔美〕肯尼斯·弗兰姆普敦:《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张钦楠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年版,第355 页。的角度来分析,构成主义在20 世纪20 年代中叶在欧洲各地形成风尚,大有“国际主义”的趋势。1925 年在德国举办的“国际构成主义者大会”上,欧洲先锋派与苏联先锋派汇合,开始试图营造国际风格。但是这种风格在形式美上极富秩序感而又非具象。这也是新古典主义、现实主义能在第二轮工业化浪潮下仍然充满活力的内因——民族性和地域性的文化特征。它与构成主义相比,学习门槛低、传播性强,有利于民族身份认同和国家形象宣传。从先锋性来讲,国际主义是领先于时代的,是符合工业技术的时代发展要求的,但是它不应该异化人与机器的关系。这是实践层面的技术哲学反思的萌芽,也是人文情感关怀与高技术理性的交锋。
到了20 世纪30 年代,欧美地区仍在推崇新古典主义,而先锋艺术早已成为苏联的国家形象代言人。但是为了与欧美各国争夺建筑和艺术的话语权,加之国内扫盲和宣传的严峻形势,对国家宣传和国际舆论都产生了极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疲于应对眼下的国内外形势,逐渐失去了对先锋艺术的解释权。此时美国接受了一批当年被迫离开德国的先锋设计师和艺术家,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与苏联构成主义和呼捷玛斯有重要关联,如莫霍利-纳吉受美国地方邀请创办了“新包豪斯”。同时对于苏联国内而言,日趋艰难的国际环境与亟待改善的国内状况已经很难容许构成主义者形而上地进行无忧无虑的尝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由于其具象的写实性,学习门槛低,对于知识传播、教育普及相较于形而上的构成主义而言具有一定的优势,所以在政策上更加倾斜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构成主义者也必须为他们的社会作出相当的贡献以继续留在苏联——乌托邦的土壤开始消逝,这不仅在苏联,在美国也是如此。莫霍利-纳吉的“新包豪斯”在芝加哥艺术与产业协会一年的短期资助下也被解散。[1]〔美〕维克多·马格林:《设计,为乌托邦而奋斗:罗德琴科、利西茨基和莫霍利-纳吉(1917—1946)》,张馥玫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293-294 页。而他们的学生却推动了设计学科的科学化与职业化。
2.包豪斯的现实困难与德国现代设计的萌发
包豪斯作为德意志工作同盟的续曲,曾是德国工业高歌猛进的强劲音符。但现实就如1914 年的“科隆论战”一样,在两方的激烈斗争中艰难前行,虽然穆特修斯是未来的方向,但当时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很赞同威尔德[2]豆笑笑、汤常鸣:《寻求科学技术与人文艺术中的平衡之旅——以“科隆论战”为例》,《大众文艺》2020 年第10 期。,于是矛盾便产生。这种矛盾也体现在格罗皮乌斯身上。格罗皮乌斯在包豪斯初期有着“回归中世纪手工艺”的逃避心理与想要进行新的尝试的矛盾,与其说是逃避,不如说是惧怕。当发现有相似甚至更加激进的观点在东方被实践,他或许也打开了自己心里的枷锁,开始运用自己的关系与兄弟院校加强联系。在呼捷玛斯的启发下,包豪斯开始在国内复杂的环境下进行设计运动,推动设计教育改革,其中所经历的苦难与艰辛,或许只有格罗皮乌斯和迈耶才知道。他们的努力探索,由马克思·比尔和马拉多纳多继承并在乌尔姆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德国理性设计和功能主义的设计文化。
3.呼捷玛斯的建设热情与路线斗争
与包豪斯的艰难处境相比,呼捷玛斯还算幸运: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新经济政策、开放宽松的办学环境,甚至可能还有学费免除[3]浦安原、张磊:《呼捷玛斯悖论:构成主义的国家身份和功能再造》,《艺术设计研究》2021 年第4 期。;自由和专业的学术氛围,堪称豪华的建筑师教师团队。这些都是包豪斯所不能拥有的。
呼捷玛斯是第一个在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尝试用艺术来指导生产实践的公立设计学校。他们当中有的大刀阔斧地抛弃一切传统,从零开始塑造为生产的应用艺术和为人民的艺术;有的立足传统,从长辈的角度出发去保护这些来之不易的新生思潮。他们相互交流,互相学习,逐渐形成了博采众长的设计艺术培养模式。不止如此,对新社会的美好向往也推动他们充满激情地投入生产实践,随着“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口号的提出,所有人都被动员起来。虽然呼捷玛斯内部也有各种风格和观念的分歧和冲突,但总的而言是以美好理想的实现为核心的。呼捷玛斯的学生毕业后大量投身社会实践,从水电站到招贴海报,从大型工程到日常用品,所有人都成为国家机器运转的零件,紧凑而高效地运行着。
五、唤醒与激荡:乌托邦的设计探索对先锋性与现代设计观念的塑造
“先锋性”的艺术家在20 世纪初由形式艺术走向应用艺术和“总体艺术”的职业转向,很大程度上源于工业革命的机器文化,它作为一种新的生产生活方式,推动着嗅觉灵敏的“先锋派的社会-艺术家”的快速转型,而对于机器文化的回应,也能在另一个角度体现“先锋性”。
在苏联,面对过于超前的甚至去文脉性和民族性的现代艺术设计,与人民群众接受程度较低的矛盾,加之欧洲波谲云诡的国际环境,内忧外患强迫着上层机构作出取舍。而十分巧合的是,构成主义也快速地走完了一个生命周期——由一个源于为人民、为社会的先锋观念走向形而上的形式主义,只活跃了短短十年,旋即被勒令停止。其最核心的意识形态上的观念为呼捷玛斯之后的莫斯科建筑学院所继承,而其与新古典主义的斗争,最后以汇合在拉多夫斯基学派,构成特殊的苏联现代主义为结局。而在1933 年的德国,构成主义者和包豪斯都被打上了政治烙印,被强行关闭,教员学生们只得前往美国另觅出处。
在美国,设计理念的过于深刻与大规模快节奏的资本主义市场相矛盾。市场要求他们能做设计,能产生经济利益即可,而他们却在思考怎样培养设计“思想家”。在逆流而上中不断与市场相互激荡、沉淀,最终推动了职业设计师与咨询设计师这两种设计师职业的产生,并推动了设计的科学化、系统化。甚至“包豪斯设计文化”都能够被国家舆论力量武装起来,营造“包豪斯神话”,以此来强化自由多元的国家形象。
构成主义作为现代主义运动中最具民主性与社会性的先锋艺术运动与设计革命之一,在欧美垄断话语权的世界现代设计史中,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随着包豪斯和呼捷玛斯双双建校一百周年的史料被解封与再研究,构成主义的整个生命周期被再一次较为完全地发掘,成为世界现代设计史、现代性研究中一块重要的拼图;同时,开展对先锋性本质的研究,不仅仅是对过去欧洲社会主义遗产的挖掘,更是对现代性的深度探索,对于中国现代文化体系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