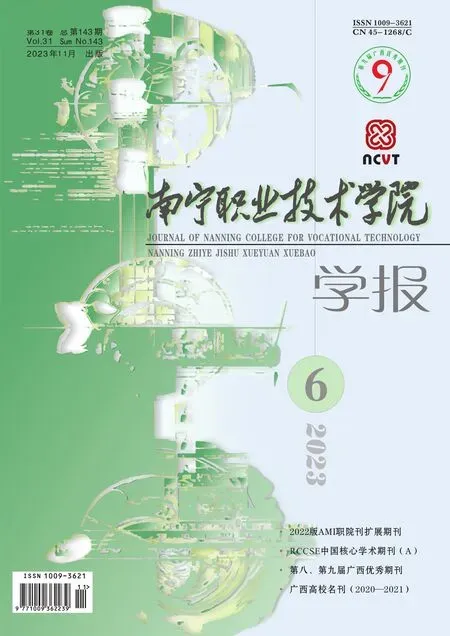从宫廷食羊看元代蒙汉文化的交流
——以《饮膳正要》为中心
马 騻
(大庆市人大常委会 人大代表履职服务中心,黑龙江 大庆 163311)
元朝是由蒙古族建立的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所以其宫廷饮食也呈现出明显的蒙古文化特色,在烹饪“羊”这一食材时就能够体现这一点。煮食与炙烤是蒙古族传统的烹羊方式,元朝政权建立后,食羊传统进入宫廷,其烹煮方式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具体变化表现为在煮和烤的基础之上,羊被配以各类食材、佐之各种调料,采取蒸、炸、炒等各类翻新的做法,体现了蒙汉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融。在目前关于元代食羊的考述中,学者们分析了“羊”成为北方游牧民族主要食材的原因,也介绍了以羊为主料的部分菜品,但是从文化交流的视角切入考察宫廷食羊的相关研究还较为鲜见。在普通的饮食背后,文化发挥着难以忽视的作用,故而从饮食传统变迁观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情况亦成为一个研究方向。
一、蒙古文化中的传统食羊法及其发展——炙烤、煮食
在入主中原之前,元代统治者常年在草原上活动,过着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虽然他们在养殖羊上有较多经验,也具备较大规模,但是对羊的主要烹饪方式却相对单调。由于蒙古族经常搬家,在蒙古包中准备太过复杂多样的炊具是不现实的,所以牧民们往往只以简单的水煮或炙烤等方式烹羊,有时候甚至直接风干,制成朴素却美味的餐食。
而宫廷食羊则不同。据《南村辍耕录》记载:“国朝日进御膳,例用五羊。而上自即位以来,日减一羊,以岁计之,为数多矣。”[1]此即表明,元代宫廷里每天都要消耗5只羊制作御膳,即使后来出于节俭改用4只,其数目仍不可小觑。羊的用量如此之大,其食法更是多种多样,以烤、蒸、煮、羹等为代表的烹饪方式则值得关注。
忽思慧的《饮膳正要》是反映元代宫廷饮食的重要典籍,其中与食羊相关的膳食就有70多种,但是以传统炙烤为主要烹法的菜品不多,炙羊腰是其中一种:“治卒患腰眼疼痛者。羊腰一对,咱夫兰一钱。右件,用玫瑰水一勺,浸取汁,入盐少许,签子签腰子火上炙。将咱夫兰汁徐徐涂之,汁尽为度。食之甚有效验。”[2]94“咱夫兰”即藏红花,“右件”是指“以上这些食材”。取掺了盐的玫瑰水和藏红花汁混合,慢慢地涂抹在用签子串起来在火上烧烤的羊腰子上,从中能看到现代烧烤的雏形。在享受炙羊腰美味的同时,还可以治疗突发性腰眼疼痛,颇有“以形补形”的意思。而从材料中注明的涂花汁速度来看,这道炙羊腰应该是需要把控好火候与时间的,如果是急火速成,便容不得“徐徐涂之”了。
炙羊腰是烧烤羊的内脏,柳蒸羊则是整羊上阵。“羊一口,带毛。右件,于地上作炉,三尺深,周回以石,烧令通赤,用铁芭盛羊上,用柳子盖覆,土封,以熟为度。”[2]110-111“铁芭”是用铁条制成的带支架的烧烤篦子,“柳子”即柳树枝条。挖地三尺作为炉灶,底层和内壁都垒满石头,再用明火入内烧灼。等到石头被烧得通红,取出火源,把带毛且去除内脏后的整羊放在铁条篦子里再放进炉灶。羊上铺满柳枝,把土覆盖在柳枝上封起炉坑,等羊被烤熟即可享用。柳蒸羊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烧烤,羊肉是被石头的温度烤熟的。元代蒙古人食羊似乎善于使用各类植物进行辅佐烹饪,正如他们也惯于使用丰富多样的香料佐以调味一样。另外,《饮膳正要》中有一则生食现象值得注意:“肝生。羊肝一个,水浸,切细丝;生姜四两,切细丝;萝卜二个,切细丝;香菜、蓼子各二两,切细丝。右件,用盐、醋、芥末调和。”[2]106这里仅仅是把羊肝用水浸泡过,就切丝佐以其他辅料、调料食用,风格不拘小节,这大概是游牧时期饮食习惯的保留。
不难发现,在元代的宫廷食羊法中,煮食仍然占了很大一部分比例。但是不同于草原上的烹饪,宫廷饮食中“煮”多半只是局部手法,在煮熟之后,还要配以面食加菜同炒等,仅以一种烹法制成的御膳极少。以煮为基础,可以衍生出各式各样的精致菜肴。如煮羊肺名为河西肺:“羊肺一个;韭六斤,取汁;面二斤,打糊;酥油半斤;胡椒二两;生姜汁二合。右件,用盐调和匀,灌肺,煮熟,用汁浇食之。”[2]97“河西肺”是把半斤酥油和面糊混合,兑入二两胡椒和适量的盐,再将这些灌入处理干净的羊肺中煮熟,配合韭菜汁、生姜汁食用。虽然其主要的烹饪手法仍然是煮,但是已经与草原上的煮物大不相同。比起“煮熟”这一目的,河西肺更追求味觉上的绝妙体验。
羹类膳食更能体现由煮食所发展出的宫廷饮食之丰盛:“杂羹。补中益气。羊肉一脚子,卸成事件;草果五个;回回豆子半升,捣碎,去皮。右件,同熬成汤,滤净,羊头洗净二个,羊肚、肺各二具,羊白血双肠作一副,并煮熟切。次用豆粉三斤,作粉,蘑菇半斤,杏泥半斤,胡椒一两,入青菜、芫荽炒,葱、盐、醋调和。”[2]69“羊肉一脚子”可以较为精确地指代四分之一块羊肉,或是粗略地指代一块、一部分羊肉,“卸成事件”就是把羊肉拆解成小块。“回回豆子”指的是鹰嘴豆的种子,是元代宫廷饮食中常用的食材之一。羊白血双肠俗称“羊双肠”,制作方法是把羊血、羊脑、羊脂灌进清理干净的羊大肠内,煮至略熟,晾晒到羊肠中的羊血凝固,切小段后加调料煮熟食用。杏泥是杏肉制成的果泥,芫荽即香菜。羊肉、草果和去皮捣碎的回回豆子一同熬煮成汤,并滤净汤汁。把处理干净的羊头、羊肚、羊肺、羊白血双肠也煮熟切小块。豆粉做成面丝煮熟,与炒熟的蘑菇、杏泥、胡椒、青菜和芫荽混合,最后加调料葱、盐、醋调匀,菜品才算做好。一道杂羹所需要的原材料竟有16种之多,足见元代宫廷食羊已经不再只是追求朴素的美味,而是开始走向工艺繁复的精致。
二、汉族文化影响之下的食羊法——蒸、炒、炸
宫廷御膳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帝王及其亲眷,他们有足够的能力“聚敛天下美食,役使天下名厨”,寻觅最优秀的厨师,使用最上等的食材来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所以宫廷御膳往往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最高烹饪水平[3]。元代御膳不仅保持着蒙古族原本爱好食羊的习惯,还兼收并蓄汉族饮食文化中的长处,采用蒸、炸、炒等多种烹法,使羊的烹饪方式不断推陈出新。
元代宫廷食谱中不乏与羊相关的蒸物:“剪花馒头。羊肉、羊脂、羊尾子、葱、陈皮各切细。右件,依法入料物、盐、酱拌馅,包馒头,用剪子剪诸般花样,蒸,用胭脂染花。”[2]113元代的馒头形制更接近于现在的包子。在切细的羊肉、羊脂、羊尾子、葱、陈皮中加入各类调料,拌成馅料,再包成馒头。与其他菜肴不同的是,剪花馒头有用剪刀剪花样、胭脂染色的步骤。这与菜的味道无关,完全是满足审美需求的工艺,代表着宫廷中的人们已经不满足于单种手法烹饪的美味,他们更希望的是“色香味”俱全,这也使得宫廷食羊与游牧时代的食羊区别开来。以蒸为主要烹法,但制作更复杂的有荷莲兜子:“羊肉三脚子,切;羊尾子二个,切;鸡头仁八两;松黄八两;八担仁四两;蘑菇八两;杏泥一斤;胡桃仁八两;必思荅仁四两;胭脂一两;栀子四钱;小油二斤;生姜八两;豆粉四斤;山药三斤;鸡子三十个;羊肚、肺各二副;苦肠一副;葱四两;醋半瓶;芫荽叶。右件,用盐、酱、五味调和匀,豆粉作皮,入盏内蒸,用松黄汁浇食。”[2]116这里提到的“苦肠”并不是指猪小肠,而是羊小肠,相比于猪、鸡、鱼等肉类,羊始终是元代宫廷最常用的肉类食材。“松黄”即松花,松树的花粉。一说松黄汁是松花调制的汁液,另一说松黄汁是农历三月间松花落地,四五月遇雨而出,八九月散布松下的红黄交错之物绞成的汁[2]59。荷莲兜子口感丰富,兼容并包。豆粉擀皮,内馅制作使用羊肉、羊尾、羊肚、羊肺、羊小肠等羊的五种部分,在盏中蒸熟后,以松黄汁佐食。除了像剪花馒头那样用胭脂染色,荷莲兜子还使用栀子色汁增添色彩,可见元代宫廷对御膳的“色”十分重视。
如果说蒸食仍然是水煮烹饪的变形,那么宫廷炒菜的存在不可否认地证实了蒙汉文化之间的交流:“熬蹄儿。羊蹄五副,退洗净,煮软,切成块;姜末一两;料物五钱。右件,下面丝炒,葱、醋、盐调和。”[2]107羊蹄直接爆炒不易熟,所以要先把退毛洗净的羊蹄煮软切块。起锅热油,下葱花姜末爆香,羊蹄块与熟面丝同炒,再调和食用。还有一种叫“围像”的炒菜,用料更为丰富:“补益五藏。羊肉一脚子,煮熟,切细;羊尾子二个,熟,切细;藕二枚;蒲笋二斤;黄瓜五个;生姜半斤;乳饼二个;糟姜四两;瓜齑半斤;鸡子一十个,煎作饼;蘑菇一斤;蔓菁菜、韭菜各切条道。右件,用好肉汤,调麻泥二斤、姜末半斤,同炒。葱、盐、醋调和,对胡饼食之。”[2]80“糟姜”和“瓜齑”都是腌渍的小菜,“乳饼”是由羊、牛或马奶熬炼、压缩而成的饼状奶制品,“胡饼”即新疆常见的烤馕。“围像”综合了羊肉、羊尾这样的荤菜以及藕、蒲笋、黄瓜、蘑菇、蔓菁菜、韭菜这样的素菜,荤素搭配,营养价值丰富。
炸也是宫廷御膳的重要制作手法:“姜黄腱子。羊腱子一个,熟;羊肋枝二个,截作长块;豆粉一斤;白面一斤;咱夫兰二钱;栀子五钱。右件,用盐、料物调和,搽腱子,下小油炸。”[2]97准备煮熟的羊腱子和羊肋排,外面裹上豆粉、白面、咱夫兰、栀子粉末和盐等调料混合的面糊,入锅油炸,出锅即可食用。《饮膳正要》中提到,在元代宫廷烹饪中,咱夫兰与栀子的使用频率都很高,一方面是因为它们有一定的染色功能,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这两种料物都具有养生功效。在忽思慧看来,咱夫兰能够疏散淤堵之气,通解抑郁之情,长期食用会让人心情愉悦:“咱夫兰。味甘,平,无毒。主心忧郁积,气闷不散,久食令人心喜。”[2]485而栀子则可以通利小便,化解五脏中可能导致疾病的邪气,对眼睛发热红肿也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栀子。味苦,寒,无毒。主五内邪气,疗目赤热,利小便。”[2]488而大量食用羊则能够起到益气补虚的作用。宫廷饮食注重的不仅是菜式的可口与美观,对食疗养生方面也十分关注,《饮膳正要》记录的每一道菜谱均最先注明其所具有的食疗功能,由此可见一斑[4]。蒙古族人已经熟悉米谷、禽、兽、鱼、果、菜、物料等多种食材的性味、功能、可治疗病症及副作用,在烹调时也懂得注意食物相反相克的原理,避免食物中毒。这些养生概念大多是从汉族文化中汲取的,从另一角度显示了蒙古文化受到汉族文化的深刻影响。
三、蒙汉文化交流中的契合——食羊血和内脏
虽然元代宫廷王室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完全可以只吃羊肉的精华部分,但实际上,羊的各类内脏和羊血也在元代宫廷饮食范围之内,如上述提到的炙羊腰中的羊肾,肝生中的羊肝,河西肺中的羊肺,杂羹里的羊头、羊肚、羊肺和羊白血双肠,剪花馒头中的羊脂、羊尾,熬蹄儿里的羊蹄,等等。元代甚至有“全羊宴”,顾名思义,是以整只羊作为原材料,从羊头至羊尾,利用羊的不同部分烹调出各式各样的美味佳肴。蒙汉文化在这方面一拍即合,证据就是宋元文献中有大量使用羊血及内脏的记载,这种在饮食上意料之外的默契也为两种文化的交融提供了有利条件。
除了前文提及的几种菜肴,元代御膳里还有羊血制成的“红丝”:“羊血同白面依法煮熟;生姜四两;萝卜一个;香菜、蓼子各一两,切细丝。右件,用盐、醋、芥末调和。”[2]109用新鲜羊血和面粉和成光洁的面团,然后把面擀平、切丝,下锅煮熟后捞出。最后在掺入羊血的红色面条里加入配菜姜丝、萝卜丝、香菜、蓼子和调料同炒而食。另有一种羊脊骨羹:“治下元久虚,腰肾伤败。羊脊骨一具,全者,锤碎;肉苁蓉一两,洗,切作片;草果三个;荜拔二钱。右件,水熬成汁,滤去滓,入葱白、五味,作面羹食之。”[2]206“肉苁蓉”是一种常用中药,可以补肾益精。为了使羊脊骨的营养和香味能更充分地被熬制出来,需要先锤碎一整副羊骨头,再佐以肉苁蓉、草果、荜拔这些香料文火慢炖成高汤,滤除残渣,只留汤液,即可制作面羹。食用羊血及其内脏具有一定的养生作用,《饮膳正要》中列举了羊头、羊心、羊肝、羊血、羊五藏、羊肾、羊骨、羊髓、羊脑、羊酪的养生功效与禁忌,比如:“羊血:主治女人中风,血虚,产后血晕,闷欲绝者,生饮一升。……羊骨:热。治虚劳,寒中,羸瘦。”[2]303这样说来,食用红丝可以专治女性中风、血虚或是产后失血过多导致的眩晕,而有虚损、寒中病症或身体羸弱的人则非常适合喝羊脊骨羹。蒙古族人在食羊上时时刻刻牢记食疗进补。
食羊血和内脏并非由于元代宫廷节俭,与之相反,奢侈一词更能代表元朝帝王妃嫔的日常。其实和食羊这件事本身一样,一是受蒙古统治者曾经的饮食习惯所影响。在草原上,羊是珍贵的食物,养殖、放牧都需要较大的人力物力,为了避免浪费,牧民们往往倾向于将羊的食用效益最大化,羊的各个部分都尽可能地纳入食谱,这是属于游牧时代的文化印记。二是汉文化中也一直有着食用动物内脏和血的传统。食羊并不是元代的专利,宋代宫廷为了避免寻求珍奇异味所带来的不必要的人、物浪费,御膳基本只用羊肉,并且兼及羊杂,宋孝宗就曾以“胡椒醋羊头”款待他的讲读老师胡铨。虽然最后的结果与初衷背道而驰,但是宋代宫廷对羊的偏爱是毋庸置疑的。宋代还有羊粉血羹、羊头签以及羊脊骨粥:治老人脾胃气弱,劳损,不下食。大羊脊骨一具,肥者,锤碎。青粱米四合,淘净。上以水五升,煎取二升汁,下米煮作粥,空心食之。可下五味常服,其功难及,甚效[4]。元人的《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收录了与之文字相同的煮粥食谱,其中锤碎羊脊骨的做法与上述羊脊骨羹的准备工作极其类似,体现了元代宫廷对宋代食羊法的继承。先注明膳食功效,再详写具体做法的体例似乎也对《饮膳正要》的编撰产生了影响。
四、结语
如同文化融合的过程不是简单的二者相加一样,各类烹羊法之间也并非界限分明。有的先煮后炸,有的先煮后炒,烤、煮、蒸、炒、炸等多种烹饪方式以错综复杂的形式结合在一起,不能单纯而论。蒙古文化中传统的以炙烤、煮食为主的食羊法在元代建立以后,并未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和汉族饮食文化结合发展,吸收蒸、炒、炸等烹饪手法,衍生出适应新需求的多种菜肴。同时,宫廷御膳也比游牧时代更加重视菜品视觉上的美观,懂得学习汉文化中食疗养生的观念,也不避食羊血及内脏。元代存新而不去旧,继承了宋代的优良烹饪技术,迸发出蓬勃发展的活力。元代宫廷食羊这件饮食小事所体现的,是蒙古文化与汉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印证各民族共融共通早已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