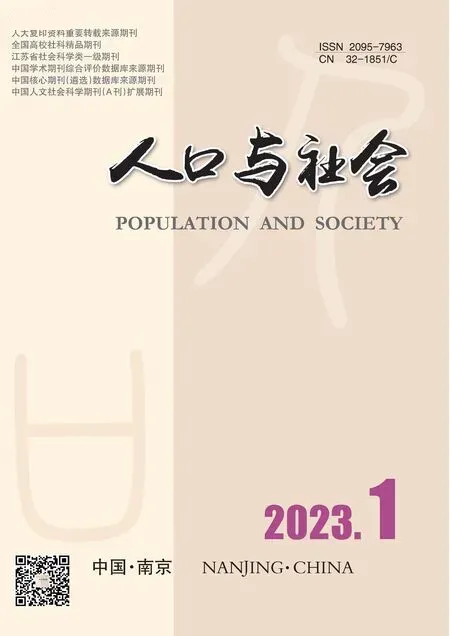三十年来关于生育水平的争论和对总和生育率的重新估计
乔晓春
(北京大学 人口研究所,北京 100871)
一、研究背景
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全面推行计划生育,到现在已经快五十年了。当时计划生育的核心目的是降低生育水平。20世纪70年代我国生育率出现了明显下降,进入80年代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1984年开始执行的“开口子”政策导致生育水平出现了明显的反弹。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年的总和生育率为2.31,明显高于“更替水平”。由于1990年以后历次全国性调查(包括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不包括2020年人口普查)得出的总和生育率值均大大低于人们的期望值,所以长期以来政府和学者普遍认为调查得出的出生人口存在严重的漏报,得出的总和生育率严重偏低。尽管如此,官方和学者当时普遍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妇女生育率确实出现了下降,但并不知道真实水平是多少。尽管国家统计局每年都公布年度出生人口、出生率,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或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也公布一些总和生育率的估计值,但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府部门对生育水平到底有多高从未达成过共识。
学者之间、政府和学术界之间针对生育水平的争议一直很大[1-6]。尽管一些官员也曾发表文章对普查数据做过一些评价[2,7],但国家统计局并没有公开承认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1995年、2005年和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以及历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直接计算得出的总和生育率是准确的。国家计生委从1990年以后“一直使用总和生育率1.8,或用达到更替水平或低于更替水平的模糊说法”,(1)详见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上)》,中国人口出版社,第112页。还在《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将总和生育率1.8左右作为未来人口发展目标。(2)详见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上)》,中国人口出版社,第16页。
尽管20世纪80年代生育水平比较高,但大家都知道有多高;而90年代以后大家普遍认为生育水平比较低,但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低。缺乏可信的生育率数据,直接导致人口学界在三十多年里很少有针对生育率的深入或系统研究,有的只是对出生漏报或生育率的估计,或者是在假定生育率准确的情况下做一些生育率变化或差异的比较分析。
1990年以后,中国的计划生育是在这种懵懵懂懂的状态下走了三十年,尽管国家在2013年和2015年两次调整了生育政策,但直到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官方才在三十年后第一次正式承认本次人口普查得出的1200万出生人口和1.3的总和生育率是准确的,而且学者也普遍认可这一结果。可以说这是三十年来官方和学者针对生育水平第一次达成共识。遗憾的是,我们在不知道生育水平多高的情况下将计划生育政策持续执行了三十年,这期间政府做过很多决策、发布过一些政策,计划生育工作也曾进行过调整和改革,也可能失去了很多原本应该抓住的机会。现在到了我们对以往走过的三十多年历程进行重新梳理和反思的时候了。
本文将在笔者发表在《人口与发展》2022年第5期的《对三十多年来中国出生人口的估计》[8]一文的基础上,重新估计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并在此基础上对以往学术界在生育水平上的争论和认识做一个讨论。尽管这种估计和讨论已经无法弥补过去在认识上和政策上的失误,但至少还可以弥补三十多年来一直搞不清生育水平所留下的遗憾。
二、对以往估计结果的回顾和讨论
1982年之前国家公布的人口数据基本上来自公安部门的户籍统计和人口变动登记。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之后,国家统计局于1983年末首次开启了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3)国务院办公厅1983年8月31日以国办发(1983)71号《关于认真做好一九八三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工作的意见的通知》规定,“望统计、公安、计划生育等各有关部门密切合作,认真做好这项工作,并应在今后每年进行一次,形成一项调查制度”。1990年之前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的人口变动数据均来自直接调查得出的结果,人们对人口普查或其他官方公布的出生人口、出生率和总和生育率数据并没有产生过太多的怀疑,对出生人口漏报的讨论不是很多。第一次对这些调查数据产生明显怀疑和激烈争论出现在1992年9~10月国家计生委组织的“38万人调查”结果出来以后,调查直接得出的1991年和1992年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65和1.52[1]。这一结果与刚刚公布的1990年人口普查得出总和生育率为2.31的结果相差甚远。很多学者如曾毅、于景元、袁建华等都得出该数据漏报严重的结论[1,9-10]。曾毅还对总和生育率进行了估计,并得出1990、1991和1992年总和生育率分别为2.43、2.20和2.10。在“38万人调查”之后,国家计生委也意识到出生统计漏报的严重性,并于1993年9~10月在河北和湖北两省随机抽取了16个行政村的4万多人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结果与统计上报数据进行比对,发现出生漏报率为37.3%[1,11]。尽管检验的出生漏报并不是针对人口普查或是统计部门给出的数据,但给人的印象却是出生数据漏报和瞒报现象已经非常严重。
统计部门在1990年人口普查结束后也发现1982年以来根据历次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公布的出生人口存在很大程度的漏报,从而在普查结束后立即对1982年到1989年期间曾经公布过的出生率数据进行了上调。(4)将1991年和1990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公布的1982年到1989年出生率数据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数据的变化。基于这样一种判断、规律和教训,1990年以后国家统计局不再直接公布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得出的结果,而是对直接调查结果进行调整后再公布数据。比如,将1993和1994年的出生率在直接调查结果的基础上分别上调了2.51和2.38个千分点,从而将1993和1994年的出生率从调查得到的15.58‰和15.32‰,直接提升到了公布时的18.09‰和17.70‰[12]。按照这样一种调整幅度,如果平均每年将出生率提升近2.5个千分点,意味着平均每年添加进去200多万出生人口,估计到2000年十年累计添加了2000多万出生人口。
添加进去的人口是否合适,需要通过2000年人口普查来检验。遗憾的是,普查结果并未证明这2000多万出生人口真的存在。2000年人口普查实际登记的(当年11月1日0时)人口为124261万人。而国家在普查之前已经公布的1998年和1999年年末全国总人口分别为124810万人和125909万人。(5)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1998年和199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参见中国政府网。实际上这些结果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公布后国家统计局对此又做了重新调整,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1年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给出的最新结果:1998年、1999年和2000年年末总人口分别为124767万、125786万和126743万。很明显,人口普查直接登记的总人口少于前两年年末总人口,这一结果很难被人接受。这样,2000年人口普查最终公布的全国总人口为126583万人,普查共计补进去2322万人,(6)在国家统计局于2002年8月份出版的《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编辑说明中明确指出:“本资料总人口(即通过个案数据汇总后得到的人口)为124261万人,比国家统计局根据快速汇总(或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发布的总人口126583少2322万人。”而且统计部门将补进去的这部分人以人口普查登记漏报1.81%的名义列入公布的全国总人口中。尽管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一号)”文后的注中明确指出,1.81%的漏登率是普查事后质量抽查得出的结果,但根据笔者的分析这一结果实际上来自人为的估计[13]。
不仅1992年“38万人调查”得出的总和生育率不可接受,1992年以后不管是统计部门还是计划生育部门历次调查得出的总和生育率结果似乎都“一致性地”偏低,与人们感知或认知的生育水平相差甚远。比如: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为1.43;1997年国家计生委组织的人口和生殖健康调查得到的1997年总和生育率为1.35。尽管这些结果具有很强的一致性,但绝大多数学者并不相信这些数据是真实、准确的,并发表了大量文章来论证和描述计划生育引起的出生人口漏报和瞒报,并认为这是最终导致调查出生人口偏少、生育率偏低的主要原因[14-18],这类判断当时在学术界和官方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国家计生委“中国未来人口发展与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在2000年初发布的《中国未来人口发展与生育政策研究》对此也进行了确认:“对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判断之所以是人口学界的难题,因为目前还没有令大多数专家和学者认同的能够准确反映生育水平的数据。”[19]“1990年以来所公布的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结果给人的感觉是,出生率或总和生育率出奇地低,低到令人难以相信的程度。时而见诸报端的超生瞒报、漏报的报导,使人们更怀疑上述公布结果的真实性。同时,试图找出漏报原因的多次局部复查也收效甚微。”
为了能够了解当时的生育水平,很多学者利用不同方法对1990年代总和生育率给出了各种各样的估计和修正(见表1)。张为民[2]等尽管给出了估计结果,但作者认为(估计结果显示的)生育率比政策生育水平还低,这是不可能的;反过来又进一步判断总和生育率是基于2000年人口普查0~9岁人口直接推算出的,所以认为0~9岁年龄人口存在一定程度的漏报。而郭志刚[3]给出的估计结果是所有估计结果中最低的,但他认为自己估计的结果“是比较可靠的”。 除了这两个比较低的估计外,其他学者的估计结果差异并不是很大,即1991年总和生育率都在2.0以上,到90年代末期基本上在1.7左右,中国人口信息中心估计出的2000年总和生育率最高,达到1.80。基于这些估计,学术界和政府基本上达成的共识是:生育水平从1992年开始下降到了总和生育率2.1的更替水平以下,即中国已经进入了“低生育水平”阶段。

表1 部分学者对1990年代总和生育率的估计
毫无意外的是2000年人口普查直接得出的总和生育率继续走低;意外的是总和生育率居然能如此之低,只有1.22。尽管此时绝大多数学者仍然认为真实生育水平不可能这样低,但调查得出的生育率长期的、一致性偏低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怀疑,并开始相信真实生育率可能确实很低,比如有学者提示出生漏报可能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并认为统计调查得出的结果真实地反映了生育率的下降[3-4]。但更多学者试图利用各方面的相关数据(包括计划生育数据、教育数据、卫生数据等)对2000年的“真实生育水平”进行估计,遗憾的是估计出的结果仍然是千差万别,估计的总和生育率基本在1.2到2.3之间变化[23]。这样一个宽泛的结果体现的已经不是数据差异,而是认识上的差异,争论也就从此开始了。比如,郭志刚[3]估计的2000年总和生育率为1.23,给出的判断是因为“所有应用实际调查和普查数据直接计算的总和生育率都表明2000年的TFR在1.3左右”,所以作者“更倾向于相信1990年代后期TFR已经处于1.5以下的可能性很大”。而梁中堂[24]和张为民[2]等依据小学入学登记数据对总和生育率进行估计,前者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妇女在1982—2000年平均的总和生育率为2.3;后者推出的结果是2000年总和生育率下限为1.63,上限为2.0,实际水平应该在1.8左右。马嬴通[5]对90年代总和生育率的判断是:“生育水平低于或大大低于1.8的任何数据,都难以令人置信”,他同时认为“本世纪初(总和生育率)最乐观的估计也低不过1.8~2.0,接近于实际的估计约为2.0左右”。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学者都对2000年的总和生育率给出了估计,比如王金营[21]估计的结果是1.70,Retherford[25]等的估计为1.5~1.6,张青[26]的估计为1.66,翟振武[6]的估计为1.68。
不幸的是,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得出的总和生育率比2000年还低,只有1.19。学者们对这一结果的看法与2000年普查完全一样,仍然认为数据不可信。很多学者依据2010年普查数据,以及相关的教育、卫生或公安数据来估计2000年以后的出生人口和总和生育率(见表2)。尽管估计结果整体上低于2000年之前,但在趋势上既有上升又有下降,还有估计结果表现为无规律波动;不同人估计的差异相对比较大,基本上在1.2~1.9之间波动,几乎找不出一致性的规律。2010年以后尽管一些学者转向用公安、教育和卫生数据,或使用不同的方法进行估计,但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这些其他来源的数据在多大程度上是准确的,是否能作为估计真实结果的依据则是令人怀疑的,而且使用者也并未给出充分和可信的论证。尽管如此,对于学者来说仍然分为两派,一派认为生育率并不像普查给出的结果那样低,比如翟振武等[27]估计的2010年总和生育率为1.63,陈卫[28]得出的结果为1.62;另一派继续坚持认为普查得出的生育率基本上反映了真实事实,比如郭志刚直接对六普和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总和生育率进行分析并认为,总和生育率低并不是严重的出生漏报所致,而是“具有人口发展自身的内在原因”[29-30]。

表2 部分学者对2000年以后总和生育率的估计
尽管多数人口学者都不相信总和生育率只有1.19这样低,但却相信中国的生育水平已经比较低,并开始主张尽快放开生育政策,最终促使国家于2013年底实施“单独二孩”政策,随后的2015年底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七普”数据公布后又立即在2021年5月底实施了“全面三孩”政策。
三、总和生育率的估计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是一次高质量的调查,一方面普查方法有了明显的改进,特别是“户籍人口”和“现有人口”的双登记,导致“人头”漏报大幅度减少,另一方面普查事后质量抽查也得出普查漏登率只有0.05%。(7)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一号),2021年5月11日发布。本次普查数据为我们重新估计以往30多年的出生人口或出生率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笔者在《对三十多年来中国出生人口的估计》一文中使用了2000、2010和2020年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分性别和年龄人口数据,用逆存活率的方法估计了1986年到2022年三个基准人口下历年出生人口(见表3)。这里基准人口1实际上是三次普查同一队列中人口数最多的;基准人口2是三次普查同一队列数据一致性最好的一对数据中数值最大的;基准人口3直接使用了2020年人口普查分年龄人口数据。
下面我们用出生人口和总和生育率的关系[39],借助已经估计出的历年出生人口数来估计1986年到2022年的总和生育率。
出生人口和总和生育率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以下公式来表示:
在这里,TFR(t)为t年总和生育率,B(t)为t年出生人口,K′(t)为相对固定系数,而且
这里,hx(t)为t年x岁标准化生育模式,Wx(t)为t年x岁育龄妇女人数。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首先,用1990、2000、2010和2020年四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出各个普查年份的K′值(以万为单位)。其次,在两点之间做线性内插,得到各个日历年的K′值,见图1。

图1 四次普查的K′值和内插结果曲线
最后,代入上面公式计算出各年的总和生育率,估计结果见表3和图2。

表3 按不同基准人口估计的1986—2020年出生人口、总和生育率和K′值

图2 1986—2022年总和生育率变化曲线
因为三个基准人口估计出的出生人口只在1986到1995年之间存在差异,1995年以后的估计结果完全一致,所以得出的总和生育率在1986到1995年略有不同,主要是基准人口1估计得出的总和生育率更高一些,基准人口2和3基本相等,到1995年以后三个结果完全相等。
从估计的结果看,20世纪80年代末期总和生育率维持在2.5以上的高位,特别是估计得出的1990年总和生育率为2.48到2.67之间,这一结果比国家公布的2.31高了7.4%到15.6%;令人意想不到是,估计得出的1991年总和生育率在2.02到2.13之间,这意味着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在1991年就达到更替水平。在随后的10年里,总和生育率几乎是直线下降,1999年下降到1.42,这已经低于国际上公认的1.5超低生育水平。而且总和生育率在超低生育水平上保持了7年,并在2002年达到1.36的最低值,然后触底反弹,2012年达到1.83的新高。尽管2013年底国家实施了“单独二孩”政策,但2014年的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80,略高于2013年的1.77,仍然低于2012年的生育水平。2015年总和生育率再次下降,跌至1.69。而2015年底出台的“全面二孩”政策导致总和生育率在2016年和2017年再次出现小幅反弹,分别为1.83和1.84。2018年以后出现大幅度下降,以至于2020年总和生育率出现新低,只有1.31。2021年和2022年仍然在继续下降,2022年甚至出现了人口负增长。
总之,从1990年开始到2020年结束,中国妇女生育水平经历了大幅度下降、逐步回升和再次大幅度下降的过程。这个过程在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出来之前我们是不知道的。尽管有些学者也曾利用这期间人口普查数据或其他来源数据对某一阶段的总和生育率做过估计,但是由于估计结果差异很大,各结果之间并未显示出一致性的规律,没有得到学术界和官方的承认。
四、本文估计结果与以往估计结果的比较
从表3和图2中可以看出,总和生育率从1986年到1990年期间一直处于高位波动,没有任何下降的预兆。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尽管计划生育工作会继续加强,但生育率很难出现大幅度下降,包括当时国家计生委在1990年测算和制定1991年到2000年十年人口发展规划时,设定总和生育率从1990到1992每年下降0.05,从1992到1997每年下降0.04,从1997到2000每年下降0.03,期望在十年内将总和生育率从1990年的2.31控制到2000年的1.92。(8)参见陈胜利、赵璇主编:《人口统计与计划》,中国人口出版社,1991年6月,第313页(表14 1991—2000年人口计划指标测算方案)。然而,估计的结果显示在1992年总和生育率降到1.89到2.06之间,已经接近“十年规划”时给出的2000年1.92的目标。遗憾的是,整个90年代过去以后,我们并不知道当时制定的“十年规划”是否完成了、完成到了什么程度,因为没有人相信2000年人口普查得出的总和生育率结果,而且整个90年代官方和学者也都未给出可信的数据。只是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公布以后,一些学者才利用本次普查数据对1991年到2000年总和生育率进行了估计(见表1)。曾毅曾估计中国1990、1991和1992年总和生育率分别为2.43、2.20和2.10。现在看,这种估计结果与本文估计结果比较接近,只是1990年的结果略低于本文的估计,而1991年结果与本文估计接近,1992年结果则略高于本文的估计。图3给出了部分学者得出的结果与本文估计结果的对比,很明显中国人口信息中心、王金营、翟振武和陈卫给出了比较高的估计,而张为民和崔红艳、郭志刚则给出了比较低的估计。这里不管是较高估计还是较低估计,总和生育率在整体上仍在下降,而不存在上升趋势,这一点在学术界当时就达成了共识,并认为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已经进入低生育水平。

图3 本文对1991—2000年总和生育率的估计与部分学者估计结果的比较
200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也承认“生育水平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强调“稳定低生育水平是今后一个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称其为“一个新的重要发展时期”,并在这个前提下,“我国人口将由低增长逐步过渡到零增长,人口总量达到峰值后(接近16亿)开始缓慢下降”。遗憾的是,此时尽管知道处于低生育水平,即总和生育率小于2.1,但不知道生育水平到底有多低。
“稳定低生育水平”文件发布后,因为当时连生育水平是多少都不知道,所以各地对如何做好稳定低生育水平工作感到十分困惑。感觉生育水平已经非常低的东部沿海和东北地区仍然要继续坚持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感觉生育水平还相对较高的西部和少数民族地区也不清楚是应该继续降低生育水平还是保持生育水平不下降。从计划生育工作上看,在继续坚持现行生育政策的前提下,生育水平的高低完全是由基层计生工作执行力度决定的,力度大一些生育率会下降,力度小一些生育率会升高,力度保持不变才可能保持生育水平不变。在对基础计划生育工作进行评价时,很难认为生育率下降或生育率提高都是工作没有做好,只有生育率保持不变才算工作做好了。所以,“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政策”对实际计划生育工作来说是一件很难解释、也很难操作的事情,再加上真实的生育水平又得不出来就更增加了工作难度。在这种目标不清晰、定位不明确的情况下计划生育又走过了十多年的时间。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出来以后,一些学者们又开始利用本次人口普查数据和相关数据来对前十年的总和生育率进行估计。陈卫和朱勤估计的2000年到2005年的结果与本文估计结果比较接近,只是还略低于本文的结果,但是到了2005年以后本文估计的总和生育率出现持续的上升,而他们的估计结果基本没有变化且到最后出现大幅度下滑;崔红艳等和赵梦晗两篇文章的估计结果非常接近,但是他们的估计结果在2000年到2005年明显高于本文估计的结果,而2005年之后则明显低于本文的估计;陈卫和张玲玲的估计结果与本文估计结果在趋势上正好相反,2009年明显高于本文的估计,之后则显著低于本文的估计;陈卫和段媛媛与陈卫在2021年的估计结果在水平上有一定差异,但在趋势上几乎完全一致,而本文的估计结果明显高于他们的估计结果,但却显示出同样的波动趋势,只是本文估计结果的波动幅度明显小于他们的估计。详见图4。

图4 本文对2000—2019年总和生育率的估计与部分学者估计结果的比较
五、总结和评论
纵观学者们以往对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的估计和本文的估计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判断:
1.中国妇女生育率从1992年就开始低于2.1的更替水平。本文的估计结果与曾毅教授早期得出的结果都证实了同样的结论。国际上通常把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称为“低生育率”,然而即使实施了“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生育政策,自1992年以后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再没有回到过更替水平之上,这意味着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已经保持了三十年,而且将长期持续下去。
2.从1986年以后到2013年之前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并未发生过改变,工作也在持续地推进,但生育水平却出现了明显的、甚至是大幅度的波动。这里有两件事情是出乎意料的,一个是从1990年以后生育率出现大幅度下降,而且在1999到2005年期间居然已经进入了超低生育水平。如果这一结果在当时就能够被确认,可能在2000年之后就应该把调整生育政策纳入议事日程,而不是在2010年之后。另一个是人们一直认为在计划生育政策干预下生育率应该不断下降,哪怕下降的幅度小一些,很难想象会出现明显的反弹。这可能跟2000年发布“稳定低生育水平”政策有关,因为在这之前计划生育工作方向是明确的,即降低生育率,这之后似乎失去了方向。这表面上看是放松了工作,但却起到了放开政策的效果。
3.从1999年开始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首次低于1.5,进入超低生育水平。一般来说,总和生育率低于1.5被称为进入“低生育陷阱”。然而,此次掉入“陷阱”并不是自发的结果,而是计划生育政策干预和人们生育意愿下降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低生育陷阱”理论并不适用于中国当时的状况,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生育率在跌入“陷阱”的几年后又自动“爬”了出来,而不是继续“陷”下去。不幸的是,从2019年开始生育率再次掉入“陷阱”。与前一次掉入“陷阱”性质不同的是,这次是在生育二孩容许空间内的“自发”结果,此时走出“陷阱”将更为困难。
4.从2002年以后总和生育率一直处于上升的态势,到了政策调整之前的2012年总和生育率就已经升高到1.83,这与两次政策调整没有任何关联,此时的生育水平比“单独二孩”政策放开后的2014年总和生育率还略高;尽管“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导致了2016年和2017年总和生育率比2015年略有升高,但与2012年的总和生育率几乎持平。政策调整之前和调整之后生育水平几乎无差异,这意味着政策的调整对于提高生育水平几乎是无效的。
5.尽管2018年后媒体上出现了鼓励生育的宣传,甚至有些地方还出台了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此后的总和生育率不仅没能够保持住2016年和2017年1.8的水平,甚至出现了断崖式下降。这不仅意味着政策的微弱效果已经在2017年之前释放完毕,也意味着从2016年和2017年开始适龄生育人群的生育意愿就出现了明显下降,从而导致在可以生育二孩的自由选择空间中,主动选择生育的育龄人群迅速减少。过去是“想选,但不让选”,现在是“让选,但不想选”。这并不是人们的观念突然发生了变化,而是“让”的时间来得太晚了。
6.尽管几乎所有学者和官方都认为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直接得出的总和生育率为1.22 和1.19完全不能反映真实水平,而且几乎所有估计结果都大大高于这个水平,但郭志刚教授在2004年估计中国2000年总和生育率为1.23,并认为人口普查得出的结果是真实的,特别是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存在严重出生漏报的大环境下能够给出“更倾向于相信1990年代后期TFR已经处于1.5以下的可能性很大”的判断,是非常可贵的。遗憾的是当时并未得到更多学者的支持,也未得到政府的关注。
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自1986年以后的三十多年来历次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得出的出生人口和总和生育率都是准确和真实的,那么中国会发生什么?估计我们不需要等到2015年才放开“全面二孩”政策,更不至于在2022年中国人口就进入了负增长,因为我们至少有两次可以放开生育政策的机会,一次是1992年进入低生育率之后,另一次是1999年进入超低生育率之后。遗憾的是,因为我们得不到、也不知道真实情况,所以也就错过了这样的机会。如果生育政策的调整比现在早10年、15年、甚至是20年,生育的主体人群将是部分“60后”和全部的“70后”,她们中的很多人非常渴望生育二孩,甚至三孩,只是由于当时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限制了她们的生育。不幸的是,2015年底才出台的二孩政策,让70后“整建制”地错过了生育时机,最终导致全社会出现严重的低生育困扰和焦虑。人们在犯错误以后通常会提醒要“吃一堑长一智”,但这句话放在人口问题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人口运动是不可逆的,一旦错过“窗口期”,政策的调整就会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