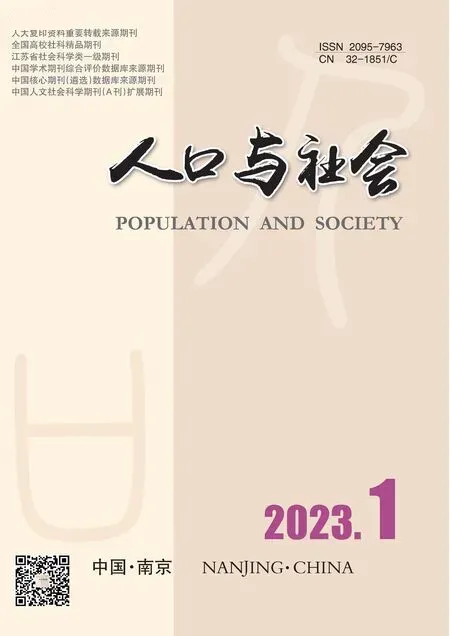优势视角下家庭养老功能复归与重塑的国际经验与中国路径
李 静,闫彩旭,刘华清
(1.云南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2.河海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由2000年的10.33%上升到2010年的13.26%以及2020年的18.7%;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由2000年的6.96%上升到2010年的8.87%以及2020年的13.5%。(1)根据国家统计局官网第五、六、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整理而得。老龄化进程之快,老龄化程度之深,对我国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考验。新考验亟需新举措应对,《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强调,要“注重发挥家庭养老的作用”,“鼓励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就近居住或共同生活,履行赡养义务、承担照料责任”。(2)详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2021年11月24日,http:∥www.gov.cn/zhengce/2021-11/24/content_5653181.htm受家文化与孝文化之影响,家庭养老长期以来是中国主要的养老方式。与其它养老方式相比,家庭养老在提供养老资源、维系家庭情感、改善老年人精神健康方面具有不可比拟之独特优势。然而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我国家庭形态及特征发生了极大变化。一方面,我国家庭规模小型化特征日趋明显。我国平均家庭户规模从1953年的4.33人下降到2020年的2.62人,(3)根据国家统计局官网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整理而得。家庭规模缩小导致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与分化;另一方面,家庭成员流动性日趋增强。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全国人口中流动人口为3.76亿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流动人口增加1.54亿人,增长69.73%。(4)详见: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七号)》,2021年5月11日,http:∥www.stats.gov.cn/ztjc/zdtjgz/zgrkpc/dqcrkpc/ggl/202105/t20210519_1817700.html家庭成员流动性增强导致“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观念逐渐淡化,家庭养老的服务功能被极大削弱。正因如此,家庭养老的供需张力不断突显,亟需相关部门重视家庭养老功能的复归与重塑,充分发挥家庭在养老服务中的基础性作用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同为东亚国家的日本、韩国、新加坡,近年来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存在劳动力不足、社会负担加重等诸多问题,经济发展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同时,日韩新三国同处“儒家文化圈”[1],深受家文化及孝文化之影响,历来注重家庭在养老中的作用,强调子女对老年人的赡养与扶助。正因为中国与日韩新三国具有人口老龄化进程快、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家庭养老传统悠久等相似国情,日韩新三国各自优势及有益经验可为我国家庭养老功能之重塑提供重要借鉴。
二、家庭养老功能复归与重塑之理论视域:优势视角
(一)优势视角的理论阐述
优势视角理论兴起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其创立者萨利贝(Saleebey)认为,优势视角的实践取向不是立足于问题本身,而是要立足于探索和利用个体及其环境的优势和资源。这一视角强调人的尊严和价值,强调人具有内在的转变能力和优势资源。概括地讲,优势视角理论就是要求转换视角,不再聚焦于问题与缺陷,而是着眼于对象优势,以发掘并利用其优势和资源为出发点,协助其在挫折与不幸中寻找希望,并从逆境中挣脱出来,最终达到目标及实现梦想[2]。随着优势视角理论的不断发展,其展现出了强大的学科生命力和实践包容性,被广泛运用于老人服务、家庭实践、社区发展及社会政策、精神健康等实务领域。2004年萨利贝的《优势视角:社会工作实践的新模式》被引入中国,这一理论开始受到更多中国学者重视,被应用于家庭亲子关系、残疾人就业、老年人心理干预等领域[3]。本文以优势视角来探究家庭养老功能的复归与重塑,聚焦主客观优势及内外部优势(如图1所示),发掘并利用这些优势,以此推动中国家庭养老功能的复归与重塑。

图1 家庭养老功能复归与重塑之优势
(二)优势视角与家庭养老功能复归与重塑之理论耦合
优势视角理论包括四条最基本信念:一是赋权(Empowerment),指赋予和充实人的权力,挖掘或激发人的潜能的一种过程、介入方式和实践行动,即“去标签化”,改变个体的思维定式,引导他们认识到自己的潜能,重新树立希望[4]。二是成员资格(Membership),即每个人都有希望在一个可靠的团体或社区中成为被尊重的社会成员的需求,所有成员享有平等的各种权利[5]。三是抗逆力(Resilience), 又称为复原力,即个体在困境中依靠内外部的优势和资源克服困难,展示积极适应结果的能力[6]。四是治愈与整合 (Healing & Wholeness),即治愈个人的创伤,整合个体存在的各种内外部资源,将个体放置在社会环境之中,优化个体与社会的互动,避免出现个体与社会环境脱节的情况[4]。
具体来说,其一,赋权是指政府通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手段引导社会组织、企业等为家庭赋能,使家庭成员重新认识到自身潜能,重新树立信心和希望。家庭成员受工作压力增大、养老负担加重等因素影响易产生悲观情绪,未能认识到自身和外部社会潜藏的资源从而丧失对家庭和生活的希望。通过赋权,政府能够了解家庭成员之需求,实现家庭、社会组织、企业等多元主体的资源链接,帮助家庭成员从不利环境中摆脱出来。其二,成员资格是指每个老年人都应该得到家庭成员和社会的尊重,平等享有获取各种内外部资源之权利。身体机能的退化和劳动能力的下降使得老年人内心极易受到刺激和伤害从而封闭自己,不敢面对生活及外部世界。成员资格的理念强调家庭既要注重抚育,更要注重赡养,家庭成员不仅需要了解和满足老年人需求,而且需要营造孝亲敬老之家庭与社会氛围,使老人融入家庭、融入社会。其三,抗逆力是指老年人拥有利用内外部优势和资源并提高抵抗逆境之能力。老年人虽然会面临疾病、孤独、自身价值难以实现等困境,但同样拥有自身优势和资源,同样拥有改变现状之愿望,故需协助老年人面对现实、激发其对生活的积极性,促使其努力发挥自己优势以实现自身发展。其四,治愈与整合是指老年人需要适应新身份和新生活,借助现代科技,充分彰显其人格威望、知识经验、思想政治素质等自身优势,与社会环境进行良好互动以转变自己的消极情绪并发挥余热。
三、日韩新三国家庭养老优势探析
优势视角强调任何个体都是有优势的[7]。基于优势视角四大基本信念,本文将日韩新三国家庭养老之优势界定为三大维度(如图2所示):制度优势即为家庭养老赋权,指日韩新三国包括经济鼓励、法律约束政策在内的顶层设计;文化优势即成员资格,指日韩新三国家庭养老所具备的家文化、孝文化根基;技术优势即抗逆力、治愈与整合信念,指日韩新三国家庭养老所具备的智慧化优势资源。其中,制度优势与技术优势为家庭养老之客观优势,文化优势为家庭养老之主观优势。

图2 基于优势视角基本信念的家庭养老功能复归与重塑路径
(一)以制度优势赋权:经济鼓励+法律约束
日本、韩国和新加坡都十分重视将家庭养老的经济鼓励政策与法律约束政策结合起来以强化家庭养老功能的制度赋权。通过赋权增能,日韩新三国整合政府、企业、社会组织资源,激发家庭成员内生性动力,助其从不利环境中摆脱出来,重新树立信心和希望,提高赡养能力。日本受儒家文化影响,具有较高程度的“再家庭化”倾向,实施发展型家庭政策并将家庭作为整体考虑。为促进家庭赡养行为,日本推行住房支持政策,如1972年开始推行“高龄者同居住宅”项目,三代居家庭入住时可享受优先程序[8]。“抚养扣除”政策是日本激发家庭成员孝老动力的又一重要制度。日本《所得税法》规定,依据老年人年龄及共同居住情况,赡养老人的家庭成员可享受一定额度的税收扣除,如与70岁以上老年人共同居住的扶养人,其居民税可获得45万日元的扣除额度[9];1978年,日本政府在所得税扣除与个人居民税扣除额度中导入配偶补助费[10],以提高家庭成员的社会认可度,鼓励家庭成员赡养老人。日本还实行了公共养老金制度,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以来,日本高龄者家庭的收入中,公共年金等所占比例约为六七成;收入全部来自公共养老金的高龄者家庭合计约为五六成。(5)详见:日本厚生劳动省,《令和2年版厚生労働白書-令和時代の社会保障と働き方を考える》,2020年10月,https:∥www.mhlw.go.jp/stf/wp/hakusyo/kousei/19/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实施增加了日本高龄家庭的收入,减轻了高龄老人的生活负担,进而减轻了家庭照料者的赡养负担。同时,日本社会救助制度也起到间接强化家庭养老功能之作用,日本于2014年开始实施的《生活保护法》将家庭赡养情况作为申请人申请救助之依据[11]。此外,日本在增强家庭成员照护能力的同时,也致力于规范其行为。《老年人福利法》《老年人保健法》《介护保险法》明确家庭养老各行为主体权责边界[12];《防止虐待老人法案》监督家庭养老服务,规范家庭照料者赡养行为。
韩国具有家族保护特征,家庭在老年社会服务中扮演主要角色,国家则借助政策、制度鼓励家庭赡养老年人[13]。为实现多维赋权家庭,韩国采用直接经济政策与间接经济政策相结合的方式,为家庭成员提供若干优惠,从而有效化解家庭养老功能发挥中的矛盾。如韩国残疾老年人与困难老年人家庭可享受税收、居住优惠;1992年制定的优惠税制政策规定三代同居家庭赡养老人5年 以上,可减少财产继承税,以此激励三代同住[14]。韩国于2008年推行的长期照护保险规定,对住在边远地区需要照护的人的家属实行现金给付。同时,韩国注重通过法律政策的约束力,发挥家庭养老的制度优势。韩国早在1961年和1977年就分别制定《生活保护法》《医疗保护法》,将家庭确立为赡养老人的首要责任承担者[10];而后,1981年通过的《老年人福利法》明确了家庭的赡养责任;2006年公布的《住房认购制度改革方案》规定赡养老人的家庭成员可获得优先购房机会[15];2007年颁布《孝行奖励资助法》宣传孝道文化、重视塑造家庭价值观以维护家庭养老功能。此外,韩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对老年人提供的居家照护、昼夜照护、短期照护等服务,也给予了家庭照料者喘息机会,节约了家庭成员的时间资源,促进家庭内部增能。
新加坡侧重借助组屋政策,建立建屋发展局(Housing & Development Board),发展家庭养老服务事业,对老年家庭或有老人的家庭的住房配置给予相应优待措施。为应对人口老龄化,1999年新加坡老龄问题跨部委员会首次提出“就地养老”的政策理念,以帮助老年人在熟悉环境中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需求得到满足。同时,为鼓励家庭成员与老年人就近居住且发挥家庭对老年人的支持作用,建屋发展局于2001年起推出“接单建设”(Build-to-Order)政策以进行公共住房的申请和预售,并在该政策下推出“多代优先计划”(Multi-Generation Priority Scheme)、“已婚子女优先计划”(Married Child Priority Scheme)、“老年人优先计划”(Senior Priority Scheme)等计划[16]。此外,根据建屋发展局文告,包括兀兰、义顺和盛港在内的八个市镇都推出了三代同堂组屋单位,其中,盛港的三代同堂组屋单位售价甚至比同区五房式还便宜。这些组屋政策的出台减轻了家庭成员的经济负担,可使家庭成员更好地照顾老年人。新加坡还于2019年推出居家看护津贴政策以取代之前的女佣津贴,这一新津贴具有金额更多、用途更广、灵活性更强等特点,看护者可向政府申请每月200元津贴抵消聘请女佣费、复诊交通费、日间护理中心费用等看护支出,以此鼓励家庭成员赡养老年人。此外,新加坡制定了专门的《赡养父母法》,规定不能完全自我供养的父母可向法庭申请赡养费,并设立专门的赡养父母仲裁庭以推动家庭成员责任落实和保障父母合法权益[17]。
(二)以文化优势彰显成员资格:儒学传统+尊老氛围
成员资格的获取是老年人社会融入的重要条件,日韩新三国通过发挥文化优势营造尊老敬老的和谐家风与社会氛围,满足老年人不同需求,促进其真正融入社会。日本深受中华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之影响,将孝顺父母、尊敬长者作为基本道德准则[18]。二战前,“家”制度在日本起主导作用,结婚的长子及其妻子与父母同住,承担为父母养老送终的义务;同时,近亲、邻里相互扶助的伦理道德规范促使子女承担赡养老年父母之义务,解决老人赡养问题。二战后,随着民法的修订,赡养父母的义务扩大到了所有子女[19]。如今,日本仍维系着孝亲敬老的传统,将每年9月15日确定为“老人节”(又称“敬老日”),并将每年9月15日至9月21日定为“老人周”,鼓励人们加强对老年人的关心与了解;同时,日本还开展了多种多样的老年人福利事业,努力营造为老服务的社会氛围。
家庭中心主义与“孝”思想是韩国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一方面,家庭中心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和基本原则对个人的生活方式和家庭关系起到规范作用。另一方面,“孝”思想为营造全社会孝老氛围、激活老年人成员资格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基。敬老爱老是韩国的一种社会风气,如公共交通工具设敬老席,对老年人使用敬语,社区定期免费邀请老年人参加敬老宴会[20]。建立老年人福祉馆、敬老堂、老年人教室等设施,为老年人提供多种信息及服务,满足其参与社会活动之需求[21]。同时,韩国在节日方面也体现了对老年人的尊敬,如韩国有“行孝休假日”,并将每年10月份定为“孝之月”;1973年起,将原来每年5月8日的母亲节改为“敬老节”,对70岁自理老人发放终身优待证;韩国的中秋节被称为“秋夕”,在这天除了全家团聚之外,人们还追忆祖先恩德,以祭祖和扫墓的方式表现孝道。此外,尊老敬老也体现在韩国教育中,如韩国的《孝行奖励资助法》规定将孝行教育纳入幼儿园、小学及中学课程中,在婴幼儿保健所、社会福利机构等进行孝行教育,以加强社会对“孝”的关注并且激发子女“孝”的意识[22]。
属于儒家文化圈的新加坡将“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作为“治国之纲”和社会道德标准[23],推崇儒家文化并重视公民道德教育,注重培养公民孝道观念,提倡从小培养孩子尊老爱老、敬老孝老意识。新加坡教育部于1990年向全国小学推行《好公民》教育教材,大力弘扬中华文化“仁义礼智信”和“孝”等十五大价值观;之后于2013年修订为《好品德 好公民》,依然大力彰显“孝”之理念。除此之外,新加坡也着力营造尊亲敬老的社会氛围,社会爱心人士、社团组织、企业等逢年过节便会为老年人发“度岁金”,设宴招待老人;一些团体定期举办义工照顾弱势人士、捐赠食物与日常用品等活动,以体现对老年人的尊敬与关爱。
(三)以技术优势提升抗逆力:科技赋能+适老改造
抗逆力是一种自我适应的过程,治愈与整合需要个体与社会进行良性互动。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与现代科技的推广,家庭养老功能之发挥大受其益,在这方面,日韩新三国表现十分突出。日本智慧养老技术是完善家庭养老功能之重要手段,养老辅助产品的研发与相关技术的发展有助于提高老人抗逆力,改善其生活质量并促进社会参与。日本还鼓励企业展开众多“定制服务”。为帮助老年人消除数字鸿沟并融入智能社会,日本电信运营商都科摩公司专门设立“智能手机教室”,帮助老年人熟练使用智能手机,便利老年人与家庭成员远程交流;同时,为让老年人更好地理解家电功能,日本一家企业在销售面向老年人的产品时,特意招聘60岁以上人群作为工作人员,既可增加受雇老年人收入,帮助其实现自身价值,还可减轻家庭成员赡养老年人的经济负担并节约时间成本。(6)详见:人民网,《世界各国养老新趋势 中国将社保征缴划给税务》,2018年12月29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8/1229/c1002-30495776.html除此之外,日本政府还出台《机器人白皮书》, 提议通过机器人技术解决老龄化及人口减少问题,并研发具有与老人交流、保护老人安全等功能的老年服务机器人,用于监测与照料老人日常生活及身体健康。日本电气株式会社研发的智能鞋可监控老人行踪, 防止老人走丢[24]。通过机器人、智能鞋等智能设备,家庭成员可随时随地监测到老年人的健康与安全情况,一旦老年人发生危险,家庭照料者即可最快做出反应。
韩国推动家庭养老功能重塑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大力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及发展智能家居产品,为家庭养老技术赋能。韩国一直重视智慧城市建设,已进入智慧城市建设3.0时期,2019年韩国制定《智慧城市综合规划(2019—2023)》,推动智慧养老进一步发展。(7)详见: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国外智慧城市发展现状及经验借鉴》,2021年12月1日,http:∥cicscert.org.cn/web_root/webpage/articlecontent_101006_1465859188637831169.html基于智慧城市的发展,韩国健康促进发展院实施基于物联网的老人健康管理服务示范项目,利用ICT技术,由保健中心专家在线了解老年人生活习惯并提供个性化健康咨询,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为家庭成员节省了送老人去医院的时间。与此同时,韩国物联网技术助力家庭实现家居智能化,如智能娃娃的设计既可排遣老人的孤独与寂寞,亦可帮助家庭照料者看护老人;智能安心机的研发可实时监测老人状况,确保独居老人安全以缓解子女不在老人身边时的担忧。
新加坡为应对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提出“智慧国”计划,通过数据全面共享与技术广泛应用,让全体老人享受科技红利以实现原地养老。老年人监测系统成为“智慧国”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建屋发展局测试开发的“居家老人智慧警报系统”可监测老年人生活作息,老年人若遇突发状况可启动紧急按钮及时向家人或看护者求助;“夜监智能地毯”的研发可通过互联网技术将老人活动数据上载至云端,一旦监测到不寻常动态便会发送手机短信给家庭成员;红十字会试行的“居家监测辅助服务”计划,为每户家庭安装感应器,一旦探测到老人日常作息有异样就可立即通报亲属为老年人提供援助。发展智能公寓,引进智能家居,进行适老改造,营造适宜老年人的居住环境,是新加坡发挥技术优势的另一重要经验。新加坡顺福轩(Jade Scape)公寓引进遥控系统、体温检测系统等智能住宅管理系统,家庭成员通过手机应用即可远程监测老年人健康状况、活动状况;2017年建成的海军部村庄(Kampung Admiralty)把组屋和包括超级市场、医疗中心、社区花园、托儿所以及熟食中心等在内的许多设施综合在一起,为居民提供“一站式”的生活便利服务,组屋内扶手与防滑地砖等设备的安装极大提升了老年人居住环境的安全性与舒适性。除此之外,在该社区内父母可与已成家的子女毗邻而住以便家庭成员关心与照料老年人,更好地发挥家庭养老功能。
四、中国家庭养老功能复归与重塑之路径
历史和现实无不彰显家庭养老在中国养老系统中不可动摇的重要地位,以优势视角为指导,借鉴地缘相通、文化相亲的日韩新三国经验,充分挖掘家庭养老功能之优势潜能,彰显制度、文化、技术优势,方可提高家庭内生发展能力,推动家庭养老功能逐步复归与重塑,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实现习总书记强调的“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8)详见:央视网,《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2021年10月13日,http:∥www.news.cn/politics/2021-10/13/c_1127954637.htm之宏伟目标。
(一)多维赋权:政府支持家庭
优势视角理论认为问题本身不是痛点,关注案主所处环境中多元优势和资源才是关键点,提倡以积极的态度和方式与环境进行连结和合作[25]。这一优势视角理念为家庭养老功能之复归与重塑提供了可行思路。当前如何激发政府主体在重塑家庭养老功能中的潜能,优化政府支持家庭之有效路径,成为复归与重塑家庭养老功能的关键之举。有鉴于此,赋权意味着政府需要与家庭积极连结,挖掘家庭内部优势资源并明确家庭赡养老人之义务,提高家庭内生发展能力。
第一,发挥制度优势,提供政策保障。一是政府依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老年人养老需求,适当对照料老人的家庭成员进行经济补偿,可借鉴新加坡“居家看护津贴”政策,每月给予家庭子女一定的津贴以弥补其劳动力损失或雇佣看护者所支出的费用,从而推动建设养老、孝老、敬老的社会环境。具体而言,我国家庭成员照料老人的经济补偿可包括直接现金补贴、社会工资、赡养老人税收减免等,还可包括就业补贴、住房补贴、探亲补贴等。二是政府通过制定喘息服务制度、家庭成员照料培训制度、康复制度等支持家庭成员为老年人提供服务。最早提出长期护理保险的日本,为缓解家庭成员照料压力,增设了夜间紧急家庭医疗保健服务,让家庭成员从沉重的养老负担中解放出来。我国可探索建立并进一步优化喘息服务制度,完善喘息服务准入条件,对家庭成员、老年人情况进行评估,符合喘息服务条件的家庭成员即可享受政府为其提供的喘息服务。同时,江苏苏州等地推行的“家庭养老夜间照护床位”亦值得关注。三是加强对家庭子女赡养老年人的监督与管理。新加坡于1994年颁布的《奉养父母法》对家庭成员养老服务进行监督;1995年颁布的《赡养父母法》规定拒绝给予父母赡养费的家庭成员将受到法律制裁。我国也可建立多位阶、多层次、多维度的涉及家庭养老之法律制度,如《家庭照料条例》《家庭养老服务支持条例》等,在其中规定养老服务职责与内容、政府对子女供养父母的监督工作、不赡养者的惩罚机制,规范家庭与其他主体间关系并将其法律化、制度化、具体化、规范化,为家庭养老功能之复归与重塑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第二,发挥文化优势,塑造尊老氛围。一方面,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发挥典型人物正向示范效应以增强内生性孝老动力。内在文化素养之提高及孝老意识的培养是推动家庭养老的重要因素,要深入挖掘尊老孝老先进事迹和典型人物,通过网络平台等渠道大力褒扬,不断激励家庭成员孝老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鼓励构建和谐家庭,加强学校教育,推动家校共育孝老文化。和谐家庭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引导家庭成员共同营造尊老爱老的家庭氛围,同时通过学校教育,潜移默化地提升整个社会的孝老意识、尊老观念、敬老行为。第三,发挥技术优势,搭建智慧平台。政府可通过集中培训、送教上门、远程培训等方式为家庭照料者提供适当技能培训,提高其照护能力;依托智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实现养老服务供需精准匹配,并实时监督居家上门服务质量,减少家庭成员时间成本;支持与推广家庭养老床位,为老年人提供专业照料、远程监测等服务,减轻家庭成员养老负担。
(二)激活成员资格:家庭支持老人
优势视角理论认为成员资格意味着老年人作为家庭中一员,享有同样的尊严和责任。随着家庭资源下移和老年人身体机能退化,老年人在家庭中经常被忽视或被贴上消极标签。费孝通先生的反馈模式认为,不同于西方家庭的亲子关系,在中国家庭中不仅父母有抚养子女之义务,而且子女也有赡养父母之义务,即受“养儿防老”思想影响,在中国形成了“甲代抚养乙代,乙代赡养甲代,乙代抚养丙代,丙代赡养乙代,下一代对上一代都要反馈的模式”[26]。故而,家庭成员应认同老年人家庭地位并激活其成员资格,使其拥有相同的能力和权利,并受到家庭成员尊重。
第一,整合家庭资源,强化家庭支持。子女不仅可向老年人提供直接的经济支持以满足其日常生活开销,而且可提供间接的经济支持,如依据需求为老年人购买居家上门服务、为老年人支付医疗费用、健康体检费用等;老年人不仅需要物质资源的支持,更需要子女关怀、陪伴与照料,故子女应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精神慰藉服务,“常回家看看”履行家庭养老义务。第二,购买智慧产品,实现适老改造。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国发[2021]35号)提出“提升社区和家庭适老化水平”“营造老年友好型社会环境”。(9)详见:《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的通知》,2022年2月21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2/21/content_5674844.htm在成员资格信念指引下,家庭成员依据老年人居住状况、居住需求为老年人购买相对专业的适老配套设施,如智能手环、防滑垫、上翻扶手、升降橱柜、一键通呼叫器等,并引导老人熟练使用智慧产品,利用现代科技提升居住品质。同时,具备一定能力的家庭可购买家庭养老床位。家庭养老床位管理系统通过远程监测在床状态、整合社会医疗资源等,为家庭提供专业延伸服务,给予老年人个性化定制服务。总之,家庭既是养老服务的“购买者”,又是养老服务的“监督者”[27],通过对老年人居住环境的合理性、系统性、科学性适老化改造,改善老年人居住环境与条件,实现家庭物理环境友好。第三,弘扬优良家风,促进孝道传承。优良家风不仅有利于个人养成良好道德品格,而且有利于营造和谐社会风气,传统优良家风中的“孝道”“勤劳”“诚信”“仁爱”等价值理念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28]。在新时代,需重新激活家风生命力、继承家风优良传统,家长在日常生活中既要注重言传身教,又要发挥榜样示范作用,在无形中形成一种有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同时,需要树立家风典范,弘扬孝道正能量。古有王祥卧冰求鲤、郑兴割股奉母,今有田秀英、王春来等全国慈孝道德模范,家长要由点及面地引导子女在学习古代孝道先贤风范的同时,以当代孝道模范为榜样,从细节处开始,让孩子在和谐家庭氛围中明白“孝敬”之重要性,并以此指导自己的日常行动,这样孩子方能在耳濡目染中学习和体会孝道。
(三)提升抗逆力,加强治愈与整合:老人互帮互助
在传统观念中,老年人被视为社会弱势群体,这种标签和认知长久影响着老年人自我认知及周围人对他们的认同。优势视角下抗逆力的基本信念强调每个老年人都有自己的智慧与优势,我们要正确看待老年人面临的知识退化、器官老化、思想僵化等困境,理解这只是人的生命历程所必经之阶段,从而引导老年人化劣势为优势,激发其内在动力,推动其实现“老有所为”。治愈与整合的基本信念则强调老年人可通过整合内外部优势资源,满足自身养老需求。基于此,应发掘老年人内在的优势潜能,以互帮互助形式合理整合外部资源,提升老年人自身价值和社会认同感。
第一,更新养老观念,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养儿防老”是中国的传统观念[29],但随着人口流动加剧,家庭结构小型化、核心化、空心化特征日益凸显,家庭养老的社会基础与传统观念受到冲击。英国一项调查数据显示:社交活动有助于降低痴呆风险,在60岁时几乎每天都与朋友会面的人,与隔几个月才与朋友会面的人相比,此后患痴呆症的风险要低12%。(10)详见: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研究:老年人多社交可降低痴呆风险》,2019年8月3日,https:∥www.zaobao.com/realtime/world/story20190803-977998养老的第一动力和第一保障是老年人自身[30],为适应家庭结构的变化,老年人应转变对子女过度依赖的观念,树立“自立自强”的养老观念,培养独立意识,追求生活品质,丰富个人生活,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第二,努力自我赋能,提高互助能力。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认为,老年人可行能力的缺失造成了其实质自由的缺失,阻碍了其幸福感的提升,应努力通过自我赋能,发现资源、获取资源、利用资源、转化资源、发展资源[31],以提升自身抵抗逆境之能力与互助能力。数字素养提升是新时代老年人自我赋能的重要环节[32],老年人可以依据自身家庭状况、养老需求、健康水平等,提升利用数字技术之主体自觉性,在积极社会参与的过程中紧跟数字时代的步伐,从而在享受科技红利的同时提高互助能力;同时,老年人可积极参与由政府各部门或社会组织举办的健康养生及护理照顾等知识讲座,了解养生保健、生活照料、康复护理、心理护理等相关知识,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实际操作技能,以此提升互助能力,更好地为他人服务。第三,利用时间银行,充分链接资源。人力资本理论认为,老年人在其人生阅历中积累了丰富的无形资本——知识、技能、健康等,社会应善用这些资源,使老年人继续为社会服务[33]。“时间银行”作为一个资源链接平台,不仅链接物质资源、服务资源、资金资源,还充分链接人才资源,是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本的重要平台。在抗逆力、治愈与整合信念指引下,推动“时间银行”进社区,以社区为服务半径,激励活力老人加入志愿者行列,通过数据资源全区域共享、信息资源全方位覆盖,为老年人营造良好环境、提供专业养老服务。这种“老老互助”的模式,不仅能缓解当下“照护赤字”[34]的困境,且能真正实现“老有所为”与“老有所养”有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