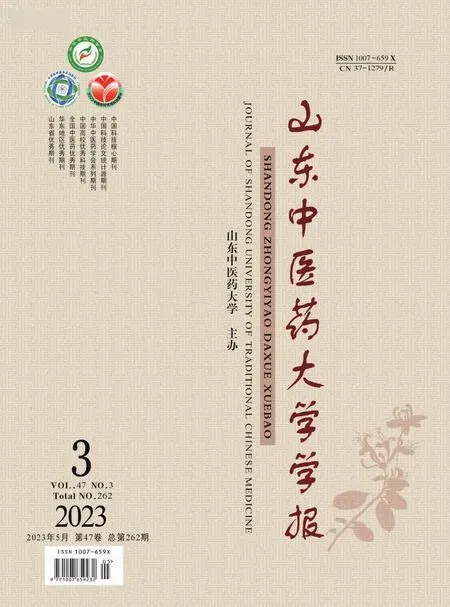基于疫毒湿热理论探讨岭南疫病防治
余 锋,信梦雪,刘 南,洪永敦,朱 敏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州 广东 510405)
当前新发疫病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这亟需我们对疫病的病因病机和临床诊治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和思考。 特定的气候条件、社会环境和地理位置均可对疫情的发生和流行产生重大的影响,岭南地区(包括现在的广东省、海南省、广西东部等地区)因其特殊的自然、社会环境成为传染病的重要传入地和流行区。 岭南医学在疫病的防治方面有丰富的论述,而现代医学的飞速发展和中医药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为创新岭南疫病病因学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
1 岭南疫病古代流行概况及干预措施
先秦时期岭南地区气候以湿热为主,疟疾始终影响着岭南,到唐宋时期疟疾流行达到顶峰。 东晋医家葛洪以青蒿清热解毒截疟,其在《肘后备急方·治寒热诸疟方》记载有“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药物制备方法。 此外葛洪在药物化学、预防医学等方面也有重要论述,如提出疫病非鬼神作怪,而是由于外因所致,铜青可以治疗皮肤病、雄黄和艾叶合用可以消毒等。 在明清时期,岭南地区疫病多以鼠疫、霍乱、天花为主,发病季节集中在春夏两季。 受当时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疫情较内陆地区更为频繁和严重[2]。 新中国成立后的40 年间,麻疹、疟疾等传染病均在岭南地区有散发病例报道[3]。 岭南地区湿热的地理环境影响了当地居民的体质和生活习惯。 岭南医学在防治湿热引发的常见病、多发病及疫病方面有别于其他地域医学,成为南方代表性的医学流派。 医家们在论治疫病时更多注重清热解毒、芳香化湿和顾护津气,同时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观察到岭南疫病多见挟湿证,从而提出岭南疫病以湿热为主,治湿是岭南温病学派的重要学术特点。 因湿乃重浊之邪,热为熏蒸之气,湿热相合,机体内外上下均可受到侵袭,故在选方用药时多从中焦脾胃入手,调畅斡旋气机治其本,临证喜用甘苦寒平药物,如黄芩、连翘、石膏、淡竹叶等,同时辅以轻清渗湿之品如杏仁、枳壳等以分解湿热,使之外透内化,护津存阴[4]。
2 岭南疫病近年流行情况及中医药干预
2.1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
该病是由SARS 冠状病毒(SARS-CoV)通过飞沫传播所致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起病急、传染性强的特点。 2003 年广东全省有1512 人感染SARS,死亡58 例[5]。 研究表明,SARS 患者中焦湿热证候常见,半数以上患者存在湿热证临床表现,且挟湿在卫分、卫气同病、气分三阶段中的分布无明显差异,提示易挟湿邪是SARS 邪气自身的特点,与该病辨证分期无明显相关性,其原因与岭南气候特点有关。 治疗上多以温病卫气营血传变理论为指导,选用以辛凉解毒为主的中成药注射液联合中药汤剂的综合治疗方案。 2003 年,我们团队对70 例SARS 患者采用西医常规对症支持治疗联合中医药治疗,以银翘散为基本方随证加减,辅以清开灵注射液等,患者体温多在72 h 内恢复正常,43 例患者的胸部影像学检查示病灶完全吸收,所有患者均治愈出院,且依从性较好,未出现明显药物不良反应[6-7]。
2.2 甲型H1N1 流感
甲型H1N1 流感系流感病毒感染人体所致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性疾病,本病四季均可流行,而以冬春两季多见。 2009 年广东省累计报道甲型H1N1流感病例9784 例,其中死亡36 例,推测全省2009年因流感至医院就诊者不少于270 万[8]。 从既往的文献报道来看,不同地域的流感患者具有不同的病机特点。 广东省H1N1 流感以风热疫毒侵袭肺卫为主,北方以风热疫毒为主,卫表症状轻微,热毒壅肺症状突出;南方则在感受风热疫毒的同时,兼见寒、湿之邪,并以湿为重点[9-10]。 岭南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及人群偏湿体质,均提示岭南流感与湿邪有一定的相关性,因此应详察岭南流感与湿邪的相关性,明确其证候分布规律进而指导临床诊治。 我们团队既往根据岭南流感特点,认为对于该病的治疗,解表透邪是核心治则,然而热由毒生,流感的治疗不能忽视解毒药物如重楼、黄芩、连翘等药物的应用。 临证分流感表证、里证两种证型论治。 流感表证症见恶寒、发热、舌红、脉浮者以柴胡桂枝汤合银翘散加减,若症见咳嗽、胸痛、舌红、脉滑数等里证表现,则以麻杏甘石汤合千金苇茎汤加减。 临床观察本治法疗效确切,可明显减轻发热、咳嗽等临床症状,缩短病毒转阴时间,提高患者生活质量[11]。
2.3 登革热
登革热是登革病毒主要通过埃及伊蚊和白纹伊蚊传播所引起的急性传染病。 本病迄今尚缺乏有效的治疗措施,西医主要采用补液稳定内环境等对症支持治疗。 1978 年我国首次登革热流行发生在广东佛山市,当年共报道确诊患者22 289 例,其中13 例死亡。 2014 年广东登革热爆发,全省有20 个地级市累计报道登革热病例38 753 例,其中重症病例20 例,死亡6 例[12]。 我们团队的研究表明,广东省登革热中医证候以卫气同病、湿热阻遏、瘀毒交结常见,致病因素以热、湿、毒为主。 在西医对症治疗基础上联合解毒化湿方(甘露消毒丹加减)口服具有较好临床疗效,不仅能明显缩短退热时间、住院时间及疾病总病程,还能改善患者的白细胞、血小板水平及凝血功能,降低住院费用[13-15]。
2.4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是新冠病毒通过呼吸道飞沫和密切接触为主传播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对于岭南地区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现多认为其病因为感受疫毒,加之岭南地区冬季应寒反温,春季气温过暖的异常气候,形成湿热疫疠之气,从口鼻而入,疫气相传,致使疫病流行。 本病以肺为病变核心,涉及脾、胃、肾,病机特点为“热、湿、瘀、毒、虚”[16]。 小样本的证候调查提示本病证型主要是湿邪郁肺,其次为邪热壅肺,湿热之邪占主导;舌苔以腻苔为主,舌质以红和淡红为主[17]。
3 疫毒湿热致病理论的提出
3.1 理论认识
基于以上疫病文献回顾及近年来救治登革热、甲型流感等的诊疗实践,针对疫病的严重危害性和发病特征,我们提出岭南疫病应从“疫毒湿热”角度认识。 岭南地区地处亚热带,气候炎热,土地卑湿,靠山临海,雨量充沛,当地居民多为痰湿、湿热体质,加之嗜食海鲜及肥甘之品,久则伤脾碍胃。 独特的气候地理环境决定了该地区致病邪气的特点以及人群体质的特殊性。 疫毒多从口鼻或卫表肌肤而入是疫病发病的核心环节,兼湿、热之邪是岭南疫病区别其他地域疫病的前提基础。 湿具有重浊、黏滞、趋下的特性,湿蕴日久,胶着不化,久而化热亦可酿生毒邪。 热为火之渐,火为热之极,进而致瘀毒内蕴。 失治误治,病情迁延,则蕴毒骤发,毒瘀搏结,导致病势进展。 疫病发病急骤,累及五脏,早期多见实证、湿热证,湿热蕴结,病邪累及肺卫和中焦脾胃是其核心病机。 对于疫病恢复期患者的康复更应充分发挥中医优势,如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期间,部分患者虽达到出院标准,但仍有咳嗽、心悸等症状,少数患者达到治愈标准出院后仍出现症状反复,复查病毒学指标再次“复阳”。 这与湿为阴邪、黏滞固着、较难速去的致病特点一致,且湿邪为患,往往病程较长,缠绵难愈。
3.2 疫毒
吴又可提出的“戾气”学说是中医病因学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疫气的存在、流行与否以及疫气的盛衰与疫病流行地区、四时及岁运等因素有关,这一认识与现代医学的病原微生物学说有相似之处。 临证应注意毒邪当有外来毒邪及内生毒邪之分,六气皆可化火,湿热蕴结可为毒。 人体在在感受致病邪气后所呈现出来的一系列病理状态如红、肿、热、痛的特点,相当于西医学的炎症反应,亦属于毒的范畴。
3.3 湿邪
湿包括外湿和内湿两个方面,《瘟疫论》中提到:“南方卑湿之地,更遇久雨淋漓,时有感湿者”,明确指出南方疠气流行时易兼夹湿邪。 岭南地处亚热带,气温常年较高、雨量充沛,靠山临海,海鲜、野味丰富,且本地居民素有饮早茶、煲汤的习惯。 嗜食阴柔厚味之品易酿湿生热,加之湿热气候有碍脾胃运化,若外感邪气,则临床多见挟湿证候。 此即叶天士所述:“内生之湿,必其人膏粱酒醴过度,或嗜饮茶汤太多,或食生冷瓜果及甜腻之物。”既往研究也表明岭南地区居民多有湿热内伏的体质特征[18-19]。 湿性黏腻,较其他邪气其势虽缓而实重,湿热为患,邪在卫分、气分之间可见头痛恶寒、发热身重的上焦症状,如邪在气分,则见胸膈痞满、心烦口渴、下利黏垢之中焦症状。 如湿邪久羁,弥漫三焦,运化失职,则见少腹硬满、二便不爽及头晕发斑等症状。
3.4 热邪
体质因素、生活习惯对湿邪的寒化或热化起决定作用。 《临证指南医案》指出:“若其人色苍赤而瘦,肌肉坚结者,其体属阳。 此外感湿邪必易于化热;若内生湿邪,多因膏粱酒醴,必患湿热、湿火之症。”岭南气温炎热,雨湿偏盛,加上岭南人群偏湿体质,内外相搏,故易患湿热。 《医碥·发热》有“凡痛多属火”“热生于火,火本于气,其理不外气乖与气郁两端”的认识。 气郁发热正合岭南名医何梦瑶的岭南人“气多上壅”之论。 如平素脾胃湿盛之人,容易感受湿邪,进而导致湿热。 薛生白《湿热病篇》云:“太阴内伤,湿饮停聚,客邪再制,内外相引,故病湿热。”因此,湿证体质的患者更易感受六淫或疫疠之邪,且病情亦较缠绵。
4 防治要点
4.1 中医药干预靶点
针对岭南疫病的“疫毒湿热”病机特点,我们提出清热化湿解毒的治疗原则,其中解毒是核心,祛湿清热是基础,防止疾病传变,截断病势是关键。 同时应注重养阴保津,树立治未病思想及五脏相关、中西医结合思维。 清代医家薛生白提出“湿热乃阳明太阴同病也”,湿热病是脾胃先伤,复感湿热邪气形成,内外合邪导致湿热。 针对“热得湿而愈炽热,湿得热而愈横”的病机特点,在治疗上应按三焦部位和湿热多少辨证,即“湿多热少,当三焦分治。 调三焦之气,分利其湿”“湿热俱多……当开泄清热两法兼用”,分解湿热,使其不相合。
4.2 理法方药的拟定
结合我们前期诊治疫病的经验,临床可选用甘露消毒丹、银翘柴桂汤及白虎清解汤等化裁使用。热者寒之、实者泻之固是常理,然而湿热相合,应用寒凉之品应避免寒遏冰伏,以防阻滞气机,郁闭邪气。 另一方面临床所见疫病患者以成年人居多,且大多兼有消渴、眩晕等基础病,一般疾病初期因病情较轻而很少来医院就诊,故纯表纯里证者所占比例较少,湿热阻遏、寒热错杂及表里夹杂者尤为常见。因此采用寒温并用之法,在解表清热处方中酌加辛散或辛温之品以振奋阳气,防止寒凉解毒药物阻遏气机或凉遏闭邪更为恰当[20]。 正如清代杨栗山所谓:“扬之则越,降之则郁,郁则邪火犹有,兼以发扬,则炎炎之势皆尽矣。”银翘柴桂汤由银翘散合柴胡桂枝汤加减而成,能解表清里,透邪外达。 白虎清解汤是麻杏甘石汤和千金苇茎汤的合方。 麻黄性味辛苦温,能发汗、平喘、利水,为解肌第一要药。 石膏味辛甘性大寒,本阳明经药,能缓脾益气,止渴清火,解肌出汗,且上行至头,又入手太阴、少阳经,而可为三经之主。 麻黄与石膏配伍,相反相成,宣肺透邪而清泄肺热,使邪有出路。 全方具有透邪外出、化痰祛瘀之效,可清除毒邪、痰浊、瘀血等病理产物并使正气渐复[11]。 甘露消毒丹能利湿化浊,清热解毒,主治湿温时疫湿热并重之证,为夏令暑湿季节常用方,被王士雄誉之为“治湿温时疫之主方”。 临证应用以身热肢酸、口渴尿赤、咽痛身黄、舌苔白腻或微黄为辨证要点。 全方利湿清热,两相兼顾,且以芳香行气悦脾,寓气行则湿化之义,佐以解毒利咽,令湿热疫毒俱去,诸症自除。 对于恢复期患者需注意补虚而不留邪,祛邪而不伤正,应关注湿、热的致病作用,酌情予以清热益气、养阴化湿之品,可选用清暑益气汤、当归六黄汤等加减。
4.3 临床意义
现代医学针对疫毒病原体的研究突飞猛进,免疫接种、疫苗及抗病毒药物等特异性治疗手段层出不穷,但仍存在一定局限性。 辨证论治、谨候其时、谨守病机、个体化治疗是中医治疗疫病的特色,中西医结合、取长补短是目前最佳的诊治策略。 尽早、全程的中医药干预对控制疫情有着重要作用。 在岭南疫病的诊治过程中,应以三因制宜理论为指导,正确认识疫毒湿热病因病机并四诊合参,辨证施治。 如在冬春季疫病高发季节提前对高龄、幼儿及罹患心肺等基础病的高危人群进行积极干预(一级预防),从而降低疫病发生率。 在患病之后将救治关口前移(二级预防),从疫毒湿热理论入手,探索中西医结合有效方法,有望进一步降低疫病病死率及危重症患者比例。 总之,在岭南疫病的疫毒湿热理论指导下,早期识别高危患者,在辨证论治基础上,及早给予解毒清热化湿治疗,必要时联合现代医学治疗,有望起到既病防变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