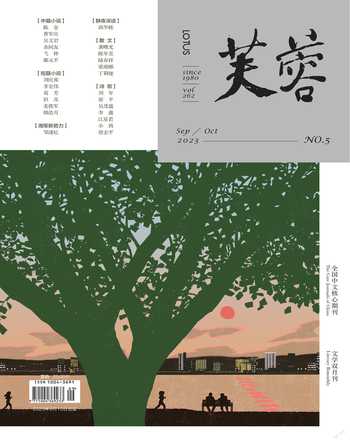引雷
李宏伟,四川江油人,现居北京。著有诗集《有关可能生活的十种想象》《你是我所有的女性称谓》,长篇小说《平行蚀》《国王与抒情诗》《灰衣简史》《引路人》,中短篇小说集《假时间聚会》《暗经验》《雨果的迷宫》,对话集《深夜里交换秘密的人》等。曾获吴承恩长篇小说奖、十月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徐志摩诗歌奖等奖项,作品入选收获文学榜、扬子江评论文学榜、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亚洲周刊·年度十大小说等榜单。
进入后山不久,天色就变了。云从四面拥过来,朝拜一般。速度本来就快,比速度更快的,是它们颜色的变化。无瑕得让人往轻逸联想的白,奔流间,往凝重了去,往沉坠了去,先是肿胀而瘀青,不及缓解、复原,即炭黑即墨黑,挨挨擦擦、碰撞夹缠,裹出了浓烈的怆惨的比黑更深彻的紫,只等着无来由的一刺一燎,就要泼洒下来,就要燃烧起来。
简客刚好转到山路的弯折处,停住脚,上下望。下面的云还在往上堆垒,上面的云则越压越深。高高低低,摆开阵势,营造摧城的气场,更酝酿暴雨的战场。滂沱将至,就算不把这矮小的山丘从大地撕裂,推至汪洋,至少也得把一草一木、一沙一石冲刷个遍,涤荡一新。要不要抓紧雨落前的这点缝隙,快速下山?阿或他们选定的那头羊想必已宰掉,正在剥皮,预备炖或烤……这一点转念,被一道闪电打断。银色的光自重重云中排闼而出,以粗壮的近乎直线纵贯半空,这才爪牙四探,在云的表面虬张伸缩,其中一条根须攀搭在半山腰上,似乎就在他抬眼可望的地方,然后迅速销匿。就是这电光石火之间,简客从闪电销匿的地方,瞥见一角飞檐。
真走起来并不容易。后山的路本来就窄就陡,石子混在泥土里,不时还有突兀的埋伏着的绊一下,磕一下,让人跌跌撞撞,走出几分狼狈来。何况拢在上方的枝叶、斜在下方的草茎,在暗沉的天光里,没来由多出几分凶恶,如同无数只手,沿途抓挠不休。好在,闪电不时从不同方位,以不同形式,曳过天空,多半能在须臾间,让简客看清面前这段路。即便短促、微弱得不能照明,借助上垂之光驱散畏怯总是可以的。因而,他手里把玩的铜打火机一次都没点燃。
简客就在这闪烁中,深一脚浅一脚往上行,云层仍在加厚,雨水尚未落下。他一面侥幸,一面纳罕,觉得哪里不对头。究竟是哪里?再转过一个弯,飞檐就在数十米开外时,答案就在心里若隐若现时,简客却在又一道闪电的提示下,看清飞檐所系的亭子,看见亭子有个人影,随即忘却了追问。
说是飞檐,不过是上翘一角,高出亭檐十数厘米而已。走得近了,看清楚是几块漆色剥落的木板,以锐角向上拼出。木板的拼接并不严密,且已被风吹日晒雨淋损耗不少,因而摇动不已。但这个六角的亭子上有两层,仿照庑殿顶的样式,托在半空,虽不伦不类,倒也高出一大截,难怪在山下能望见。简客要再细看亭子里的人影,闪电如被人吹动的烛火般,一阵摇摆后,熄灭了。银光的印迹仍旧在简客的视网膜上悬挂了片刻,让他意识到,之前它垂挂在亭子的一侧过于长久,并且居然如许柔和——至少可以逼视。心中难免骇异,可终归被好奇压过,简客定定神,等银光彻底消失,双眼适应了越发深重的天光,这才一步步向亭子挪去。那之前忘却了的追问,再一次在心里起伏,却在一时半刻间,更无心力辨别清楚。
亭子里的人自带光亮似的,让简客走到十米开外时,确认其须发皆白。毋宁说,那白即是一种光亮,不但现出自身,还映照出那人的眉目、身形。要据此判定他的年龄却难,因为须发掩映中的脸稚气毕露,拢扎在脑后与翘在下巴上的两根小辫,一粗一细地相互映衬,让他整个人滑稽中带着出尘,脱俗中又难掩烟火气。简客立在亭子外,等候良久,那人也没看过来一眼,他便只好把目光顺过去,落在亭子外不远处巨石缝里蹦出的一棵幼树上。是寻常的油松,不到婴儿臂粗,刚刚一米出头,树干、树枝、松针都如洗过那般簇新。油松不堪目光的压力,颤动着摇晃着,仿佛在躲避必然到来之物的庞然泠然。是什么呢?简客目光向上。初步的交融、吞噬后,乌云变作巨大的几团,速度慢下来,碰撞的频率降下来,但那撞击之力之势在肉眼可见地增强。推搡间,两团云交接的边缘漏下一线白,细而疾,直扑那棵油松。
可不要殛灭了它。简客并非祈祷,只此闪念,目光同时往旁边挪动几米,落在巨石斜出的犄角上。白线如针,直直扎下,距幼松尖不过数米,方才歪得一歪,朝着巨石移了一移。烟尘、巨响随之而来,幼松一侧的松针燃起。负气抑或心疼,简客冲过去,双掌夹击,拍灭松针上的火。再往闪电落处看去,石头赫然被劈开一角,断裂处齐齐崭崭,绝非凡间工匠所能达成。这一瞬间,简客反应过来,抓住之前的念头,明白了悬在心间、若现若匿的疑问是什么。揭晓谜底或作為回应般,一声炸响轰然而至,是否笔直在他头顶无从断言,但在他上方不远却是无疑的,因为那声响直击颅骨,迅速扩散至四肢百骸、心肝脾肺,将他体内整理一遍后,才从两只耳朵贯出。贯出即命令,四声炸响同时引爆,在之前那一响的四方,距离相等,力道相同,传到简客这里时间不差毫厘,因此是四声而呈一声,是一声而有四部,充分展示了立体声的魅力。
要不是亭子里的人正望过来,要不是他的表情在昏暗中不减分毫的递送,简客几乎要被雷霆震动得捂住耳朵。那表情难以名状,也可以说五味杂陈,能让人在惊惧疑惑安定躁动……诸般种种之中游移,但它们的底色都是难以置信兼视若无物。那表情不是冲着人,而是对着物,就像孩子初次望向蚂蚁。简客比蚂蚁多出一份尊严,至少是在人的层面能够理解的尊严,他不能被声响以及声响引发的恐惧压倒。于是,简客稳住心神,清理掉脑子回荡的余音,控制好发软的双腿,向亭子走去。踩点一般,跟随他的步子,上方爆出一连串闷响,足足有七响,高出不少远去不少,也就没那么震怖,仿佛作为之前五响的尾声或回声。
简客进入亭子时,那个须发皆白,扎出两根小辫的人自远处收回目光,向他看一眼。霜雪之刃在心上滑过,欲剜而止,让简客在冰冻与疼痛之间缓过一口气。他还是不知道说什么,只好走到亭子中的石桌旁,在一张石凳上坐下,目光在亭子里游弋,时而柱时而梁时而顶,时而又回到那个人身上,看他如雪的须发倏然竖立倏然垂下,仿若鼻翼翕张。
“你学过引雷术?”那人忽然开口,声音比形象清澈,是让人信任的成年人的稳重。简客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他是在和自己说话,却反应不过来话里的意思。
“你一定学过引雷之术!”那人笃定起来,“要不然,我练习这么久,怎么会被你轻易破坏。不过——”他看着简客,露齿一笑,“你用不着得意,我刚刚是一时大意,才让你带偏了这一点,声势和威力完全还在我的掌控中。”
“你是说,刚才那一道闪电受你的控制?”简客不相信说出口的话,又忍不住往上追索、往下推导,“这么说,悬在亭子旁的那道闪电也受你控制?连刚刚那一串雷声,排列得那么整齐,轰响得那么有节奏,都是受你的控制?”
那人再次看简客一眼,这一次没有锋刃,有的是纯然的无法抑制的好奇。看完,他沉默了一会儿,才说:“你不相信?难道你真的没有学过引雷术?不可能。就算没有学过,你一定知道,自己可以引导,至少是干扰雷霆,要不然刚才怎么那么一气呵成。”
简客被那人的话尤其是笃定的语气弄得恍惚起来,禁不住苦思,可这方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记忆。除非……他想起五岁时,那个阴天,一条大黄狗堵在回家路上,冲他龇牙咧嘴,低声嘶吼,随时都会扑上来似的。他一边按照大人说的,慢慢蹲下,装作捡拾石块,一边以余光左右寻觅……好不容易摸到一块称手的卵石,抓在手里正要站起……恰在这时,一阵闷雷滚过头顶。要是这雷能……他还没想定,滚动的雷开闸般落下。没有闪电,只有积攒的声响,掉在大黄狗的头上。大黄狗显然被炸蒙了,却还未来得及甩出一阵凄厉的惨叫,才仓皇开逃,跑出几步,两条后腿绊在一起,翻滚进路旁的沟里。此后很多年,那惨叫都回荡在简客的记忆里,只不过慢慢解除了与其捆缚在一起的雷声。
“想起来了?”那人看出简客的踌躇,看准踌躇所在。
但是……等等,简客喝止自己对记忆的修正。因为再往后稍稍延伸几分钟,画面里就会出现阿或。那时的阿或,只比他大半岁的阿或,右手拿着他爸的铜打火机,左手捏着从一只衣兜里摸出的小鞭炮,那是从五十响上拆下来的,正作势要点了继续往黄狗掉落的沟里扔去……也许有别的……简客回看那人一眼,却顿不住思绪的奔流……大概八年前,同样是个阴天,在他的办公室,阿或与他双双站立,沉默相对,直到室外完全被乌云压至黑暗,路灯虚浮地亮起。“我要是参与了——”阿或声音轻细,却几乎一字一顿,“天打五雷轰。”话音刚落,一串雷炸过,仿佛正经行窗外。望着身形摇晃的阿或,“不要”的念頭生起,尽管简客不确知要止住什么,尽管他没再看向对面的脸。有记忆需要修正吗?外面的雷声与阿或的慌张是确定的。可以补充的是,雷声翻滚中,在沉默中抽完一支烟,他没再说什么就让阿或走了。
还可以补充的是,阿或走后,他打开了办公室所有的灯,在赤白的固定在某一刻的闪电般的灯光下,从抽屉里拿出那份匿名材料,从头至尾又读了一遍,让阿或的纸上言行在眼前又演过一遍。然后,他停止猜测递来材料的人的意图,在碎纸机商标上那头绵羊的注视下,将材料塞了进去。然后,他将那份早在阿或他们这次密谋之前就拟好,只待一个时机的离职声明打印好,签上名字,叫来助理,交给她,嘱咐完她周一递上去时该说的话。然后,他走出办公室,乘电梯下到一楼,走出大堂。门外,一道诀别般的霹雳迎面扑来……到了这里,就到了终点。没什么再要继续,且不能也不想再继续。于是,简客的记忆返回现实,将右手里的打火机放入裤兜,再向对方伸过手去:“简客。简单的简,客人的客。”
那人愣了一下,极不自然地握住简客的手:“他们叫我老引,引导的引——引雷的引。”
“你是在控制那些闪电和雷吗?”
“不是控制,是引导。”老引有些严肃地纠正道,然后顿住,怅然逐渐在脸上浮现,“当然,到了最高层次,是能控制的。也不是控制,是合一。就好像孔子那句,‘从心所欲不逾矩,并非说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为所欲为,规矩一点都奈何不了,而是说修炼到了那个程度,心之所欲也在规矩内,心之所欲就是规矩,从心自然就不逾矩。嗐,谁知道呢,这不过是我的想象和理解。没到那个阶段,揣摩出来的,终归是门外的话。”
“你是说,这个,这个引雷之术,还有级别的区分,就像学术界评职称、公务员评职级那样?”
“对啊!每一个行当不都有层级、高低的区分?”老引像发现外星人那样看着简客,直看得他难免自惭起来,这才一挥手,不再计较,“多说几句也无妨。就冲你刚刚露那一手,也应该让你知道引雷这个行当更多的情况。说不定,你就此转了回来,真正开始进入这一行——”他摆手止住要插话的简客,“要是你哪天真正修炼起来,甚至臻至化境,那我好歹也有一份引介之功。你等等——”
老引再次止住简客,闭上双眼,原地入定似的。并没有飞沙走石这类夸张迹象,简客却分明感受到了世界在加速运转,仿佛眼前事物正在以1.5至2的倍速播放,他禁不住抬起头。天上的云印证了这一点,它们不是在流散,而是在原地,冰块掷于热水那样,在迅速融化。漆黑退至乌黑,乌黑退至乌青,乌青退至阴沉,阴沉……阴沉就那样悬着弥散着,一整片横过天际。并没有阳光露出来,并没有澄澈如洗,但比起之前,却实实在在清明不少,之前被压缩的视野随之打开。随之打开的,还有之前被乌云与雾气遮掩的后山全貌。山顶在望,离亭子不过两三百米,坡度陡峭,却并不险峻,反而一派细小娟秀模样。连贯其余,如同一头并不庞大的草食动物的腹背。
画面得以刷新后,简客方才意识到,通往山顶这一面,植被并不茂密,以不规整甚至于丑的石头为主,大的过于屋宇,小的及于磨盘,一律疤疤瘌瘌,全无奉承目光与人心的意思。石头之间,稀稀拉拉,毫无规律地散布着油松,还有从石头缝里倔强探出身来的。这些松树都极为挺拔,攒着一口要拔高整座山的境地的怒气似的,因而十数米乃至数十米是它们寻常的高度。它们还给简客一种罕有的孤傲感,仿佛侧着身,不乐意正眼瞧人。是天气带来的错觉吗?简客由近及远,再由远及近,数次扫视,明白过来,“侧着身”并非错置的感觉,是实实在在的。每一棵松树,都只有一侧枝叶繁茂,另一侧一律空着。即使生长的这一侧,也并非恣意恣肆,而是经过整理,或者被整枝截去,或者被半途芟夷,有那么几株,削发去顶,甚至拦腰斩断。
“是我练习的结果。”老引再次涉入简客的思路,“走,我带你看看。反正,今天不可能再练下去了。”
不过几棵,简客就明白过来,那些松树的侧身是被迫的,或者说只是显得如此。所有的松树都伤痕累累,松針披垂的这一侧,仅仅是幸存。只不过,它们的枝叶都恰好朝向亭子的方位,因此,站在那里才不会轻易发现,才会觉得繁茂依旧。伤痕都已炭化,有的经过长时间的冲刷,洗去了焦黑,只是以暗淡的创口进行着申述。有的则负伤不久,手指触碰、剥动,还能掉落一块块、一粒粒的炭。
“这些都是你练习引雷造成的?”简客站住。这个角度,恰好是很多松树伤痕的朝向,让他如处伤兵营中。
“提升缓慢。”老引反倒羞涩起来,“以前在南方,我总拿活物练习。不是鸡鸭鹅猫狗这些——没那么富裕,也没那么残忍;更不可能在人身上,那是犯法的。昆虫啊,蛇、老鼠之类的,偶尔有过路的鸟。练了十年,除了周围越来越安静外,没什么进展。后来我明白,活物在动,难度太高,何况我找的那些又小,要求的精准度非比寻常。沮丧之余,我离开老家,四处浪荡。有几年,压根儿不愿意动这个念头,不想听见雷声。后来到了这里,在下面的村子住下,偶尔上了后山,看到这些松树,心有所动。试了一下,后山简直是天造的练习场地,容纳得下雷霆的声势,这些松树更是绝佳的练手之物,光与电的威力纤毫毕现……”
“你就这么自己练,没有人指点,没有什么参照?”
“你觉得我是野狐禅?”老引不以为忤,哈哈一笑,“引雷术不是什么稀罕物,至少听起来不是。有关引雷术的传说众多,练习法更是纷繁复杂,归于道家、佛家,称为方术、妖术,乃至魔术,都有。也有人说它是奇迹,是神力的施为。近来,还有人用科学方法尝试……究竟搁在哪一块、怎么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真的有效,这效果又能通达哪里。换句话说,在今天,练习引雷术干吗?”
简客听得一愣,不由得重复道:“在今天,练习引雷术干吗?”
“问得好!”老引夸张的语气让简客想笑,转头看去,老引的样子一下子将正要从他喉咙涌出的笑声堵了回去。老引头上与下巴上的两根辫子都翘了起来,下巴上的那根尤其夸张,笔直前伸,几乎要平行于水平面。没有扎进辫子里的头发、胡子都奓起来,支棱着,银白而坚硬,随时都能将他从地面提起来一般。这不算什么,真正骇人的是老引的神情,骇人之下更让人担忧。老引一脸空无,经年白纸般已不打算再容纳下新的事物,或者说已没有余地容纳。盈满的空无,空无的盈满。难以把握的,还是老引的目光,落在右侧那棵被劈开一半的油松上,又不粘连,不是走兽更不是飞禽,比蛛网还轻,风或可比拟,却少了其中的依附。
就在简客由惊惧开始不耐烦时,开始怀疑老引在装神弄鬼时,老引猛地抬头,目光越过油松,直送上天际,拽住变淡变薄的云层里牵引的风筝线一般,往下一扯,再落回来,往油松上面一送。一团炽白的光迅疾落下来,包裹着油松焦黑中泛青的半截断枝,吃甘蔗那样,一点一点啃进去,青烟股股,与之相随的,是小串鞭炮那样的噼里啪啦的声音,分不清是光携带的,还是燃烧生成的。啃上一阵,哗的一声,白光与声响同时消失,只留下余波在简客的眼前、耳畔。
“练好了引雷术,可以修整世界。”老引指着那棵油松,让简客注意,那多余的半截断枝已经被雷霆吞噬。“物理修整只是附属作用,是最不重要的那一部分。等到真正有成的那一天,特别是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引雷术就不是单纯的术了,它是对世界的裁判,是人与人之上力量的交会,借之以影响、修正这个世界……”
“等等——”简客打断他,“你说得太玄乎了,对世界的裁判、影响、修正……你是说成为神,主宰人类的生活吗?难道我们作为个人,不是应该先调整好自己的生活吗?”
老引的脸唰的一下红到脖子,一种深度的羞涩由内向外,占据他整个人。“哪儿能存着主宰人类生活这样的念头!不过是,不过是做一个补充而已。要做你说的那些事,至少不是我这样的人能够想象。我能想象的极限,也不过是,不过是做一个他们,神们的职员、随从、门徒,或者干脆点,一个仆人。在这方面缺乏想象力,理解不了引雷根本上的意义,如何恰如其分地容身于目下的生活,这也是我只能成为一个二流引雷师的缘由吧。”
“二流引雷师?这个是谁评的,标准是什么?”
“不用谁评。”老引摇摇头,神色、举止开始复位,“当你真正进入一件事,从技艺、从内部理解它时,是完全清楚它的深浅的,对于自己究竟到达了什么境地,只要冷静地客观地分析,完全能做到心中有数。就算你不知道超迈者究竟是何等样的风采,也绝对能感知到,他比你高出不是一星半点,你和他不在一个层次上。就好比……嗯……”老引抬头,目光在云层间逡巡良久,“这么一场风暴,电闪雷鸣,雨露甘霖,如何定性定量,不同体系有自己的标准。有一点却是清楚的,那就是内行人,修习引雷术的人,一望可知,是否有人在操纵它,在拿它练手。”
“有人涉入就必有人留意。事与物一旦被搅动,总会留下痕迹,无论抹除得多么干净。”简客忽然出神,随即意识到这一点,生出与老引方才相同的羞赧,“我是说,就像……就像一个人光着脚过河,虽然到了对岸,虽然水流冲走一切,但是……”
“不用解释。”出于理解抑或原宥,老引一笑,又把话题引回开始,“后山这些年,这些松树,供我练习,见证我取得进展,同样——伴随我停滞——”
戛然而止。老引紧紧闭上嘴巴,又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这一次,简客没再感到尴尬,他在老引旁边站着,找不到话安慰,甚或不知道是否应该安慰。且不说这件事的真实性有多少,即便完全可信,它与那些常见的偏执故事,与自己离开之后,在对阿或及以前的人与事上避而不谈不见的执念,又有多大区别?不能因为关涉天上,境界自然就能得以提升吧?望过去,天色仍旧阴沉,但暮色分明赶了上来,黄昏的拉链快要锁闭入夜晚。呼吸般可感的加重的晦暗中,一棵棵油松相互间更加疏离,它们因为人引导而遭受雷殛的部分渐次隐藏起来,模糊成一团。要是它们能开口,会对老引的举动毫无怨尤吗?又有谁能允许,以它们为练手对象?
“搞得这么沉重——”老引强行从沉默中挣出来,“谁让我迷上了引雷呢?迷上了它,进入它,就得接受,终我一生都极有可能跨不过一流的门槛,无法登堂入室。至少,很有可能跨不过。不过——”老引转过来,脸上的笑容越發纯净。他盯着简客看,因为暮色的稀释,目光与笑容都少了些逼迫。“你要是愿意修习,我一定——”
“我不愿意,不愿意再进到你这条具体的门径里来……”简客摇头,“就算如你说的,我在这方面有点天赋,那就让我保留一点由此产生的想象吧,这样今后每一次雷起,我都能以想象,自得其乐。”
老引听完,移开目光,又是久久不言。最后,他的目光重在简客身上晃一晃,转过身。“走,带你去看我的密室。”
越往上,路越窄,没走上一会儿,就不能再并行。老引在前,简客跟着。除散乱的尚未协调起来的虫鸣鸟啼外,就是他们的脚步声,沉而不闷且相互混淆,但稍一留心,仍旧辨得出“一二三四”的节奏。杂草与荆棘偶尔牵扯鞋面或裤腿,挣一下也就带开了。路并不长,向上三十来米,到了一块露出地面部分如船帆的巨石旁,老引举手示意,随即转向船帆内侧。
石头这一面出其不意地光滑起来,少了正面的坑洼、疤瘌,让人愿意用手抚触,体会它传过来的凉意以及凉意中若有若无的温润。沿着侧面,拉拽着贴石头而生的几株灌木,往下去几米,再一折身,到了老引说的“密室”。其实一点都不密,背靠着同一块石头的另一侧,其余几面都敞开在天地间。只不过,背靠的地方有一米来高如刀削般垂直着,上方斜着上去了几米,形成遮挡。地上是另一块石头托着,十来度的倾斜,与上方石头垂直部分衔接处,留有一片仅容一个人躺卧大小的平台。暮色中,简客判断不了,那平台是否有人力的作用。
老引毫不谦让,径自走过去,在平台上坐下,脊背挺直,倚靠在石头上,双腿箕张,身躯稳静。要不是白色的须发在暮色中轻微地飘扬抖动,要不是难以完全摒弃的呼吸推拉着周遭空气的些微涨缩颤动,简直要让人以为他自古以来就坐在那里,而且随时都可以出入石头内外。
“这是我师父的地方,他长年在这里打坐、练习,引雷而来,掣电而去。”
“你有师父?”简客讶异得出了声,随即连连抱歉,“你师父到了你所说的一流引雷师的境界了吗?有他指引,你想必……想必……也不用太失落,迟早总会迈过门槛的。”
“我的师父——”老引抬头,注视着简客,狡黠自下而上漾过他的脸,“就是我自己。自从我领会引雷的乐趣,决定沉浸其中,哪怕花去一生的时间无所成就也认了。乐趣已经让我得到回报,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乐趣的阈值提升得很快,但牵引着我往上寻求的,最终、必然——只能是我自己,我就这样成了我的师父。有时候,想象师父可能到达的境地,我仿佛确然具备了相应的本领。”
“等等——”简客捋不清其中的逻辑。
老引却没有满足他的要求,他垂下头,静默片刻,再次抬起。这一次,他没有望向简客,而是望向远方,苍苍茫茫的浑浑冥冥的天际,以及天际的背后。“也许,从他所坐的地方,从两块石头夹出的空间望出去,如同在潜望镜的这一端,以目光予世界的改造……”简客承接不上老引那游丝萦绕的目光,胡思乱想着,忽然,他心有所动,赶紧站住,随后往旁边让出好几步,矮下身来,似蹲似坐,半伏在石头上,再度看往潜望镜的视野范围。
不一会儿,得到了响应。先是一点白光闪现,细若初绽麦芒,但不及眨眼,即一变似米粒,再变如碗盏,三变若圆盘……再要联想,已经不可逼视,欺身上来。一团巨大的光占据了简客他们容身的巨石间的空间,不,是熔化了整个空间,只留下光芒遮住人的眼、掩住人的口,夺去一切感知,取缔立足之地,让人无法将自己的意识从光上剥离,无法确认自己的存在。因为无隔无间,与之一体,因而感觉不到那光的冷热,只是定定的,被它笼罩,被它带离了时间的范畴。
时间终究得回归,嘀嗒或咔嗒仍旧要继续,只要意识的根基尚在,就必然要浮出浑茫的水面。简客在光的笼罩下意识到自身与自身所在时,那光如烟花绽放,陡然绽开,以极其柔和的紫色漫开,穿过他的身体,穿过上下的岩壁,游蛇般,消失在已然降临的黑暗中。或者,是在光绽放与消失之后,简客才恢复意识,站了起来。声响是在那之后,极细极密,如同游蛇在空气中相互追逐,进而自相引爆那样,爆裂在空气里,完全想象不出是雷声。
“你是怎么做到的?”简客问,老引并没回应。简客回头看一眼,发现老引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收回双腿,盘坐在那里。看上一眼,掉开头,等着。心里一动,再次回头,发现了蹊跷所在。老引坐在那里,却像有专属的光打过去,将他从周遭的昏暗中分隔出来。不对,光不是打过去,而是透出来。还是不对,简客再仔细看,那光是从老引身后的石头上出来的,但并不是一整块石头在发光,而是从他倚靠的地方,贴着他身体的边缘还有一道线。是东西方绘画中都会有的,神、菩萨、圣人头顶的那种光圈,只不过这里是沿着身体。而且,线只是边缘,整个后背都有,隐约穿过体内透出,类似手电筒的光抵在手掌上,让老引的身体沿着脊柱向两边扩散的微微透明感。
老引闭着双眼,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光从背后托着他,这景象不是让简客惊悚,而是困惑。这些异象的指归到底是什么?哪怕是单纯的劝诱,可也并不具备多少说服力。再说,引雷之术嘛,根本不需要那么多人厕身其间……何况,到了该下山的时候。那老引怎么办呢?听之任之,让他自己待着吗?他连……简客这才一惊,走上前,似乎声息全无,他伸出右手,食指横在老引鼻前,似乎……老引蓦地睁开眼,盯着简客,目光中的神采一点点回归。神采全部落回时,老引目光灼灼,站起身,他背后的石壁仍旧透出光,由白色而玫瑰色而紫色,并在毫无预兆的时刻,全然退去。
“我发现这个地方时,简直不敢相信。”老引说着,回头看看石壁,当初的惊异、喜悦犹见,“引雷,和所有的事情一样,到最后,都可以是印证自身在时间中穿行的痕迹。有一个地方留存这些印迹,验证抵达的最新境地,是每一个沉浸在修习中的人能够得到的最幸运最高等级的支持、支撑,而这面石壁就是我的留存与印证。”
“然后呢?是等到那一天到来,再行破壁吗?”简客不耐烦起来,事情正变得出乎意料地烦琐,其中充斥的某种熟悉的重复的东西,在迅速增多。
“不不,不是那样的故事。”老引摇摇头,“要比那个更复杂。简单来说,我每个阶段练习引雷术达到的程度,都能经由石壁自我验证。我在这里坐下,引来雷霆,让它作用在我身上时,身影在石壁上留下的光影,显示了我达到的境地。比起上次,那还是三年前,我略有进步,却也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如果有一天,我能大成,石壁上的影子就会长驻不去,仿佛我在跨过门槛时,留下的遗蜕。那时候,我将乘闪电遨游,得大自在,以雷霆惩恶,佑护善根。这么逍遥的境地,你真的不心动吗?”
“你的逍遥境地,仍旧以有为根,依系于实,并不那么动人。”简客再度摇头,“等有一天,你不需要依靠乌云现成的聚集、碰撞就能引来雷霆,随时都能从晴天招来霹雳,或者再進一步,不需要霹雳,不必引雷,才算登堂入室吧。”
老引皱着的眉头开始舒展,两眼中的光越发灼亮,在他将要开口时,简客以右手食指竖在唇前,止住了他。两人就这样静默着,又一阵风从密室外掠过。简客忽然大笑,老引随之也笑起来。嘿嘿哈哈间,简客冲老引鞠一躬,以作道别。
“等一下——”老引叫住简客,走上来,左手抓起他的右手,右手扒拉开拳曲的手指,以食指尖在简客的手掌心上勾勾画画,不知道在写字还是画符,或者兼而有之。“谢谢你这番话。各有引雷之事,各有脚下之路,原不必强求在一条道上。看你还有心事未去,送你三道雷吧。耀眼如日,炽热如火,声响嘛——马马虎虎。游戏而已,当不得真,伤不得人。”
下山途中,老引的模样在简客的脑子里反复,每每带出他回到石壁前坐下,白色的须发在傍晚的风的吹拂下,轻轻抖动起伏的情状,既有令人恍惚的属于仙人的飘逸,也有令人酸楚的纯属暮年的衰朽。老引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说的一切、做的一切究竟是真是假,甚至于,这个下午经历的目睹的究竟存在与否,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简客右手插入裤兜,习惯性地摸出打火机。入手有异,举到眼前一看,分明是一块小小的卵石。前后左右摸索,跟了他这么多年的阿或他爸的铜打火机都不见踪影。
简客站在那里,待要辨认那卵石的形貌,断定它的来历。毫无预警地,卵石忽然碎了,不,是瓦解了。先是碎成几片,只容眨眼间,成了一把沙。握不住的沙顺着手掌边缘往下流动,并且越流越快,不容呼吸之间,干脆成了灰,消失在晚风里。勉强可以安慰的,是在卵石而沙而灰流逝消散时,隐隐有雷声夹杂,如同猛兽幼年的吼啸。
这时,阿或的院子已然在望。这时,他的手机响起。阿或问:“下山了吗?”
“快到了。”
“好。今晚咱俩好好喝一场,把这几年的酒都补上。自从……”阿或滞了一滞,毫无预警地放送出一长串他那标志性的魔性笑声。笑完,阿或说:“还生怕你被老引拐走了呢!”
“你认识老引?”
“方圆几十里,谁不认识老引啊?他这个人,不能说故弄玄虚,至少经常无中生有。”
“你是说,他说的都是假的?”
“那要看说的是什么了。翻面,翻面,顺着这个反向撒——”阿或反应过来串了场,又是一串笑声,“你到哪儿了?全羊烤得差不多了!对对,说回老引。别的不管,他要是和你说引雷那一套,千万不要信。他那年在山上差点被雷殛没了,之后,就开始讲那套故事。前几年村里来了几个人,不知道是艺术家,还是搞田野调查的,和他们待了几周后,老引越发拿自己能引雷当真事了。较这个真干吗,逗他开开心挺好的,逗得他开心,你也开心。有人看见他深更半夜拿火烧那些松树,也不管,反正松树相互间离得远,不至于引起多大的麻烦。再说,那些松树烧成那样,多得成了规模后,真有种诡谲的魅力。你看到了吧?喂——喂——”
简客挂断电话。阿或的声音在围墙那头传来,又“喂”了两声后,他仍不甘心地大喊“羊不等人”。应该不是心理作用,简客闻到了随喊声升起的烤羊香味,肉在火上烤得正黄正脆,一滴滴油落在火上,这让他感到饥饿难堪,并随之心慌。
总不能一点力不出。简客这么想着,停住脚,站在原地,望向退散得快要完全与夜色一体的云,伸出右手,摩挲这云的缝隙。白光如线,渐渐在他手上盘旋、缠绕,交织成一团。
等那一团闪电大若银盘,热如洪炉时,简客一抖手,将它抛过围墙,投在羊的两面。一片惊呼中,羊肉的香味浓郁阵透,扩散至围墙的这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