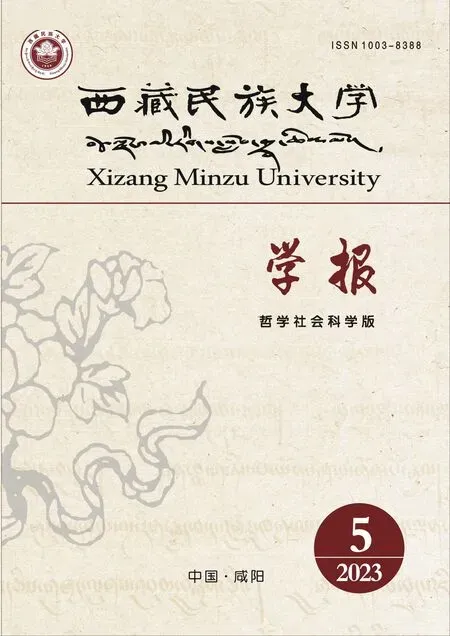海门道夫的尼泊尔夏尔巴人研究及其评析
赵 勇
(西安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 陕西西安 710128)
“夏尔巴”是藏语的音译,意为“东方人”,也被译为“舍尔巴”“谢尔巴”等。夏尔巴人(Sherpas)主要聚居在中尼边境地带,主体在尼泊尔和中国,印度、不丹等地也有较少散居。尼泊尔夏尔巴人生活在中尼边界囊巴山口南坡的要道上,是喜马拉雅山麓两侧宗教、文化、贸易往来的“中介”,在尼泊尔与我国西藏的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海门道夫尼泊尔夏尔巴人研究的成果
海门道夫①是20 世纪50 年代尼泊尔国境开放后,第一位深入夏尔巴人中进行调研的西方学者[1]。在之后的三十多年里,他对夏尔巴人进行持续跟踪研究,用人类学的方法系统记录下了当地人传统社会和文化习俗,见证了尼泊尔夏尔巴社会新旧秩序交替的过程。
(一)社会结构
海门道夫调查发现,在尼泊尔夏尔巴人社会内部,“骨系”是社会身份的核心元素和不可或缺的象征。同一父系血缘后裔的“骨系”不仅是划分人群的标准,也是夏尔巴人通婚范围最重要的参考和仪式的单位。夏尔巴人实行氏族外婚,同一“骨系”的成员,无论相距多远、有血缘关系的可能性多小,都被认为是宗亲,不允许通婚。[2](P20)相同“骨系”的夏尔巴人祭拜的共同氏族保护神,将氏族内部成员联系在一起。
在夏尔巴社会核心结构之外,康巴人、尼瓦尔人、切特里人等是主要的外来“移民”。这些外来者除不能拥有氏族名外,可以通过自身努力不断提升经济、政治、宗教地位,也可以与夏尔巴人通婚。海门道夫据此认为,尼泊尔夏尔巴人将部落社会的弹性与藏传佛教的包容、分享特性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基本开放的社会。[2](P38)
村庄既是夏尔巴人地域、政治、宗教的基本单位,也是社会职能能够充分发挥的载体。[2](P100)夏尔巴人的村庄是以宗亲和姻亲为基础的物质和精神相统一的有机体,依靠传统的村务管理者、寺庙俗官、收税人等保护自然资源,进行仪式活动,维护社会秩序。当所谓的基层民主村务委员会“潘查亚特”在尼泊尔推行时,因对当地人习俗缺乏了解和尊重以及管理能力的缺乏,使得社会矛盾逐渐显现,严重影响到了夏尔巴人的生活。突出表现在新政府无力控制森林遭受破坏的同时,使得当地人使用森林资源变得更困难。[3](P58-61)
(二)生计方式
尼泊尔夏尔巴人主要聚居在昆布、索卢、帕拉克地区,由于地理条件的差异,大多数夏尔巴人除在日常居住的主村有土地外,形成了不同海拔间交错搭配的移动式农业生产模式。在夏尔巴人的传统生计中,农业提供主要的食物来源,牧业则在丰富当地人的食物结构的同时,成为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和有利可图的生意。同样是由于地理因素,在不同牧场间定期移动成为了夏尔巴人牧业的主要特点。农业和牧业保证夏尔巴人的基本生计,但决定其生活水平比尼泊尔其他山地族群更高的则是与西藏的传统贸易。夏尔巴人本身并不生产平原地区和西藏所需的物品,但其所处的地理优势以及他们擅长携带货物穿越雪山的才能,使其将都德科西盆地粮食丰产区与西藏高原连接起来,成为了这条传统盐-粮贸易线上最大的受益者。
20世纪50年代末,中尼边界封闭后,夏尔巴人与西藏的贸易受到影响。对于他们来说,仅靠传统的农业和牧业是无法维系较高的生活水平,传统边贸的突然停止对其生计提出了挑战。幸运的是,从1953 年尼泊尔对外国人开放国境以来,登山和旅游逐渐成为了夏尔巴人生计中的新因素,弥补了边贸中断形成的缺口。
据海门道夫观察,登山和旅游在尼泊尔夏尔巴人中兴起后,在明显改善当地人生活的同时,也给夏尔巴社会带来变化和潜在问题。在传统社会中拥有大量土地和牲畜的长者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明显下降,财富从年老一代流向年轻一代、从富人转向穷人的同时,社会地位也完成了同样的转换。青壮男性从事登山和旅游相关工作后,大大加重女性家庭负担,未婚女青年的适婚对象也成为问题,随之而来就是夏尔巴人的出生率下降。[3](P80-83)对于夏尔巴人来说,挑战不仅来自新生计方式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来自登山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阻碍。大多数夏尔巴男孩被登山和旅游业的高额报酬吸引,早早辍学,缺乏相应的教育,对行业的规范和个人职业的可持续发展都产生了负面影响。[3](P78)
(三)宗教信仰
海门道夫经过调查发现,尼泊尔夏尔巴人主要的宗教信仰是藏传佛教。尽管他们对神灵充满敬畏,但并不认为当人活着的时候,超自然世界的力量能够影响到个人的生活。当物质利益和健康受到威胁时,他们不认为是触犯了神灵而导致的不幸,也不指望得到神灵的直接帮助。在夏尔巴人的观念里,只要努力追求功德就能获得重生。对于危害人类福祉的恶灵,认为可以通过“通灵人”、祭司、占卜师与之进行沟通,并由喇嘛用仪式进行安抚或驱逐。
寺院及僧侣是夏尔巴社会和文化的重要力量。[2](P126)在夏尔巴人的宗教信仰体系中,佛教信仰与民间信仰并存,村民对地方神灵的崇拜并不排斥寺院仪式表演,博学的喇嘛也不会与村里的祭司发生冲突。在寺院住持的带领下,僧人层级分明、分工明确,用严密的组织体系和戒律共同管理着寺院的日常事务。年轻的僧侣需要完成相应的考核才能获得更高的职位,对无视寺规戒律者按相关规定处罚。与其他社会宗教机构明显不同的是,夏尔巴僧人必须自食其力,自己解决住所和生计。[2](P138-139)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进入寺院,他们都对寺院僧人这一身份十分认可和崇敬。
据海门道夫观察发现,登山和旅游在夏尔巴人中出现后,寺院体系经历了两个明显变化的阶段。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登山和旅游刚刚兴起的时候,寺院发展受到了负面影响。年轻的僧人成批还俗,投身这些报酬高的新兴行业里。20 世纪80 年代初,登山和旅游积累起来的财富,大量用于支持宗教事业发展,寺院再度繁荣,同时也被卷入到相关的商业活动中。
(四)道德价值观
海门道夫认为,夏尔巴人的道德价值观直接受到藏传佛教思想的影响。[3](P106-110)夏尔巴人的道德体系是由“功德”与“罪”两大要素构建起来的,对于他们来说,一切利他行为都是善行,每一种善行都会增加个人的“功德”;对独立于个体的普遍道德秩序的违背就是恶行,每一种恶行产生的“罪”都会抵消善行积累的“功德”。“功德”与“罪”平衡的结果是评价人一生的标准,也决定着人死后来生的命运。与一神论宗教信仰不同,对于夏尔巴人来说,“罪”不是冒犯神灵的行为,他们没有将道德行为与对神灵的尊重联系在一起。
在面对无法避免的“罪”(如砍伐树木、阉割公牛等)时,夏尔巴人克服了理想与现实间的矛盾,提出善行可以减轻罪过。这一观念既缓解了人们对小罪过的悔恨,又激发了人们对善行的强烈追求。另外,在夏尔巴人的道德体系中,恶行带来的“罪”虽然会消减个人的“功德”,但不会使触犯者甚至整个群体面临危险。
夏尔巴人传统的道德价值观是在其社会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是每一个个体自愿的结果。在与贸易伙伴甚至陌生人交往过程中,夏尔巴人总是热情、随和,将宽容待人和利他精神淋漓展现;在夏尔巴人内部交往中,夫妻通常和睦、宽容,亲朋好友总是温暖、亲切。在传统观念里,他们普遍认为和睦是美好生活的基本要素,财富只是经营家庭的一种手段。即便是对财富有所追求,也都是因为它能够使拥有者向穷人施舍、向宗教机构捐款,从而获得“功德”。
夏尔巴人的道德价值观念在登山和旅游兴起后发生了变化,一个没有竞争和争斗的传统社会价值观,不再适合鼓励个人把获得金钱作为第一要务的经济制度了。[3](P112-114)这些新兴行业的从业者只有把工作放在家庭生活之上,才能在与同行竞争中生存。在工作机会竞争和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中,夏尔巴传统社会的和睦遭到了破坏。大批登山者和游客的涌入,也冲击了夏尔巴村庄的安宁和夏尔巴人的待客热情,重塑着夏尔巴人的道德价值观念。
二、海门道夫尼泊尔夏尔巴人研究的特点
20 世纪50 年代初,海门道夫回到了英国学术圈,开启了新的人类学研究领域——尼泊尔夏尔巴人研究。在他持续关注夏尔巴人的几十年里,用文化多样性的视角、综合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当地的传统文化和社会变迁进行了全面、系统地记录和研究。
(一)全面性、系统性
1953 年尼泊尔宣布对外国人开放边境后,海门道夫立即申请了去尼泊尔的签证。他首先对尼泊尔昆布、帕拉克、索卢地区几个夏尔巴人的定居点进行了初步调查,为进一步调查与研究奠定基础。1957 年,他再次来到昆布地区,对夏尔巴人的高地牧场夏季定居点进行跟踪调查。次年,他又对散居于尼泊尔西部的夏尔巴人进行调研。1962年,海门道夫对昆布和尼泊尔西部的夏尔巴人和菩提亚人(Bhotias)进行回访,并进一步扩大调研范围。1966 年、1971 年、1972 年,他继续对尼泊尔东部的夏尔巴人、塔卡利人(Thakalis)、西部的菩提亚人进行调研。80 年代,他又数次回访尼泊尔。在海门道夫对尼泊尔夏尔巴人持续研究的三十多年里,形成了大量研究成果(见表1),使其成为了该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

表1:海门道夫关于尼泊尔夏尔巴人研究的主要论著
在海门道夫进入尼泊尔调研之前,夏尔巴人的研究一直处于简单记录、猎奇、服务殖民需求的前科学研究阶段。海门道夫用《尼泊尔的夏尔巴人:高地佛教居民》[2]《喜马拉雅贸易者:生活在尼泊尔高地》[4]和《夏尔巴人的转变:尼泊尔佛教社会的变迁》[3]三部民族志以及相关论文,全面、系统记录了20 世纪50 至80 年代尼泊尔夏尔巴人的社会结构、生计方式、宗教信仰、道德观念等方面的传统和变迁,形成了一个完备的夏尔巴人研究体系,使其成为该研究领域当之无愧的开拓者。他对夏尔巴人的研究不仅带动了雪莉·奥特纳(Sherry B.Ortner)、奥皮茨(Michael Oppitz)、麦克唐纳(Alexander William Macdonald)、费舍尔(James F.Fisher)、珍妮丝·谢勒(Janice Scherer)等一批学者对夏尔巴人的关注,还奠定了尼泊尔人类学研究的基础。
(二)倡导文化多样性
海门道夫通过将珞巴族阿帕塔尼人(Apa Tanis)、夏尔巴人以及现代西方人关于“罪”的概念及存在形式进行比较,得出并不是所有社会都存在罪感,而且其与社会性质、政治结构、经济水平等也没有对应关系。罪感与其他文化形式一样是一种独特而多样现象,不能用特定的社会秩序来解释。[5]
海门道夫指出尽管基督教世界里的西方男女都坚信“罪”是普遍存在的,但“罪”这一概念不一定为所有人共享。在信仰藏传佛教的夏尔巴人中,功过平衡的观念十分明显。他们的道德体系建立在每一个善行都会增加个人的功德储备,每一个道德上罪行都会减少功德,人一生罪行的总和也可以被更大总量的善行抵消。俗世中的夏尔巴人仅从人与人、人与其他生灵间的关系来理解“罪”。人可以利用储备的功绩平衡自己犯下的罪行的观念,与致命的“罪”相对的恩典状态的概念完全不同,也没有任何观点认为罪行会降低犯罪者的社会地位。
在未受到任何其他文化和宗教影响的阿帕塔尼人中,没有发现任何关于“罪”的概念,也没有发现任何在超自然里获得“功绩”的愿望。[5]阿帕塔尼人试图在自己部落群体社会和经济框架内取得有利地位,而不在整个超自然价值体系内区分善行与罪行。在世的幸福命运不是通过善行获得,而是由活着时取得的成就决定的,而这些成就会在亡者世界自动延续。在世和来世的满足不是对立的。在阿帕塔尼人的观念中,为了追求崇高的道德目标而自我否定、节俭或放弃理想是不可理喻的,对违反普遍道德准则理应产生的“罪感”他们也没有概念。
据此,海门道夫指出“罪”及罪感以如此多样的形式,在广泛的文化环境表现出来,以至于不能用过去或现在的任何特定社会来解释。作为人类学家只能指出这种文化形式的多样性,而把为什么有些社会成员对自己和人类的总体状况极为不满,而另一些社会的成员却认为人类既不在通往更大衰败、也不在通往救赎和更美好未来的道路上,而将人视为平衡世界的一部分这类问题留给心理学家和哲学家思考。[5]
(三)研究理论与方法综合性
在海门道夫的治学中,早期理论上经历了从传播论向功能论转变的过程,中后期则主要运用功能主义理论开展研究,最终站到了文化相对论的立场上。参与观察和比较研究是海门道夫的基本研究方法,同时他还倡导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相结合,并用日记、图片、影音等多种方式进行研究。在进行夏尔巴人的研究时,他在理论和方法上都比较成熟,整体上呈现综合性的特点。
在夏尔巴人研究中,除以功能论为基础外,海门道夫打破人类学学派的界限,综合运用各种理论。“海门道夫虽然欣赏马氏的功能理论和田野工作方法,却‘从未皈依功能主义’,而是采取了综合式的理论方法,既未摆脱德奥传播学派的影响,也认同古典进化论和历史特殊论,同时又积极吸收了马氏的功能理论和田野工作方法。”[6]
从事人类学研究需要了解多种理论和方法,才能将一个主题下的各种因素分析清楚。随着时代和研究对象的变化,仅用传统的进化论、传播论、功能论、结构论、阐释论中的某一单一理论或方法研究特定主题的阶段已经不存在了,人类学研究进入综合运用理论方法的阶段。海门道夫的尼泊尔夏尔巴人研究,将自己所接触到的人类学知识融会贯通,突破传统桎梏,摒弃学派之争,综合运用了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根据实地调查忠实记录研究对象,尊重研究结果,不以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先行,而是根据研究的实际需要使用理论和方法,最终形成以反映研究对象特点为中心的综合性理论方法模式。
三、海门道夫尼泊尔夏尔巴人研究的价值
尼泊尔夏尔巴人与我国夏尔巴人仅一山之隔,族源、语言、文化、宗教信仰一致,往来密切,对其进行关注和研究意义重大。尽管20世纪50年代初有外交官、传教士、商人、军官和探险家的记录,但海门道夫对夏尔巴人等尼泊尔族群的研究是具有明显开拓性的人类学活动。[7]尼泊尔人类学研究始于海门道夫1953 年在夏尔巴人中的调研,而他的代表作《尼泊尔的夏尔巴人》则是尼泊尔人类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8]将尼泊尔人类学研究带入现代人类学的时代,奠定了尼泊尔人类学研究的范式。[9]通过海门道夫对尼泊尔夏尔巴人研究的成果,能够更全面地认识夏尔巴人,为我国的喜马拉雅族群研究提供丰富研究资料的同时,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中尼经贸、旅游合作。
(一)填补研究资料空白,促进相关领域发展
国内学者对夏尔巴人的研究,始于20 世纪70年代末对西藏边境民族的调研。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学界在国内夏尔巴人的族源、习俗、艺术、社会发展变迁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也存在明显不足:对尼泊尔夏尔巴人的研究非常缺乏。除一些零星介绍尼泊尔夏尔巴人概况的文章、相关论著译文、书评外,仅有少数学者对中尼边境夏尔巴人的跨界流动与社会生活进行研究[10]。对尼泊尔夏尔巴人的实地调查资料的掌握也十分有限。
海门道夫对尼泊尔夏尔巴人的研究成果,可以弥补我国在该领域研究对象单一、研究资料不足的缺陷。他对夏尔巴人研究所形成的三部民族志以及相关论文,填补我国尼泊尔夏尔巴人研究的资料空白,加深国内学者对该族群的了解,促进相关领域的研究。通过他的尼泊尔夏尔巴人研究成果,学者们可以从社会体系、生计方式、宗教信仰、道德价值观、社会发展变迁等方面丰富对夏尔巴人的认识,为进一步更好地开展研究提供资料保证。
海门道夫的尼泊尔夏尔巴人研究成果在弥补我国相关研究领域资料不足的同时,还为我国开展域外喜马拉雅族群研究奠定了基础。随着国力增强和相关学科的发展,突破研究对象单一、开展更大范围的喜马拉雅族群研究的条件已经成熟。海门道夫的尼泊尔夏尔巴人研究成果可以作为认识和了解域外喜马拉雅族群研究的一个开端,作为我国喜马拉雅族群研究“走出去”的基础。
(二)服务中尼经贸、旅游合作,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中国与尼泊尔山水相连,交往历史悠久,传统友谊源远流长。“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西藏和喜马拉雅区域成为了连接“一带”与“一路”的重要纽带,西藏边境民族与喜马拉雅山地族群,则成为了这条纽带上的“纽扣”。跨中尼而居的夏尔巴人,就是这条纽带上最重要的“纽扣”之一。充分认识和研究历史上夏尔巴人在中尼传统贸易和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对于“一带一路”以及南亚大通道建设意义重大。
从20 世纪50 年代初,尼泊尔对外国人开放以来,作为人类学家的海门道夫首批进入夏尔巴人地区进行调研。在此后的十年里,他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夏尔巴人上,并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多次对夏尔巴人聚居区进行回访。通过调查,海门道夫发现尼泊尔索卢昆布地区的夏尔巴人都是从西藏迁移而来。他们由“骨系”连接在一起,但并不排斥来自西藏的“康巴人”,甚至不属于菩提亚群体的尼瓦尔人、切特里人也能很轻易地融入夏尔巴社会。正是海门道夫发现的尼泊尔夏尔巴社会的这种开放性,给当前的中尼经贸发展和跨境旅游合作带来重要启示。尼泊尔是一个语言、民族、宗教、文化多样的国家,国内情况复杂,开放、包容的夏尔巴人将会是连接起尼泊尔与中国的关键。
通过海门道夫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在中尼边境上一直存在着繁荣的传统贸易往来,而夏尔巴人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中间人”角色。这提醒我们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进行中尼经贸合作过程中,加强对开放、包容的夏尔巴人纽带作用的重视和利用。
在研究中,海门道夫还发现,当夏尔巴人在传统贸易中的地位受到挑战时,他们就开始转向登山和旅游业,并凭借其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过硬的身体素质,在日益兴起的旅游业和登山运动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我国历来重视边疆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发展和传统文化的保护,生活在我国境内的夏尔巴人物质生活丰富,民俗传统保存完整。因此,中尼双方可以整合夏尔巴人的文化旅游资源,利用尼泊尔夏尔巴人积累的经验,开发以珠峰为核心的中尼合作旅游项目;也可以在我国低海拔的夏尔巴人聚居区内,开展“夏尔巴旅游度假村”“夏尔巴民俗文化体验旅游”等项目。以夏尔巴人为媒介,以旅游为载体,将中国与尼泊尔连接起来。
边境地区既是国家领土的边缘,也是国与国间交流、交往的前沿,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发展边境贸易、跨境旅游不仅可以带动边境地区发展,也能促进两国的交往。在跨境而居的夏尔巴人的带动下,开展跨境经贸、旅游合作,将中尼边境地区富有特色的传统贸易、民俗文化转换为带动两国边境地区的发展资源,促进两国人民交往、文化交流,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和南亚陆路大通道建设。
结 语
喜马拉雅区域是多元文明的汇聚之地,域外喜马拉雅族群在历史上与我国关系密切,当前又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中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纽带,居住在该区域的族群本应是学术研究的重点,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尽管我国的喜马拉雅族群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西方学界仍掌握着该研究领域的主要资料和主导权。系统开展喜马拉雅族群研究的前提,是对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总结和分析。
对喜马拉雅族群研究领域的奠基人海门道夫的尼泊尔夏尔巴人研究进行介绍与分析,仅仅是一个开端。应该有更多的学者加入到域外喜马拉雅族群研究资料的收集、整理、译介与研究中,对相关文本、图像、影音资料进行系统整理与研究,梳理研究资料目录、建立研究资料电子资料库、构建研究的知识谱系,形成喜马拉雅族群研究的学术史,逐步构建起对域外喜马拉雅族群研究全貌的认识。最终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喜马拉雅族群研究体系,服务相关学科发展的同时,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带一路”建设以及大国外交战略贡献力量。
[注 释]
①克里斯托夫·冯·菲尤勒-海门道夫(Christoph von Fürer-Haimendorf,1909-1995),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喜马拉雅族群研究奠基人。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他先后对印度那加山区的康亚克那加人,海得拉巴的陈楚人、萨玛斯冉人、雷迪人、贡德人,珞巴族阿帕塔尼人及邻近部落,尼泊尔夏尔巴人等进行了调研,形成十余部民族志、近百篇田野报告和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