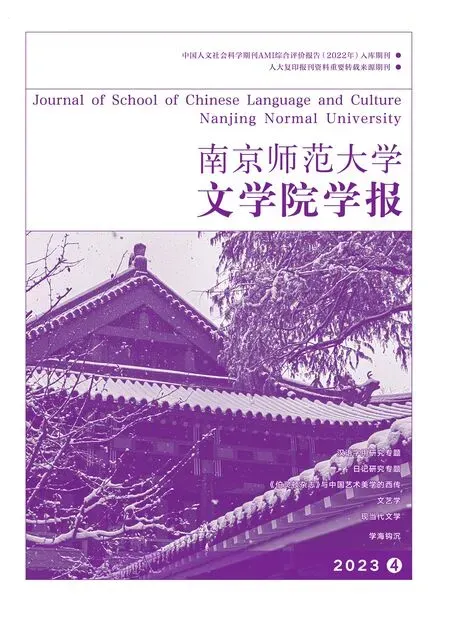《入蜀记》影响论略
章华哲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陆游的散文名篇《入蜀记》,最初被收录于《渭南文集》第四十三至第四十八卷,全文共六卷,近四万字,是宋代最长的日记体游记之一。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闰五月十八日,陆游赴任夔州通判,携家眷从故乡山阴(今浙江绍兴)出发,沿运河乘舟至江苏镇江,转入长江航道,一路逆流到达夔州任所(今重庆奉节一带),途经今之浙、苏、皖、赣、鄂、渝六个省市,历时五月有余。《入蜀记》即是陆游在这一旅途中所作的日记,记录了沿途的风土人情与他的所见所思所感。
陆游对这部作品很是重视,据其子陆子遹《渭南文集序》载,陆游在向他交代《渭南文集》编撰体例时曾特意叮嘱:“如《入蜀记》《牡丹谱》、乐府词,本当别行,而异时或至散失,宜用庐陵所刊欧阳公集例,附于集后。”(1)陆游.陆游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2491页。因此,这部作品一开始附于《渭南文集》而流传,后来才陆续出现了单行本。《入蜀记》在明清时期颇受欢迎,被收录于多种明清丛书中(2)参见蒋方.陆游《入蜀记》版本考述[J].长江学术,2006(04),第71-77页。。
前人对《入蜀记》的研究比较丰富,涉及其版本考述、思想内容、文学成就、史地价值乃至旅游资源等诸多领域(3)参见蒋方.入蜀记校注[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莫砺锋.读陆游《入蜀记》札记[J].文学遗产,2005(03),第16-27页、第157页;龚剑锋、王思思.试论陆游《入蜀记》的史地价值[J].历史文献研究,2009(00),第239-244页;吕肖奂.陆游双面形象及其诗文形态观念之复杂性——陆游入蜀诗与《入蜀记》对比解读[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1(01),第9-13页、第17页 ;黄立新.《入蜀记》人文旅游文献学价值漫议[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5(01),第35-37页。。然而,关于《入蜀记》的影响问题,仅有一些文章简单涉及,尚缺乏专题性的考察。因此,本文就目力所及的材料进行梳理和概括,尝试从文学接受的角度,探讨历史上的读者如何理解和评价《入蜀记》,以及这部作品对于后世的文学写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以期更深入地认识《入蜀记》的文学价值,揭橥这部作品的文学史意义。才疏学浅,或有挂一漏万、解读不当之失,还望方家指正。
一 宋代日记体游记的兴起与《入蜀记》的典范性
宋代是日记体游记兴起并蓬勃发展的时期。至今存世的宋人行游类日记多达数十种(4)参见《宋代日记丛编》前言中的统计,但该统计并不完整。顾宏义、李文整理标校.宋代日记丛编[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第7页。,《入蜀记》是其中文学成就最高,亦是影响最著者。
关于中国古代日记体文学最早起源于何时,虽然众说不一,但基本公认宋代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大规模出现了日记文体作品的时期。明人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中辨析“日记”文体,便以欧阳修《于役志》和陆游《入蜀记》为开端:“日记者,逐日所书,随意命笔,正以琐屑毕备为妙。始于欧公《于役志》、陆放翁《入蜀记》。”(5)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M].卷六百三十九,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而黄庭坚崇宁四年所作的《宜州家乘》被认为是至今存世最早的完全符合现代私日记三要素的日记。
最早的日记体游记或可追溯至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李翱的《来南录》,此作记录李翱由洛阳至广东的行程,但内容十分简略,每日只有只言片语,略述所经地名和所遇人事,几乎没有文学性可言。在陆游之前,还有北宋欧阳修的《于役志》和张舜民的《郴行录》影响较大。
《于役志》中记录了欧阳修从京城开封到谪所夷陵一路上的见闻,同陆游入蜀一样,走的是长江水路。陆游创作《入蜀记》显然受到了《于役志》影响,《入蜀记》有一段记载便提及此书:“十八日。小雨,解舟出姑熟溪,行江中。……夜行堤上,观月大信口。欧阳文忠公《于役志》谓之带星口,未详孰是。《于役志》,盖谪夷陵时所著也。”(6)钱仲联、马亚中.入蜀记校注·陆游全集校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第71页。《于役志》虽然在《来南录》以简单记录日期、行程为主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亲友往来、游览宴饮、天气变化等内容,文学性和情感性增添了不少,但叙述仍较简略,在文体形式上亦几乎没有发展。
而张舜民的《郴行录》则始具丰厚之质,不仅篇幅大大增加,内容也颇为精赡。梅新林《张舜民〈郴行录〉考论》一文从内容、结构、文笔三个层面,论证了《郴行录》与《入蜀记》《吴船录》间一脉相承的关系,认为《郴行录》“奠定日记体游记之基本格局”,“实为我国游记发展史上第一部臻于成熟的长篇日记体游记”。(7)梅新林、崔小敬.张舜民《郴行录》考论[J].文献,2001(01),第151-157页。《入蜀记》中亦有与《郴行录》的直接对话,“张芸叟《南迁录》(注:《郴行录》之别名)云:‘庾亮镇浔阳,经始此楼。’其误尤甚。”(8)钱仲联、马亚中.入蜀记校注·陆游全集校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第94页。可知陆游对《郴行录》十分熟稔,《入蜀记》的写作自然也受其影响。
从内容上看,《入蜀记》较《来南录》《于役志》《郴行录》等作品篇幅更长,所载事物亦更为丰富。而形式方面,两宋之际日记体游记出现了从干支纪日到夏历纪日的转向,与前述作品以干支纪日的方式不同,《入蜀记》采用了更具现代性的夏历纪日法。这种方式可以避免干支纪日法六十日一轮回容易重复的问题,更适合时间跨度大的长途旅行的记录。李杰《论〈入蜀记〉的游记特征》一文认为“陆游改变了传统的纪日方式,首次变干支纪日为夏历纪日。”(9)见李杰.论《入蜀记》的游记特征[D].太原:山西师范大学,2012,第32页。此说有误。实际上郑刚中作于绍兴九年(1139年)的《西征道里记》已经开始使用夏历纪日,时间远在《入蜀记》之前(10)感谢吴晋邦师兄指正。。当然,两部作品的影响力不可同日而语。另外,陆游突破了以往日记体游记择日记事的特点,逐日而书,旅行中一百五十余日几乎每日都有记录。即便偶有几日当天没有具体事件可写,也会留下日期。这种方式使得文章中的时间线索更加明确,游踪更加清晰,也使得对沿途风景与见闻的描摹更具有连贯性,形成了《入蜀记》如长卷山水一般宏大又完整如一的格局,“打破了以往游记片段式写山摹水、纪行状景的狭小格局,拓展了游记所呈现的时空范围”(11)李杰.论《入蜀记》的游记特征[D].太原:山西师范大学,2012,第31页。。
南宋日记体游记中还有一部不得不提的乃是范成大的《吴船录》。范成大于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出任成都府路安抚兼四川制置使,淳熙四年(1177年),因病召还,是年五月二十九日自成都起程,沿长江水路东行,于十月三日抵达姑苏盘门,将这四个多月的行程逐日记录。《吴船录》的写作时间只比《入蜀记》晚了七年,且二者一为“出蜀”,一为“入蜀”,皆是沿长江舟行,行程上大部分重合(从苏州至夔州段),所游览的景点也多有重复之处,因此,这两部作品常被相提并论,以其高超的文学成就,成为南宋日记体游记中的双璧。而且两部游记的作者也交情匪浅——二人本为旧识,陆游入蜀途中,曾遇到出使金国的范成大,并在《入蜀记》中留下这样一段记录:
奉使金国起居郎范至能至山,遣人相招食于玉鉴堂。至能名成大,圣政所同官,相别八年,今借资政殿大学士、提举万寿观、侍读,为金国祈请使云。(12)钱仲联、马亚中.入蜀记校注.陆游全集校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第38页。
五年后,范成大任四川制置使,还曾聘任陆游为参议官,二人共事两年,主宾相得,多有酬唱往来。鉴于二人的这段交往,范成大在写作《吴船录》前,极有可能已经阅读过《入蜀记》并受到了它的影响。《吴船录》前详后略,前半部分对蜀中风景见闻的记述较为详尽,而余下行程则越发简略,给人以头重脚轻之感,从结构布局和内容的完整性来看,不如《入蜀记》。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评《入蜀记》曰:“相其体制,似尤在石湖诸记之上。”(13)周中孚.郑堂读书记[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第416-417页。有学者猜测,很可能是因为自夔州以后的山川风物《入蜀记》已经做过描绘,所以对范成大的书写形成了限制,使他渐渐丧失了写作的热情(14)苏迅.文字因缘非偶然——从陆游的《入蜀记》到范成大的《吴船录》[J].江南论坛,2005(05),第56-59页。。若此说成立,则可看出《入蜀记》在当世便已经对同代人的同题材写作构成了某种“影响的焦虑”。
《吴船录》的写作与《入蜀记》同中有异。从体式上看,两者都是逐日记录,但《吴船录》采用的仍是干支纪日法,与《入蜀记》采用夏历不同。从内容上看,二者在保留了魏晋以来游记记录行程地点、山川形胜和民风民俗等实用性内容的基础上,将视线重点转向了人文领域,大量记载了旅途中文人们的郊游宴饮活动,以及登临历史古迹、考察文化故址的经历,沿途寺庙、宫观、园林、碑刻、名人故居等人文景观成为考察书写的对象,反映出南宋作者对地理空间的文化兴趣。据统计,“《吴船录》所记人文景观的数量为 89 种,《入蜀记》为 100种;《吴船录》所记自然风光为15 种,《入蜀记》为16 种:两书所记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之间的比例都在六比一左右,远远高过前代的行记、地志”(15)徐姜汇.宋代长江行记书写的人文转向——以《入蜀记》《吴船录》为中心[J].人文杂志,2019(03),第77-83页。。同时,文中经常引据诗文,考证掌故,追忆名贤,呈现出鲜明的人文化特征(16)具体原因可参见徐姜汇《宋代长江行记书写的人文转向——以〈入蜀记〉〈吴船录〉为中心》一文第三章“人文转向的发生缘由”中的讨论。。这种人文化的倾向在《入蜀记》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吴船录》虽偶有诗文掌故的引用和考证,但大部分内容仍然是叙事述景,而《入蜀记》中对诗词典故、历史故实的运用和考据则不胜枚举,占据了相当可观的篇幅。其资料之丰富,使得《入蜀记》被后世的类书、方志、诗文注本和辞典等著作频繁征引。陆游还大量运用了“引诗状景”的表达方式(17)李杰在《论〈入蜀记〉的游记特征》第四章第二节中认为陆游首创“引诗状景”之法,此说当误。张剑教授指出,北宋张礼《游城南记》中已有引诗状景的片段。但在游记中如此大面积、高频次地引用诗词以状风景,在《入蜀记》之前尚未见先例。参见李杰.论《入蜀记》的游记特征[D].太原:山西师范大学,2012,第31-33页。,引用前人的诗句来描绘眼前的景观,融风景描摹与诗词考证于一炉。据蒋方统计,次数多达一百一十六次(18)参见蒋方《入蜀记校注》前言。蒋方.入蜀记校注[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第9页。。这样的表现手法使得自然山水与文化山水和谐地融为一体,为自然风物增添了几分诗意,也使得前人的诗文灵动鲜活起来,有了历历在目之感,展现了陆游作为文学家独特的审美品味和丰富的学识。《入蜀记》和《吴船录》所代表的南宋日记体游记的人文转向,赋予自然山水以文化内涵,拓宽了游记的表现空间,为后世游记发掘出新的发展方向,形成了一类“文化型游记”,如明李日华《玺召录》,清王士禛《蜀道驿程记》,乃至今人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等作品,均属此类。
宋代为日记体游记的肇兴期,而《入蜀记》又是宋代日记体游记中的集大成者,也是其中公认文学成就最高、声名最广、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作品。虽然就时间顺序而言,日记体游记的一些写作特点并非都首见于《入蜀记》,但在《入蜀记》中表现得更为成熟和丰富,另外,就实际的传播与接受情况而论,《入蜀记》乃是早期日记体游记中被最多读者阅读和学习的作品之一,许多人对日记体游记的认识正是从以《入蜀记》为代表的这一批作品开始。因此可以说,《入蜀记》对日记体游记基本格局的定型以及后世游记散文的写作起到了典范性的作用,产生了显著的实质性影响。
二 至文与良史:后世读者对《入蜀记》的总体评价
陆游作为南宋诗坛的佼佼者,其文名长期为诗名所掩。实际上陆游不仅长于诗歌,散文方面造诣亦高,其《渭南文集》卷帙浩繁,文备众体,又有《老学庵笔记》《斋居纪事》《南唐书》等名作。南宋诗人张淏在《会稽续志》中称赞陆游的文章“学问该贯,文辞超迈”,“志铭记叙之文,皆深造三昧”。(19)张淏.(宝庆)会稽续志[M].卷五,清嘉庆十三年采鞠轩刻本。四库馆臣虽认为陆游“以诗名一代,而文不甚著,集中诸作,边幅颇狭”,但仍然肯定其“元祐党家,世承文献,遣词命意,尚有北宋典型。故根柢不必其深厚,而修洁有余。波澜不必其壮阔,而尺寸不失。士龙清省,庶乎近之。较南渡末流以鄙俚为真切、以庸沓为详尽者,有云泥之别矣”(20)永瑢.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第1381页。。钱钟书则指出:“陆氏古文仅亚于诗,亦南宋高手,足与叶适 、陈傅良骖靳。”(21)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1442页。
《入蜀记》作为陆游的散文代表作,历来为读者所激赏。古人对《入蜀记》的赞誉,有的从文学角度进行评价。如明人方以智在读书随笔中称赏了其流畅自然的行文风格和精炼传神的文笔,推崇其为无意而成的“至文”:
陆放翁《入蜀记》,有酷好者。夫无意为文,文之至也。状物适状其物而止,叙事适叙其事而止。不增不减,自尔错落,然是通神明、类万物,古今称谓,信笔淋漓,乃能物如物、事如事,而成至文耳。(22)方以智.浮山此藏轩别集[M].合肥:黄山书社,2019,第108-109页。
无独有偶,钱谦益《题南溪杂记》中亦曾引袁中道语,同样认为《入蜀记》简炼自然,“无意为文”,并给予其“天下真文”的高度评价:
袁小修尝云:“文人之文,高文典则,庄重矜严,不若琐言长语,取次点墨,无意为文,而神情兴会,多所标举。若欧公之《归田录》,东坡之《志林》,放翁之《入蜀记》,皆天下之真文也。”老懒废学,畏读冗长文字。近游白门,见寒铁道人《南溪杂记》,益思小修之言为有味也。(23)钱谦益.牧斋有学集[M].卷四十九,四部丛刊景清康熙本。
明人萧士玮也欣赏《入蜀记》信笔而至的自然之美,形容它“随笔所到,如空中之雨,小大萧散,出于自然”(《南归日录小序》)(24)萧士玮.春浮园集[M].文集卷上,清光绪刻本。。 王昶在《滇行日记自序》中亦评价《入蜀记》:“昔人称其信手抒写,别是一种文字,信然。”(25)王昶.春融堂集[M].卷三十七,清嘉庆十二年塾南书舍刻本。明何宇度则称赞《入蜀记》描摹风景时如诗如画的妙笔,以为其“载三峡风物,不异丹青图画,读之跃然”(26)湛之编.杨万里范成大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4,第171页。。清人文廷式亦赞扬《入蜀记》描景状物的辞采“上接少陵有真赏”(27)文廷式.文廷式集[M].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18,第288页。。
从以上评论中,我们不难发现,古之读者对《入蜀记》的文学品鉴中,“自然”,是最被看重的一个特点。这种自然是“无意为文”“随笔所到”的随性与真实,亦是一种不加修饰的平淡简约之美。这与陆游本人的为文主张是完全一致的。《入蜀记》中,陆游在经过头陀寺时,对寺中碑文骈俪卑弱的风格大为不满,并盛赞了欧阳修提倡古文,革新文风的功劳:
简栖为此碑,骈俪卑弱,初无过人,世徒以载于《文选》,故贵之耳。自汉、魏之间,骎骎为此体,极于齐、梁,而唐尤贵之,天下一律,至韩吏部、柳柳州大变文格,学者翕然慕从。然骈俪之作,终亦不衰。故熙载、锴号“江左辞宗”,而拳拳于简栖之碑如此。本朝杨、刘之文擅天下,传夷狄,亦骈俪也。及欧阳公起,然后扫荡无余。后进之士,虽有工拙,要皆近古。如此碑者,今人读不能终篇,已坐睡矣,而况效之乎?则欧阳氏之功,可谓大矣。(28)钱仲联、马亚中.入蜀记校注.陆游全集校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第121页。
可见陆游本人所欣赏的,正是平易自然的文风。他曾有《文章》一诗论及他的作文主张: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粹然无疵瑕,岂复须人为!君看古彝器,巧拙两无施。汉最近先秦,固已殊淳漓;胡部何为者,豪竹杂哀丝?后夔不复作,千载谁与期!(29)钱仲联、马亚中.入蜀记校注.陆游全集校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第72页。
强调的正是这种无需人为、返璞归真的“自然”之美。四库馆臣在《渭南文集》的提要中认为陆游“其文固未能及是,其旨趣则可以概见也”(30)永瑢.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第1381页。,但从人们对《入蜀记》的评价来看,陆游的文学追求已经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实现。
而《入蜀记》何以能够实现这种自然高妙的表达效果,除了陆游对于文章天然旨趣的自觉追求以及“无意为文”的创作初衷以外,还与沿途奇山秀水对作家情性和灵感的激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对此,黄宗羲解释道:“余唯山川文章相藉而成,然非至性人固未易领略。尝读陆务观《入蜀记》,揽结窈冥,卷石枯枝,谈之俱若嗜欲,故剑南之诗遂为南渡之巨子。”(31)黄宗羲.黄宗羲全集[M].第10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第22页。他认为山川与文章相辅相成,且需要至情至性之人才能领会其中妙义。黄宗羲夸赞陆游的文章充满了力量,而这既来源于长江沿岸雄奇风光的“江山之助”,亦是作家真情至性自然流露所形成的情感的力度(32)诸雨辰.黄宗羲的文气说辨析[J].文学遗产,2019(04),第189-191页。。
陆游不仅是文坛巨匠,亦是史学大家,曾三作史官,修《两朝实录》《三朝史》,并著有《南唐书》。因此,陆游的文章也往往彰显出史家的渊博学识和精严品格。祝允明《书新本渭南集》后曾盛赞其文曰:“放翁文笔简健,有良史风,为中兴大家。”(33)孔凡礼、齐治平编. 陆游资料汇编[M]. 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123页。《入蜀记》即包含于《渭南文集》中,陆游之史才与博学在《入蜀记》中亦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成为《入蜀记》极为突出的一大特色。《入蜀记》将人文历史与自然景观融于一炉,常常就沿途地区的名胜古迹、历史掌故、军事政治、兴废沿革进行一番夹叙夹议的精彩描述,即景抒情,咏古论今,寄慨遥深。古人对《入蜀记》的评价中,对史学层面的关注似乎较文学更甚。四库馆臣将《入蜀记》收入“史部传记”类,提要中对于《入蜀记》的文学成就仅以“游本工文,故于山川风土,叙述颇为雅洁”一语带过,随后便以大篇幅浓墨重彩地指出《入蜀记》的史地价值:“于考订古迹,尤所留意。……足备舆图之考证。……亦足广见闻。其他搜寻金石、引据诗文以参证地理者,尤不可殚数。非他家行记徒流连风景、记载琐屑者比也。”(34)永瑢.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第529-530页。清人程瑶田重视《入蜀记》对人文古迹的考证功夫:“其过黄州也,纪苏公之东坡,纪雪堂,纪居士亭,若小桥、暗井之属,一一取苏诗证之。其至赤壁矶也,则以图经公瑾、孟德事为不可考,引太白之歌,苏公之赋及其乐府,以为一字不轻下,而因论韩子苍诗,直以图经之言为真者,为考之不审也。其所记者,非徒纪其日行之程而已也。”(35)程瑶田.通艺录[M].合肥:黄山书社,2008,第197页。清人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中亦强调《入蜀记》“因逐日记其道路所经,缕述风土,考订古迹,俱极详赡,而引据亦多精确。”(36)周中孚.郑堂读书记[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第417页。晚清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中也格外关注《入蜀记》于纪行载事之外考证古迹、议论朝政的特点,其评价范成大之《吴船录》与陆游之《入蜀记》曰:“范、陆二公所作皆极经意,山水之外,多征古迹,朝夕之事,兼及朝章,脍炙艺林,良非无故。”(37)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第1268页。他认为这些史学层面的关切乃是《入蜀记》得以名震文坛的重要原因。
《入蜀记》中对于历史的关注不仅出于陆游的考证趣味,更寄寓了他对军事政治的深沉思考和对国家命运的关切。据《宋史·陆游传》载,在陆游开启这场入蜀之旅之前,他曾因“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38)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12058页。遭到弹劾,归居山阴故里多年,而此次被重新启用,他忧心国事、主张用兵的想法并未消歇,反而在《入蜀记》中多有流露。尤其是陆游在文中多次提及南唐旧事,不仅展现了他对南唐历史的熟稔,亦颇有借古讽今,以前朝亡国教训劝诫当朝之意。前人对于陆游的这一用心亦有敏锐的体察。如清代藏书家吴騫便在其《入蜀记跋》中感慨道:
及余观《入蜀记》,则又不能不为之嘅然者,盖行役人之所有,不过述其山川、详其风土已耳。独放翁于一路关津要隘,以及古今防守治忽之迹,靡不留意。至于溯巫峡、上瞿塘、拜昭烈之遗庙、观武侯之故垒,若低徊留之而不能去者,盖深惜当日国之无人,而付恢复之事于不可问,正不必临殁《示儿》一绝,而后觇此老毕生之心事也。然则世有读是编而犹屑屑以寻常纪行之书目之者,非特不知放翁,并不识吾以文所以表章之雅意矣。(39)吴骞.愚谷文存补遗[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第22页。
而清代的另一藏书名家钱曾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认为陆游在《入蜀记》中“凡途中山川易险,风俗淳漓,及古今名胜战争之地,无不排日记录,一行役而留心世道如此,后时家祭无忘盖有素焉”(40)钱曾.读书敏求记[M].卷二,清雍正四年松雪斋刻本。。
清人王霖《书放翁入蜀记后》一诗表达了他阅读《入蜀记》的感想:
南渡中原事日艰,小臣生在敢偷安。片帆不怕冲炎去,好趁峨嵋六月寒。哀猿啼彻暮云边,杜宇声声破晓烟。蜀道曾闻天样似,诗狂正要上青天。十二巫峰峰最奇,岷江江水碧玻璃。峡船轻疾如飞鸟,坐听巴娘唱竹枝。晚岁归来雪满簪,镜湖侧畔一茅庵。球场射圃风流歇,魂梦犹能到剑南。(41)王霖.弇山诗钞[M].卷三,清道光五年刻本。
他以放翁为实现报国之志而入蜀起笔,又以其晚年退居乡野依旧梦回剑南军营收尾,以爱国情怀贯穿全篇,在他的笔下,蜀地的绮丽风光中也仿佛寄寓着诗人从未消泯的家国之情。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曾提出著名的“史才三长说”,认为好的史家须兼具史才、史学和史识(42)《旧唐书》卷一百二列传第五十二“刘子玄”条记载:“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自古已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夐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时人以为知言。”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第3173页。,已成为史学界公认的标准。《入蜀记》虽然并非严肃的历史著作,但正如上述古人评价所指出的,这部作品展现了陆游驾驭史料的优秀功力和高超的文字表达能力(才),广博的知识积累和深厚的学养(学),更重要的是,它还包含着陆游对历史事件的独到见解与深刻反思,寄寓着他以史鉴今的关切和忧国忧民的情怀(识),因此,不失为一部“良史”。
总之《入蜀记》既具高妙文采,又具良史情怀,堪称宋代日记体游记的最高峰。
三 共鸣与对话:后世对《入蜀记》的情境体验
《入蜀记》不仅是放翁真实行游经历的记录,也通过文字的形式,为阅读者留下了一方虚拟的文学空间。当后世读者翻开《入蜀记》,踏入这方由笔墨创设的天地中,历史的山水与现实的景观重叠,接受者自身的生活经验与陆游曾经的见闻感发交织,碰撞出不同的灵感火花,也产生了诸多带有私人印记的阅读体验。比起前述看起来更为冷静持正、不含过多主观情绪的品评鉴赏之语,这些更为个人化的表达因结合了每个个体独特的生活情境和真切的思想感情,而显得更加鲜活动人。
《入蜀记》为读者建构起一方历史的空间。在这篇游记中,陆游以他的诗人之眼和学人之笔为当时的山川风物留下了一张张历史的剪影。后之读者故地重游,不再是单纯地欣赏眼前的风景,而是带着《入蜀记》所提供的历史记忆,在想象的旧山水与现实的新山水之间前后流连,完成这段跨越时空与虚实的旅程。
一如放翁在《入蜀记》中引证前人诗文描摹风景、考证古迹一般,《入蜀记》也成为诸多后世读者重游放翁行迹的前知识,以及他们题咏相关风景名胜的前文本。由长江入蜀的诸多景观经由放翁的品题,具有了更丰富的文化意义,它们频繁出现于方志等地方文献中,出现在诗词典故的注解中,亦成为许多文人墨客探访与吟咏的对象。当人们踏上入蜀之旅时,往往会联想起千百年前放翁的行程,引发异代同游的奇妙体验。在后世文人关于长江及蜀地之行的记录中,提及《入蜀记》的片段不胜枚举。如王士禛《登高唐观神女庙记》:
《入蜀记》云:“神女祠旧有乌数百,送迎客舟。乾道元年忽不至。至今绝无一乌。”盖放翁未之见也。过此即十二峰,舟人指似得其六七,缥缈秀拔令人有骖鸾驾鹤之想。中有三峰连缀其一,修纤如人扬袂而立,俗曰美人峰,即放翁所谓神女峰,最为纤丽,宜为仙真所托者也。会风急滩迅,所谓十二峰者不及尽瞩,然陆务观、范至能经此所见亦仅八九峰耳。(43)王士禛.带经堂集[M].卷七十六,清康熙四十九至五十年程哲刻本。
他在欣赏眼前山水的同时亦时时不忘不在现场的放翁,想象着哪些风景是陆游见过的,哪些是他无缘得见的,仿佛时空重叠,陆游正坐于身侧,陪他乘舟同游一般。又如钱楷咏龙隐岩放翁“诗境”手迹云:“又从入蜀游尘后,墨妙思公涤砚埃。”(44)钱楷.绿天书舍存草[M].卷四,清嘉庆二十三年阮元刻本。其自注“余前年使蜀由蜀江至夔府,行程皆与放翁《入蜀记》相合”。谢堃咏太子矶云:“孟襄阳后诗怀澹,陆剑南来心事违。”(《登太子矶》),自注“矶有孟浩然诗,陆放翁入蜀纪行。”(45)谢堃.春草堂集[M].卷四,清道光二十年曲邑奎文斋刻本。李联琇《访医记》记录自己访医行程曰:“一路风景,望亭以北如放翁《入蜀记》所云夹河皆长冈高垄,气象窘隘,非枫桥以东比也。”(46)李联琇.好云楼初集[M].卷二十三,清咸丰十一年至光绪八年刻本。他们都将自己的旅途与历史上陆游的行程联系在一起,透过眼前的景物想象放翁当年游赏的情状,其间引述《入蜀记》文字与细节信息如信手拈来,足见他们对这部作品的熟稔。
在这些描摹长江两岸与巴蜀大地奇丽风光的文字当中,不仅有与放翁的共鸣,也有和放翁的对话。
熊士鹏《题鲍觉生学使荆南杂咏》一诗盛赞了荆南山水:
山水惟蜀奇,奇皆在楚地。秭归接巴巫,滩与峡争至。夔门不可开,险奥心为悸。天生浣花翁,刻划偏尽致。下笔逾五丁,巧凿神鬼畏。至今秦川闲,未到如面对。始知才人心,而与造化类。所以荆南诗,杜陵体皆备。目眩峡光摇,耳骇滩响碎。森然石如牛,真向人面坠。胜读吴船录,差强入蜀记。范陆若见之,当必三舍避。(47)熊士鹏.鹄山小隐诗集[M].卷十四,清嘉庆二十年稽古阁刻瘦羊录本。
他认为楚地山川雄奇壮阔,哪怕是《入蜀记》的描摹亦不过是差强人意,无法再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李荣陛则有着截然不同的体会,其《巴东胜迹记游》表达了他游览巴东后的失落:“始予被檄运铜,即于行箧检读《入蜀记》,极称巴东之美。予之至此,适因帮船理柁,停一日探之。其江山虽雄而顽犷未化,无层复杳深之趣,不知何由奖借于渭南,至举为吴楚五千里间第一胜处。昔人谓‘论诗如评女色,妍媸随人意',然哉!”(48)李荣陛.厚冈文集[M].卷十六,清嘉庆二十年亘古斋刻本。在他眼中,《入蜀记》对巴东风景的称赏反而成了溢美之词,实际所见则令人大失所望。

文字的表达效果与山水的实际观感之间的落差,还体现在随着时代变迁而发生的江山变化之中。方志、地理志等文献中常常征引《入蜀记》的记载,作为追溯古今沿革的依据。如李日华《嘉兴县志小序》引《入蜀记》来说明嘉兴县的发展变迁:“尝读宋陆务观《入蜀记》云:‘自崇德至平望,尽日皆行大泽中,抵毘陵始有安流。’则知前此汪然半属巨浸,非若今日阡陌绮错而廛庐托处也。”(50)李日华.李太仆恬致堂集[M].卷十七,明崇祯刻本。透过《入蜀记》的记载,人们得以见到一座城市繁盛之前的景象。
比起从荒凉到繁盛的城市发展史,由盛转衰的古今对比更易引发骚人们的感慨。易顺鼎在诗中表达了他寻访白云亭不遇的怅惘:
白云亭子天下无,巴东峡里雄夔巫。千岁危柯虎伸爪,四时飞瀑龙垂胡。登临输与鉴湖客,今日荒亭已无迹。江山寂寞我来迟,惟见青天片云白。(《陆务观〈入蜀记〉极言巴东白云亭之胜,今访之不得,怅叹赋此诗》)(51)易顺鼎.蜀船诗录.琴志楼集[M].清光绪至民国刻本及铅印本。
金武祥《陶庐杂忆》记录了和友人同游常州荆溪馆驿桥的经历,其友刘葆真联想到《入蜀记》中“夜月如昼,与家人步月驿外”的描写,想象着驿桥当年的胜景,感叹道:“何今与昔不同如此!”(52)金武祥.陶庐杂忆续咏[M].清光绪二十四年至民国八年江阴金氏广州递刻本。
王昊《新丰》一诗也表达了类似的感伤情怀,其序曰:
李太白诗云:“南国新丰酒,东山小妓歌。”又唐人诗云:“再入新丰市,犹闻旧酒香。”陆放翁《入蜀记》以为皆指此,非长安新丰也。然予屡过之,荒凉日甚,盖古今不同如此。
昔日繁盛的酒肆歌场如今却败落为“泥墙草店”,抚今追昔,诗人不禁发出了“唐宋繁华一梦间”的喟叹(53)王昊.硕园诗稿[M].卷二十二,清五石斋钞本。。
而他在吕城寻访南朝陵墓的经历更是一次与放翁穿越时光的同行和对话,其诗《吕城闸》序云:
陆务观《入蜀记》云:“早过吕城闸,始见独辕小车,过陵口见大石兽偃仆道傍,已残缺,盖南朝陵墓,则陵口殆与吕城密迩。惜舟中失携,《润州志》莫从考证。”嗟乎!自放翁至今又四百年矣,陵墓遗迹固宜无一存者,然而重可慨也。系之以诗。
四百年前放翁行经时,南朝陵墓已成残迹,而如今更是荡然无存。诗人回顾着“渭南陆叟曾经过,叹息犹传乾道年”,慨叹着“故物如闻石马嘶,空台共滴铜人泪。残碑废碣梦凄凉,肠断花开遍野棠”(54)王昊.硕园诗稿[M].卷二十二,清五石斋钞本。。两位诗人的慨叹前后呼应,宛如一曲忧伤的二重咏叹调,他们笔下一次更比一次破败的景象让人加倍感到光阴的无情和历史的苍茫。
文学的山水未必要亲自抵达。在《入蜀记》所创造的虚拟空间里,借助想象的力量也可以扬帆远航,和放翁同游,与放翁对话。
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记录了他阅读《入蜀记》的体会:
放翁记有云:“至平江过盘门,望武邱楼塔,正如吾乡宝林,为之慨然。又过舒州长风沙有云:西望群山靡迆,岩嶂深秀,宛如吾庐。南望镜中诸山,为之累欷。(中略)越中光景,可见一斑,不禁乡思坌集矣。呜呼,渭南越产,而西川之行,全家上官,万里如砥,然尚触目生感,不胜故国之思,况如仆者,家陷虎狼之室,身居沟壑之滨乎?(55)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第1268页。
作为陆游的老乡,《入蜀记》中对越中风景的描摹和对故乡的怀念勾起了李慈铭的思乡之情与身世之感。他虽未亲抵其境,但通过放翁之笔,也仿佛眺望了武邱楼塔与舒州群山,在相似的风景间勾连起对故乡的记忆。
还有一些读者借助《入蜀记》想象远行亲友的行踪,虽身不能至,但在陆游留下的这一方虚拟空间中,他们的心可以与所念之人相伴而行。
叶凤毛《读陆放翁入蜀记怀凌氏女》一诗记录了一位父亲对远嫁女儿的牵挂:
陆子昔判夔,大江溯轻舠。遇胜必流连,似忘行役劳。反覆日纪载,不殊亲身遭。吾闻江行人,忧乐常相交。江水淼无际,巨舰比一毛。无风不能行,风行又惊涛。入峡争滩水,有如上天高。两山夹奔湍,乱石攅利刀。一触辄破碎,性命何处逃。方今春水生,其势尤怒豪。奈何乘此险,而博一下僚。吾女闭深闺,未识黄浦潮。既嫁当从夫,宁顾途路遥。皖江发一书,到今阅百朝。幸能安稳渡,应抵江阳皋。两孙吾所爱,端良见垂髫。嗟我老无力,不得随汝曹。矫首望岷峨,心旌日摇摇。(56)叶凤毛.说学斋诗续录[M].卷十,稿本。
“反覆日纪载,不殊亲身遭。”经由放翁之笔,诗人仿佛亲眼见到了长江的惊涛骇浪,亲身感受到了旅途的凶险。日记一写百余日,女儿一去亦是百余日。老父对照着《入蜀记》,日日掐算着爱女应到何处,牵肠挂肚,忧心百结,舐犊之情令人动容。
陈苌《有感》一诗则表达了对远行友人的挂念:“琴鹤图书共一船,纪行篇帙继前贤。料应十月巴江水,重记诗翁入蜀年。”诗人自注:“放翁《入蜀记》于冬月入峡,计兄亦当于是时过巴江也。”他对照着《入蜀记》中陆游船过巴江的时间,想象着友人同样在十月渡江的画面,应是“约略风流近务观”(57)陈苌.雪川诗稿[M].卷六,清康熙莺湖苏啸堂刻本。。
《入蜀记》不但承载着人们对山川、对历史、对故乡、对亲友的情感,也为囿于现实空间限制的读者们打开了通往远方风景的大门,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想象的资源。一些诗人从《入蜀记》对山川风物的描绘中获得作诗的灵感。宋末元初诗人戴表元便在《刘仲宽诗序》中阐述了他独特的作诗法:“余少时喜学诗,每见山林江湖中有能者,则以问之,其法人人不同。有一老生云:‘子欲学诗乎?则先学游;游成,诗当自异。’于时方在父兄旁,游何可得?但时时取陆放翁《入蜀记》、范至能《吴船录》之类,张诸坐间,想象上下,计其往来,何止日行数千万里之为快。”(58)李修生主编.全元文[M].南京:凤凰出版社,1998,第130页。他借《入蜀记》《吴船录》等游记作品张开想象的翅膀,幻想自己随着作者一起畅游于山水之间,从而激发诗兴,颇有宗炳“卧游”之趣味。无独有偶,明末清初诗人黄宗会在《缩斋后记》中也提到了类似的方式:“余少而不羁,长而畸僻,每有洗盋名山之愿,顾拘于累,窘于力,则时时取范石湖《吴船录》、陆放翁《入蜀记》等书,呻吟讽咏,以仿佛古之赋《远游》、歌《招隐》者,慨然怀其人,形诸梦寐。”(59)黄宗会.缩斋后记.沈粹芬等辑.清文汇[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0,第50页。可见对于没有条件游玩山水的诗人而言,《入蜀记》之类的游记作品可以成为他们想象的助力,以优美生动的文笔,带领他们抵达诗意的远方。
《入蜀记》为后世读者还原了一方历史的山水,建构起一片想象的空间,让阅读者得以跨越时空的距离,或以亲身践履,或扬起想象之帆,和放翁一路同行,共话江山。一方面,陆游传神入妙的文笔和细致入微的考察为风景的再现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入蜀记》日记的形式也使文字更具纪实性和现场感,从而让读者更有身临其境的体验。人们在阅读《入蜀记》的同时,也以自己的生命体验,为这部作品留下了私人化的注脚。这些后世的回音此起彼伏,谱写了《入蜀记》的多彩续章,也为《入蜀记》开拓出更为丰富的意义空间。
四 《入蜀记》对后世纪游类作品的影响
《入蜀记》对后世的文学影响不仅表现在阅读者的评论感发中,更体现在后来人追摹前贤的创作实践中。作为中国古代游记散文的典范之作,《入蜀记》是后世诸多文人学习、模仿的对象。现存文献当中保留了大量明清时期的《入蜀记》仿作,其中亦不乏精品。
《入蜀记》仿作主要集中于日记体游记一类。如前文所述,《入蜀记》是日记体游记的早期代表作,后世写作此体者不论是有意或无意都不免受到其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从时间上看,《入蜀记》并非最早,北宋诸行记中,至少《郴行录》便已具备了日记体游记的基本体式。且体式大成之后,后来者未必都会回想起草创者。因此,本文讨论后来者对《入蜀记》的模仿,更侧重于其中有自觉意识与直接证据者:或由作者本人自述心曲,明言受到《入蜀记》影响的作品;或由至交好友代言心声,在序跋当中点明与《入蜀记》关联的作品(选入序跋也体现了作者的认可);或形式与内容和《入蜀记》高度相似,二者相关性得到学界公认的作品。
在这类仿作中,明代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当属其中的佼佼者。徐霞客(1587年—1641年),名弘祖(一作宏祖),字振之,号霞客,江阴人,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文学家。他历时三十余年,行遍大江南北,写下十七篇名山游记和《浙游日记》《江右游日记》《楚游日记》《粤西游日记》《黔游日记》《滇游日记》等著作,经后人整理成为六十余万字的恢宏巨著《徐霞客游记》,成书于崇祯十五年。《徐霞客游记》被誉为系统考察中国地质地貌的开山之作,但其所关注的不仅限于自然地理的内容,也包括不少人文地理信息,如各地的民风民情、少数民族、商业贸易等等。它同时也是一部文学名著,文笔优美,写景如画,颇具艺术性。清代学者钱谦益曾称赞它为“此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认为“天壤间不可无此书也”(60)徐弘祖.徐霞客游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286页。。
《徐霞客游记》继承了《入蜀记》以夏历纪程、逐日记录的写作方式,两书的关系及异同前辈学者考述已详。黄建宏认为《入蜀记》“开了徐宏祖日记体游记的先河”(61)黄建宏.古代游记艺术琐谈[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1(01),第68-75页。裘禾峰《论日记体游记的高峰〈徐霞客游记〉》一文指出《入蜀记》与《徐霞客游记》“文体结构上相似,但选取的内容不同”;“语言句式上相似,但更具画意不失准确”;主体精神不同,一为文人,一为才人;且《徐霞客游记》较前者更具有“独立的山水意识”(62)裘禾峰.论日记体游记的高峰《徐霞客游记》[C].2011中国江阴徐霞客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11,第204-208页。。王慧颖认为《入蜀记》中“诸如名物地理、历史掌故的考证内容既未占主导地位,在作者的主观意识上也不具备主动考察的目的,因此也不是真正的科学考察”,而《徐霞客游记》则是中国古代科学考察游记的“集成之作”(63)参见《中国游记文学史》第九章“徐宏祖与《徐霞客游记》的崇高地位”中的论述,此章作者为王慧颖。梅新林、俞樟华主编.中国游记文学史[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第321页。。
明人学习《入蜀记》着力尤深的还有著名文学家萧士玮,前文已论及他对《入蜀记》随性自然文风的欣赏。萧士玮在《南归日录》的序言中以《入蜀记》为例阐明他的创作主张:
余读欧公《于役志》,陆放翁《入蜀记》,随笔所到,如空中之雨,小大萧散,出于自然。昔秦少游绝爱政黄牛书,问其笔法,政曰:“书心画地,作意则不妙耳。”若余此录殆晏元献享客,盘馔皆不预办,客至,人设一空案一杯。既命酒,果实蔬茹渐至。数行之后,谈笑杂出,案上遂尔粲然。但请客亦须仔细,如或不知主翁乐客之意,贪于饮食,责其旋营,客且怒矣。故此录亦未可轻以示人也。即如空中雨点,萧散可人,亦自闲静者得之耳。逃雨者想未必以为然也。(64)萧士玮.春浮园集[M].文集卷上,清光绪刻本。
《南归日录》是萧士玮天启七年(1627年)奉朝命自京城归还杭州的纪行之作,这部作品正是受到《于役志》和《入蜀记》这两部宋代行游日记的影响,不仅模仿其日记体式,而且着意追求其萧散自然的风格,一路描摹风光,叙述见闻,信笔而书,颇具闲适情调,同时文笔清丽流畅,堪称美文。此外,萧士玮的《汴游录》也是记载宦游见闻的日记,内容风格与《南归日录》大体相近。
明代的《入蜀记》仿作还有李日华的《玺召录》,此文记录作者自天启乙丑召为尚宝司司丞赴京途中的见闻,“略仿《吴船录》《入蜀记》之例,而寥寥无所记载”(65)永瑢.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第529-530页。。
清代仿照《入蜀记》而作的日记体游记存世更多。其中比较特别的一类是同样记录蜀地风光和见闻的作品,以清初文坛领袖王士禛的《蜀道驿程记》为代表作。王士禛共著有日记七种,《蜀道驿程记》是其中最早的一部,写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作者典试益州的往返途中。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评价《蜀道驿程记》:“按日纪载,大略仿陆放翁《入蜀记》而作,其间考古述今,亦有足观者,殊较其所作南来北归诸志为优。据其康熙辛未自序,知其历久而成,非他行记率尔操觚者可比也。”(66)周中孚.郑堂读书记[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第421页。王士禛不但沿用了《入蜀记》夏历纪日、逐日而书的形式,也和陆游一样,十分重视对沿途山川地理的考察和文史掌故的考订。同为蜀地行记,《蜀道驿程纪》与《入蜀记》有大量路线重合——陆游由江陵至夔州入蜀,王士禛则经此路线出蜀,但不同的是,经过明清易代的战火,蜀地民生凋敝,文物损毁,早已不复昔日繁华景象。作者在自序中写道:“陆氏之记记其盛,予之记记其衰。后有揽者参互考之,可以观世变云。”(67)王士禛.带经堂集[M].卷七十五,清康熙四十九至五十年程哲刻本。颇有与《入蜀记》今昔呼应,怀古伤今之意。正是在这种感伤情绪与创作意识的主导下,《蜀道驿程记》中时时可见与放翁的隔空对话,亦有多处引《入蜀记》中所载景物与现状相对比。如十月十八日记叙游巴东县之感:
巴东山水顽劣,自夔、巫东下,惊心动魄,应接不暇,至此剩水残山,不堪着眼。而放翁谓白云亭为天下幽奇绝境,且云“自吴入楚,行五千余里,过十五州,亭榭之胜,无如白云者。”岂山水亦因时而显晦耶?(68)王士禛.蜀道驿程记.王士禛全集[M].济南:齐鲁书社,2007,第2581页。
与前文中李荣陛游巴东的体会相似,王士禛也深感巴东山水粗劣,难匹放翁之盛赞。然而,李荣陛对此的解释是“论诗如评女色,妍媸随人意”,不过是惊诧于和陆游眼光的差距;而王士禛则感叹“山水亦因时而显晦”,疑心山川也会因为时代的盛衰而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字里行间流露出忧时伤世之情。
又如同日记归州之行:
归山水粗劣与巴东略似……七里,有宋玉宅,放翁入蜀时尚见石刻。(69)王士禛.蜀道驿程记.王士禛全集[M].济南:齐鲁书社,2007,第2582页。
十月二十日记彝陵州之行:
泊舟入城,访欧阳公绛雪堂故迹,闻《至喜亭记》山谷书尚存断碑数十字,在东门民家作砌石,语州守以他石易之。昔放翁过彝陵时红梨花已不复有,惟公手植双柟尚存其一,今亦化劫灰矣。(70)王士禛.蜀道驿程记.王士禛全集[M].济南:齐鲁书社,2007,第2585页。
放翁入蜀时石刻、柟树尚存,如今却皆已化作劫灰。今昔对比,面对满目的荒凉破败,作者的痛惜之情可以想见。
清人仿《入蜀记》而作的蜀行游记中,较有特色的还有胡云士的《蜀游记程》。这部日记记录了作者告别家人,宦游成都的经历。同为游蜀之作,《蜀游记程》不似《吴船录》《入蜀记》那样专注于水陆行程的记录和沿途古迹的考证,而是将细腻丰富的情感融入日常的书写当中,表达了作者不得已而远游的思乡念亲之情。其友吴骞评之曰:“见其于山川之夷险,风日之晦明,气候之寒燠,人情之冷暖,举历历如在吾目前,而所谓一举足不忘其亲者,亦于是乎可见,岂仅区区纪行之作云尔乎?”(《题胡云士蜀游记程》)(71)吴骞.愚谷文存补遗[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第11-12页。
以上两部作品虽然都和《入蜀记》一样以蜀地为主要书写对象,但面对前作的高峰,他们并未重蹈旧辙,拾前人唾余,而是另辟蹊径,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写下自己独特的心境与体验,从而使作品顶住了经典的压力,在文苑艺林中夺得一席之地。尤其可见《入蜀记》作为经典文本,既是后来者学习借鉴的范本,亦是他们进行同题写作所绕不开的强力竞争对象。无论是否自觉,后人在进行类似题材的写作时,都必须对《入蜀记》有所回避。因此,《入蜀记》对于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不仅仅有正面的典范意义,还有潜在的竞争意义。
除了入蜀之作外,清人还有许多行游他地的日记也以《入蜀记》为学习、仿写的对象。如汪汉倬《入闽记》,记录作者自维扬舟行入闽之见闻,写景记事、考订史材颇为详备,又在行文中“附以五七言古今体有韵之文”(72)朱书.杜溪文稿[M].合肥:黄山书社,2021,第41-42页。。周广业《冬集纪程》,写于作者自海宁赴京应试途中,同《入蜀记》一样长于掌故源流的考证。完颜麟庆《鸿雪因缘图记》,自述作者一生之游历,“博考见闻,兼综条贯生平文章政绩”(73)完颜麟庆.鸿雪因缘图记[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第1-2页。,除模仿《入蜀记》《吴船录》之体例外,还请名家按题绘制了240幅游历图附于书上,卷帙浩瀚,图文并茂。冒辟疆《南岳省亲日记》,记载作者赴湘省亲之行,内容上写景纪实、考订史乘,与《入蜀记》相类,反映了当时灾难过后的社会现状和民众生活。王钺《粤游日记》记录作者自家乡山东诸城赴广东西宁任职途中的经历,语言简练,文笔优美,《四库全书总目》评其“仿陆游入蜀记之体,案日记载。叙述颇简洁,而无所考证。”(74)永瑢.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第575页。此外还有王昶《滇行日记》《商洛行程记》,李绂《云南驿程记》,王定柱《鸿泥日录》及《续录》四卷,傅云龙《北上里志》等。
值得一提的是,《入蜀记》不仅对散文尤其是游记散文的写作影响深远,对后世纪行题材诗歌的创作和编排亦有启发。明末清初诗人朱尔迈(75)朱尔迈(1632—1693),字人远,号日观,海宁人。有《扶桑阁集》《日观集》。便仿照《入蜀记》逐日记录的体例,将他的《西瞻》《锦江》《戎州》《东将》诸集进行了编次,《晚晴簃诗汇》评其“排日为诗,而先以纪程,寓放翁《入蜀记》、石湖《吴船录》之体于诗编中,叙次雅赡,意拟道元,亦称奇作”(76)徐世昌编.晚晴簃诗汇[M].北京:中华书局,2018,第1492页。。晚清诗人赵熙(77)赵熙(1867—1948),字尧生,号香宋,四川荣县人。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亦曾作《送杨昀谷入蜀》七绝数十首,“叙一路所经,若放翁《入蜀记》”(78)陈衍.石遗室文集[M].卷九,清刻本。,王逸塘《今传是楼诗话》曾评其“直可当游记读”(79)汪辟疆撰,王培军笺证.光宣诗坛点将录笺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8,第195页。。
以上所列仅是笔者以有限目力于明清人诗文材料中拾掇而来,其余淹没不彰者,或是受《入蜀记》间接影响者更是不胜枚举。这些仿作并非对《入蜀记》写作模式的简单复制,而是于继承中有创新,于模仿中有超越,灌注了作者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各自的学识才思,各具面目、各生姿态,汇聚成《入蜀记》这轮明月身后或明或暗的群星。后浪的层层翻涌,亦体现出《入蜀记》在文学史的长河中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