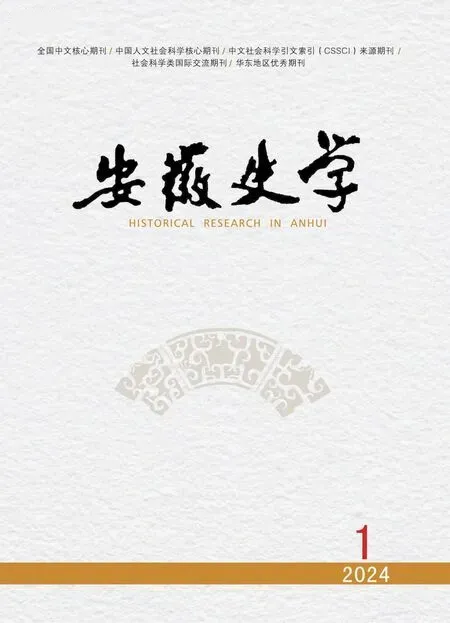明代后期的卫所与地方官府
——以《新安蠹状》所见新安卫与徽州府为中心
王 浩
(安徽大学 徽学研究中心,安徽 合肥 230039)

《新安蠹状》是明万历十四年至十六年徽州知府古之贤在任期间有关施政措施的档案文件汇编,由时任歙县知县彭好古在古之贤离任前编辑成册。学界对于该资料的研究主要聚焦社会经济史,尤其是明代后期一条鞭法在徽州的实施情况。(3)汪庆元:《〈新安蠹状〉探析》,《文献》2005年第3期;陈支平:《〈新安蠹状〉中所见明代后期徽州的条鞭法相关史料》,《徽学》第5卷,2008年;周晓光、王灿:《论明代中后期徽州一条鞭法的实施——以〈新安蠹状〉为中心》,《东北农业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本文则主要讨论《新安蠹状》中有关新安卫的四份公文,探讨明代后期地方官府介入卫所事务的细节。(4)按:《新安蠹状》为孤本,现藏于安徽博物院,本文所用为卞利点校本,参见卞利:《古之贤〈新安蠹状〉点校并序》,(台湾)《明代研究》第19期,2012年。该点校本对原书中的脱漏讹误多有指明,本文在引用时直录正确文字,并对几处错别字、句读有所更正。
一、运官路费的分担
永乐十二年正月,明成祖“命北京、山东、山西、河南、中都、直隶、徐州等卫,不分屯守,各选军士,以指挥、千百户率领,都指挥总卒,随军运粮。”(5)《明太宗实录》卷147,永乐十二年正月庚子,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明实录》校印本,第1729页。一般认为,此举是明代漕军制正式形成之始。不过明代漕军制变动频繁,其中经过三次较为显著的调整,即成化定制、嘉靖改制、万历重建。(6)林仕梁:《明代漕军制初探》,《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新安蠹状》成书的时代,正是明代漕军制在万历初年经张居正改革加以整饬后运行较好的时期。当时的新安卫漕军,隶属于上江总,运漕旗军1250人,浅船125艘,领漕28377石5斗。(7)王在晋:《通漕类编》卷2《十三总所属卫所船军漕粮数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75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290—291页。
徽州府本无漕粮,但需要负责新安卫运粮官军的行粮。既有研究表明,江南地区沿海及腹里卫所军粮一般由地方府县的存留粮供应,主要负责发放漕军的行月粮以及补足卫所军粮的缺额。(8)丁亮:《明代浙直地方财政结构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8—29页。《新安蠹状》上卷所收《呈详议加运官路费缘由》(9)按:本节引文凡未出注者均引自此篇。,所论即是关于新安卫漕军行粮、运官路费分担等事宜。
万历十四年,古之贤接到兵备副使(10)按:此处“兵备副使”,以及后文还将提及的“兵备道”,均指徽宁兵备道。牛惟炳转发上宪批文,要求其调查“新安卫领运官员有无路费及别项资给。如无,应否议加?该卫所有无公费银两堪动,或应作何处派给?”概括起来,古知府需要查明新安卫运官有无路费,如果增加运费银该从何处支给。古之贤行文新安卫询问此事,据后者回文可知,新安卫每年兑运镇江府丹徒县漕粮时,领帮指挥、随帮千百户等运官与旗军一样,仅按例开支行粮三石,并无路费银两,运官盘费往往不敷使用,不得不预支俸粮凑用。增加路费银两正中运官下怀,不过新安卫“止有轻科公费银两,书册刊有定数,别无堪动银两”,鉴于该卫运粮官军行粮本系徽州府麦米银内开支,因此请求就便在麦米银内照数加给运官路费。
古之贤在递交兵备道的呈文中,对于卫所要求增加领运官员路费银(合计30两)的提议表示赞成,但他强调徽州府“存留麦,仅够官军粮钞之用,难以别项增加”,否定了从徽州府麦米银内动支的提议。同时还提出了相关的处理建议如下:
查得议单:新安卫官军递年兑运丹徒县漕粮,则运官路费似应取该县,于耗脚内别行议处。其徽州府原无漕粮,似无代丹徒县派办路费之理。若以某卫之官运某县之粮,即派某县之民供某卫之官,事体画一,民情输服,庶运官既蒙优恤之新恩,而本府又免无干之加派矣。
古之贤认为,根据“某卫之官运某县之粮,即派某县之民供某卫之官”的原则,新安卫运官的路费理应由丹徒县承担。显而易见,避免给徽州府带来新的增派是他的出发点。但该建议提交后却“未奉批示”,新安卫运官的路费究竟做何处理尚不可知。(11)泰昌《徽州府赋役全书》记载了新安卫运粮官军行月粮的具体数额,但并未开列运官路费,可见该项费用并未由徽州府承担。
漕军支取三石行粮的标准永乐时即已制定,“永乐十三年题准,官军行粮,浙江、江西、湖广、江南、直隶各总卫所于本处仓关支,南京各卫于兑粮水次州县应解南京仓粮内扣算关支,俱米三石。”(12)王在晋:《通漕类编》卷4《漕运官军粮钞》,《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75册,第327页。据此,新安卫漕军行粮应在“本处仓”即卫所军仓关支。不过,宣德、正统以后,卫所军仓的管理权逐渐转移到地方政府手中(13)卫所军仓管理权的转移问题,参见张金奎:《明代卫所军户研究》,线装书局2005年版,第117—122页。,因此,新安卫漕军行粮改由徽州府关支。虽然明代中期即已出现地方政府扣减,乃至停发漕军行粮的情况,但《呈详议加运官路费缘由》并未显示徽州府存在这样的做法。这份材料还提到,新安卫运官请求增加路费银两是遵循“两浙运官事例”,但目前尚不知此“事例”的具体内容。不过结合此一时期《明实录》中的一些记载,如“曲体运官以禁需索”(14)《明神宗实录》卷107,万历八年十二月丙辰,第2069页。“处运官盘费以杜科扰”(15)《明神宗实录》卷187,万历十五年六月丙子,第3508页。等,我们可以推测,增加运官路费银是为了防止(至少希望可以减少)运官对漕军的需索、科扰。
二、经历协收屯粮
明代中期以后,卫所屯粮征收过程中的拖欠、侵欺等弊端日益严重,朝廷下令各卫经历参与屯粮征收起解,加强监管以求减少卫所武官私使侵费。但这一政策在新安卫落实的过程中,引发了卫经历与管屯指挥等官员之间长达数年的纠纷,《直隶徽州府为申明屯例严并屯粮以济运储以祛宿弊事》(16)按:本节引文凡未出注者均引自此篇。所载即是此事。全文两千多字,而讨论的“屯粮征收缘由”涉及数年、数人,较为复杂。我们依据时间顺序,对这份公文进行梳理,并就其中涉及的问题加以讨论。
万历七年,兵科给事中赵世勋疏论京卫屯粮征收,户部建议“着落经历同掌印官经收起解”,得到皇帝批准,这成为卫所经历参与屯粮征收的权力来源。不过这里强调的是“京卫”,并未提及新安卫等在外卫所。万历九年,南直隶巡按御史王国在名为“屯政久敝恳乞圣明及时整理以定经制以贻永利事”的题本中,论及屯粮征收官员的重要性。(17)《明神宗实录》卷116,万历九年九月戊寅,第2193页。户部认为,“要将经历、吏目同管屯官公同征收起解,免致私使侵费”,实与前述万历七年议复赵世勋题本的意见相同。故此户部拟议:“以后,责令本卫经历同掌印管屯官协收,眼同贮库。或通同侵费,与卫官一体查参。”再次确认卫经历有权与管屯官“协收”,并奉圣旨“依拟行”,得到皇帝批准。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的题本与户部的复议并未限定“京卫”,因此新安卫经历据此获得参与征收屯粮的权力。不过此项“新例”并未立即在新安卫施行,且当时该卫经历一职处于空缺状态(详下)。
万历十二年,新安卫经历诸绍先分别呈文方姓屯田监察御史(文中称“屯院”)、巡抚都御史王元敬,要求协收屯粮。屯院令徽州府通判胡邦彦调查此事。胡在回复公文中指出,新安卫“屯粮向系管屯官征收,并无经历协收事例”,且万历九年新例出台时新安卫经历一职尚缺,执行无从谈起。新安卫武官认为经历协收屯粮势必导致“彼此推捱,事不归一,卫司互相执论矛盾”。因此,对于经历应否参与屯粮征收,胡通判并无定见,故“呈乞或照新例令经历协收,或仍行管屯官照旧征解”。
而屯院的意见则十分明确:不同意经历协收屯粮。屯院认为,虽有经历协收屯粮的新例,但各卫并未施行;更为重要的是,新安卫屯粮“历年无欠”,没有必要“无事纷更”,以“蹈十羊九牧之诮”。因此,屯院要求该卫管屯指挥汪坤“仍照旧专管督征”。
与此同时,巡抚都御史王元敬对于诸绍先呈文也作出批示,要求徽州府查明“该卫屯粮,向系何官征收于何年间?奉何明文?应否该卫经历与屯官公同征收?”该批示经由兵备副使周标下发至徽州府。时任知府高时在递交兵备道的呈文中,承认新例要求经历参与屯粮征收的目的在于“俾其互相催并、稽察侵渔,以裨实政”。诸绍先请求协收屯粮,并无越俎代庖之嫌,不过高知府并不企图变更旧法,他认为新安卫屯粮“递年无拖欠、侵欺之弊”,加上屯院已有批示在先,遂建议仍由管屯指挥照旧管理。这一建议最终被抚院接受。
至此,新安卫经历诸绍先协收屯粮的请求先后被屯院、抚院否决,经历希望与管屯官共同掌理屯粮征解事宜的企图以失败而中止。新安卫屯粮历年无欠,加之新例制定不久,尚无施行先例,是抚、按官员做出上述决定的重要依据。
万历十四年,围绕经历协收屯粮的纷争再起。时任新安卫经历林日辉和仍为管屯指挥的汪坤,围绕经历应否参与屯粮征解,各自呈文兵备副使、屯田监察御史、巡按直隶监察御史、钦差巡按直隶屯田马政监察御史等官员。这些呈文经当事官员批示后,或直接、或经兵备副使牛惟炳批转,一并交徽州知府古之贤处理。不过古知府并未即刻亲自处理,而是将一应“批详文卷牒送本府通判胡查议妥当,具由回报,以凭复议转夺”。
在经过深入调查后,通判胡邦彦向古知府递交了详细的报告,这份报告共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了万历十二年诸绍先与汪坤纷争的经过与结果,上文已经论及。第二部分抄录了新安卫按要求查议此事的回文。回文首先强调该卫额征屯粮、银两向由管屯指挥征收,且“节年屯粮,俱已完足,管屯官并无侵用”,而卫经历从无协收屯粮的先例。接下来,回文针对可能导致钱粮征解不能完足的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
如官舍及民人佃种屯田,恃顽不纳者,许屯官呈府严追;如屯官侵欺,听府卫参呈究治;若屯官违期,听本府拘提屯官的亲家属,同识字比并。如是,则事体归一,而屯政可以考成,钱粮亦得早完,运务可以克济矣。
言下之意,通过加强徽州府对屯政事务的监督,在不需要经历协收屯粮的情况下,管屯指挥足以保证新安卫钱粮早完、运务克济。显而易见,新安卫武官仍不同意经历参与屯粮征解事宜。
报告第三部分是胡通判就新安卫经历应否协收一事给出的建议。胡通判承认经历有权参与卫所屯粮征收,但也存在着实际的困难:
但外[卫]经历为本府属官,实亦该卫首领,位卑权轻,与京卫经历统摄军士、事权隆重者大不相侔。若委之协收屯粮,则彼既不能管摄军人,又何能催攒粮务?异日者运饷不给,彼此推捱,咎将谁妥乎?
胡通判认为,新安卫经历既是外卫经历,同时又是徽州府属官,位卑权轻,与“统摄军士、事权隆重”的京卫经历不可同日而语。由于新安卫经历既不能管摄军人,又不能催攒粮务,协收屯粮很有可能导致运饷不给,进而与管屯官彼此推捱。因此,他建议“该卫管屯官登记发票,按季类报,属之经历”,即经历并不实际参与屯粮征解,而是对管屯官的工作进行稽查。这样做的目的,旨在使“粮务便于责成,而侵渔亦无所容矣”。与两年前没有定见不同,此次通判胡邦彦的态度较为明确。
在此基础上,知府古之贤完成了递交兵备副使的呈文,明确指出了新安卫经历参与屯粮征解可能带来的弊端,为此制定了详细的屯粮征收之法:
行令掌印官,每遇征派之时,将该卫额粮若干,每石派则若干,造完由票,每户一张。又立实征厫经一簿,俱用经历司印信,磨算相同,转发管屯官,方许开征,以杜多派之弊。又设立鸳鸯收票,中用经历司合缝引信,以一半给纳户执照,以一半存屯官案候查盘。其实征簿听纳户亲填,此鸳鸯票听管屯官出给,自一号起至百号止,用尽再印,此以杜侵渔之弊。如无经历司印信收票者,即系旗甲与屯官通用私票,拟以侵欺,仍每月经历司将收过数目揭报本府查考。如此则经历虽不掺夺征收之权,实操稽查之柄。既与新例不悖,又于事体相宜,庶屯政有裨而群喙自息矣。
征收之法的大体内容如下:每遇屯粮征派,由新安卫掌印官填写由票,发予屯户。又立“实征厫经簿”,与由票俱用经历司印信,实征簿所载由经历司核算与由票相同后,转发管屯官,后者才能开征屯粮。由票、实征簿旨在“杜多派之弊”。在具体征收时又设立鸳鸯收票,以防止旗甲与屯官通同作弊、侵渔屯粮。更为重要的是,经历司需要每月将征收屯粮的数目“揭报本府查考”,以此在卫经历稽查的基础上增加府一级的查考,以示隆重。综上可知,古知府的办法是对胡通判建议的补充和完善,真正做到了“经历虽不掺夺征收之权,实操稽查之柄”,这一征收之法也得到巡抚佘立的批准,正式推行。至此,围绕卫经历是否参与屯粮征收的纷争方告结束。
但《直隶徽州府为申明屯例严并屯粮以济运储以祛宿弊事》公文中的一处疑点必须指出,即京卫经历与外卫经历的区别,特别是新安卫经历如何成为徽州府的属官?根据张金奎的研究,明代卫所经历司承袭自元代万户府,其主官经历作为文职流官,职权宽泛,通常被视作武官的幕僚或首领官,明廷对卫所经历的职责颇为看重。为处理繁杂的事务,在经历司之下还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房,房之下又设有若干科。(18)张金奎:《明代卫所经历司制度浅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2期。但京卫、外卫经历之间具体有何区别尚不明晰。按明代外卫指挥使司“设官如京卫”,且“品秩并同”,而京卫指挥使司下设有“经历司,经历,从七品”(19)《明史》卷76《职官五》,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73、1860页。,故作为外卫的新安卫也应设有从七品的经历一员。据弘治《徽州府志》所载,新安卫经历司官员设置如下:“经历司,经历一员,从七品。知事一员,正八品。以上俱文职,今省知事。”(20)弘治《徽州府志》卷4《职制·兵卫官属》,《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21册,上海古籍书店1982年影印本,第49b—50a页。可见新安卫经历司作为卫所的文职机构,确设有从七品经历一员。而明代府一级所设“经历、照磨、检校,受发上下文移,磨勘六房宗卷”(21)《明史》卷75《职官四》,第1849—1850页。,徽州府也设有经历一员,秩正八品。(22)康熙《徽州府志》卷3《秩官志·郡县职官表》,(台湾)成文出版社1975年版,第533页。但该书对明代徽州府经历的记载截止于嘉靖朝,参见卷3《秩官志·郡职官》,第580—581页。
综上可知,府、卫的经历品级不同,且各司其职。由于府、卫经历都是较低级别的职官,史料中留存的记载极少。除了本文论及的诸绍先、林日辉外,管见所及,正统年间,刑部主事李泰“以误失罪囚”(23)《明英宗实录》卷112,正统九年正月甲子,第2252页。贬为新安卫经历,后“客死,公(按:指新安卫千户于聪)具棺殓还其丧”。(24)程敏政:《篁墩文集》卷45《武略将军新安卫千户于公宜人叶氏合葬墓志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95页。对于徽州府知府、通判等官员一再强调的新安卫经历乃徽州府属官,其具体过程如何,更无从知晓。我们或可推测如下:
一方面,卫所经历管理军仓在明中期就有事例,《明英宗实录》多有将经历与仓官并称之例;(25)《明英宗实录》卷35,正统二年十月丁卯,第681页。另一方面,嘉靖四十二年明政府将军屯管理权移交军屯地所在地区的府县行政官员,由此地方官开始直接介入屯地管理事务。(26)《嘉隆新例·户例》,杨一凡、刘海年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2册,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39页。也许,在逐步掌管屯政的过程中,原本参与军仓管理,且本身就是文职官员的新安卫经历,逐渐受到徽州府知府、通判等官员辖制,并最终被后者视为属官。从这个角度看,新安卫经历最终得以协收屯粮,特别是古之贤在“征收之法”中加入府一级的查考,其实质是地方政府进一步加强军屯管理权。
三、粮饷支放
前已提及,江南地区的府县除了发放漕军行月粮外,还需补足卫所军粮的缺额。宣德、正统以后,卫所军仓的管理权逐渐转移到地方政府手中,到了明代后期,就新安卫而言,举凡军人食粮标准的审核、城操官军月粮支领,均由徽州府总司其事。《新安蠹状》所收《呈兵道申明新安卫老幼军人食粮稿》《谕新安卫城操官军支领月粮》两份公文,反映的就是上述情况。
《呈兵道申明新安卫老幼军人食粮稿》收在《新安蠹状》上卷《议稿》,该文的主旨是“申明老幼军人食粮则例,以厘夙弊”。按惯例,新安卫城操官军的粮钞双月一放。粮钞数目造册经院、道批准后,由徽州府“佐官一员,会同卫官亲放”,旨在革除粮钞支领过程中“扣除使费、短少秤头、抵换低银、包放月粮、冒支军饷”等弊端。适值新安卫造送印信领状至府,欲“领支官军孙继先等万历十五年五、六月分粮钞,共计米银一千三十七两八钱三分一厘”。文书至此缺页。但结合缺页后的文字不难推测,缺少的部分应是府佐官等官员发现卫所官军中存在不分老幼、冒领食粮的情况。
古之贤根据《大明会典》的记载,以及自己任职户部、处理放粮事务的实际经验指出,“各处卫所,凡系食粮五斗军人,以为守城、跟官之用;食粮八斗军人,以充运粮、京操之差。”而新安卫却“独树一帜”——旗军不分老幼一律食粮八斗,这令古之贤大惑不解,因为参与守城的实为“老军”。不仅如此,新安卫指挥以“奉文沙汰老幼,俱要壮丁”为名,要求概支月粮八斗。古知府认为,新安卫的这种做法不仅是“虚冒粮饷”,而且最终会导致营伍空虚。因此,他详文兵备道,请求后者调查南直隶各卫所“有无别项事例”,即新安卫此举是否事出有因。并且建议以后选补旗军,新安卫武官必须会同督军厅(即徽州府同知)“勾取精壮正丁,方行顶替”,若确实无合格之人可以顶补,则“姑纪录事例,止许食粮五斗”。兵备副使在批文中指出,新安卫邻近的宣州卫、建阳卫并未有“不分壮弱、一体支粮”的事例,因此新安卫的做法不可取。兵备道认为古知府的建议“甚得省饷实伍之宜”,同意革退陈穿関等二十六名老弱并另选壮丁充补。
《谕新安卫城操官军支领月粮》收入《新安蠹状》下卷《告示》,与《呈兵道申明新安卫老幼军人食粮稿》内容上紧密相连,时间上前后衔接。这篇告示所论为万历十五年五、六月新安卫城操官军月粮支放的具体要求。新安卫官军月粮原先由知府古之贤委托通判胡邦彦放支,但“临期唱散,无册无军”,遂致军粮被管事官旗、势豪之家等克扣侵欺,弊端很多。故此次粮钞支放改由同知于翰“查照凿封,谕期给散”。为了惩前毖后,古知府发布此告示,要求食粮旗军必须亲身关领,不得“雇倩顶替”,且需“将员名、粮数先行造册,呈送本府督军厅查考,听候临卫唱名给散”。对于临期不到者,粮钞扣除还官,不予补发。同时严禁管事官旗、豪户等扣减军粮、预借月粮、冒名支领。
上述两份公文揭示出,在支放新安卫粮饷时,徽州府并非简单地划拨款项,而是派出通判、同知等佐贰官亲身参与,“唱名给散”。不仅如此,知府古之贤还借此机会革除粮饷支放过程中的种种弊端,进而选汰军士,革退老弱。此举实已涉及卫所军政管理的核心,足见明代后期地方官府对于卫所事务介入之深。
结 论
顾诚认为,明代的疆土管理分别隶属于行政系统(即六部—布政司、直隶府州—府、州—县、州)和军事系统(即五军都督府—都司、行都司、直隶卫—卫、直隶都司的守御千户所—千户所)两大系统,并且卫所作为一种“地理单位”管辖不属于行政系统的土地和人口,也管辖着不属于军籍的大量民户,而明清卫所“府县化”的趋势,使这种“地理单位”具有“可转换性”。(27)顾诚:《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卫所制度在清代的变革》,《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毫无疑问,这种“府县化”的“可转换性”在边疆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实土卫所表现得最为明显,而在新安卫这样的内地非实土卫所,与地方官府的关系则要复杂得多。
在明代前期卫所与地方官府的关系上,新安卫是更为活跃的一方。除了发挥维护地方治安的职能,卫所武官们还积极投身于修筑城墙、修建儒学祠庙、构建亭台楼阁、赈济救灾等地方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活跃于地方社会。(28)王浩:《明代卫所与地方社会关系研究——以新安卫和徽州府为例》,《人文论丛》2021年第2辑。相较而言,一些府县官员对于卫所官军虽然有所压制,但史料中几无地方官府插手卫所事务的记载。(29)宣德、正统之际徽州知府崔彦俊的诸多治绩中有如下一条:“新安卫卒素放纵劫夺,即劾奏,加以重罪,自是秋毫无犯。”但这仅是特别的个案,不具有典型意义。参见万历《新修南昌府志》卷19《乡献类·人物传》,《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第5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00页。但是,随着军民词讼约会制度的制定、军仓管理权的转移等一系列政策的调整,明代中期以后,地方州县行政系统文职官员开始逐步介入卫所事务。到了本文讨论的《新安蠹状》所在的万历时代,地方官府对于卫所事务的介入程度可谓极深。
本文重点讨论的《新安蠹状》收录四份与新安卫相关公文,内容涉及新安卫运官路费应否由徽州府承担、新安卫经历应否参与卫所屯粮征解、新安卫城操官军月粮的审计与支放。徽州府本无漕粮,但需要负责新安卫运粮官军的行粮。当新安卫请求自徽州府麦米银内照数加给漕运军官路费银时,徽州知府古之贤详文兵备道明确表示反对。卫所经历应否协收屯粮,本属卫所内部事务,但由于地方官府逐步掌握了卫所军屯的管理权,并将新安卫经历视作徽州府属官,故在此项持续数年的争论中,徽州府始终牵涉其中。古之贤梳理了争论的缘起、经过,在参考通判胡邦彦提出解决办法的基础上,制定“征收之法”,使卫经历正式参与到屯粮征收之中,并借机扩大徽州府的屯政管理权。城操官军月粮核支本来也是卫所内部事务,但由于卫所军仓早归地方官府管辖,故而徽州府顺理成章地肩负起督查之责。古之贤不仅希望革除卫所官军食粮发放过程中的各种弊端,还借机清退老弱,以期“省饷实伍”。
通过解读《新安蠹状》所涉新安卫的相关文书,我们发现,在具体的制度运作中,徽州府几已成为凌驾于新安卫之上的行政管理机构。凡是有关新安卫的事务,不论是南直隶巡抚、巡按批示徽宁兵备道办理,还是徽宁兵备道直接受理,都会交由徽州府查议、处理。隆庆六年,明廷设置徽宁兵备道,其职责为“管辖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安庆五府,广德州,句容等六县,及新安、建阳、宣州、安庆各卫所,隄防江贼矿徒。”(30)万历《大明会典》卷128《兵部十一·督府兵备》,《续修四库全书》第79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01页。一些研究者据此指出,随着徽宁兵备道的设置,在上述地区逐渐形成以“抚/按—兵备道—府/卫—县/所”为主的四级地方行政体系。(31)齐创业、黄忠鑫:《明代安庆、徽州地区兵备道分合演变考论》,《历史地理研究》2020年第2期,第81页。不过从本文的讨论看,徽州府已被视作徽宁兵备道与新安卫之间,且凌驾于新安卫之上的一级行政机构,这比其他内地卫所要早几十年(32)已有研究认为,“在内地……尤其是天启至崇祯年间,府州县逐渐成为凌驾于卫所之上的管理机构。”参见郭红主编:《明代卫所与“民化”:法律·区域》,上海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页。,这对于我们深入认识明代后期卫所与地方官府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