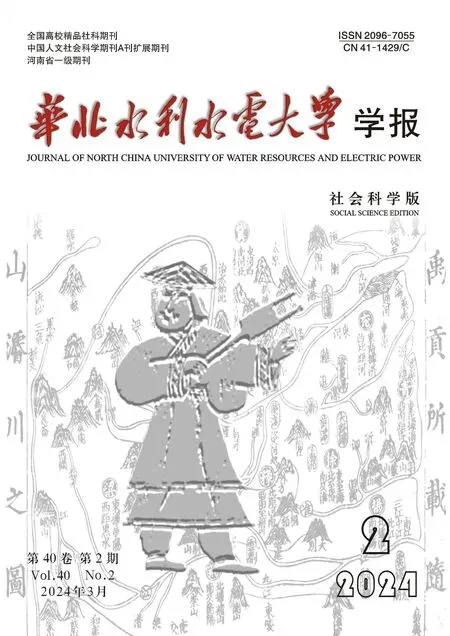2018—2022年明清大运河研究的新进展
孟祥晓,褚伟凡
(河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京杭大运河作为国家的经济命脉,在明清两朝的经济社会及政治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漕运、河工、盐运一起并称清代三大要务,故此,明清政府尤为重视大运河的疏浚与管理。大运河的畅通保障了漕运的安全,维护了王朝的正常运转,并对地方社会产生诸多影响。2014年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17年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两次实地考察大运河,并对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作出重要指示,随之大运河文化保护与传承利用上升为国家战略。大运河地位的提升与国家战略的变化对学术研究产生的影响值得梳理总结。囿于文章篇幅,加以论文刊发周期相对较短,对政策导向反应、跟进较为迅速,本文以该时段内刊发的代表性论文为分析对象,希望通过对近五年明清大运河相关研究的梳理,在社会形势和国家政策导向变化背景下,总结学界研究热点的新转向与薄弱之处,有助于深化对明清大运河的认识,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并对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
一、河道与河工方面
京杭大运河得以行运数百年,与有效的河道河工治理密切相关。明清统治者亦将运河河道河工作为关键政务,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而成为学者长期关注的重要内容。近五年,学者对该内容保持了极大热情,与此相关的成果非常丰富,数量上保持着较高发展态势。
河道方面,裴一璞从运河交通的角度看长芦盐业的发展,他认为便利的运河交通奠定了长芦盐业格局,扩大了长芦盐的营销范围[1]。张可辉对清代京杭运河水马驿站的概况、设置数量及时间进行了考证,认为水马驿站的设置促进了运河沿岸的社会交流与经济发展[2]。姜建国对元明清时期苏州运河进行了考证,包含大运河苏州段、大运河苏州段各条支线、苏州境内的其他水路航线的走向及其变迁过程,为公众展现了完整的苏州水道地图[3]。赵珍分析了嘉庆年间的张家湾改道原因,认为清廷最终放弃张家湾而选择康家沟,反映了清人对水资源的认知程度,以及时人对水利现象的观察能力[4]。另外,赵珍还从河道地貌、水量补给、剥运制度、限制水势等方面探讨了清代北运河的河道治理[5]。袁飞对嘉庆年间的漕运河道进行考察,展现了处在世纪交替之际的嘉庆朝面临的困境[6]。
河工方面,郝宝平、郭昭昭对明代山东运河段的畅通情况进行了分析,指出明廷通过修建戴村坝来保证水源、修建南旺分水枢纽来分配水源及修建水柜水闸来调蓄水源,实现了对运河山东段的有效管理[7]。姜卓对会通河的水系特征、管理体系及过闸的工程技术进行了阐述。从漕船过闸的过程来窥测明王朝的漕运机制,最后得出明王朝漕运废弛的原因[8]。张鹏程、路伟东利用河工图信息,结合相关文献还原了清口地区闸坝设施演替的细节,发现且纠正了以前研究的部分错讹,对官方闸坝命名权与民间闸坝解读权间存在的重大差异进行了分析和阐述[9]。朱年志与胡克诚都从政权角度对运河河工进行分析,均认为在运河的治理实践中伴随着政治斗争,使得运河治理变得更加复杂[10-11]。
河道河工方面的研究主要以运河主体部分为研究对象,也有少量以与运河相关的河流湖泊为研究对象。袁慧探讨了明后期淮扬运河的堤岸制度,认为堤岸制度的变化实际上是运湖关系互相作用的结果,并对淮扬运河沿线的湖泊景观产生了深远影响[12]。高元杰分析了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的微山湖湖口闸水位数据,给出了一百多年间微山湖水位的演变趋势,并且这些数据还可转换为海拔数据,给微山湖其他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数据资料支持[13]。
二、河政方面
大运河的财政问题是近年来学者关注的热点之一。凌滟分析了明万历之后由驱逐堤民到鼓励商民定居于堤上并收取赁基银这种转变的原因。明廷对堤上之房屋及耕地征收赁基银,实际上反映了赁基银从杂课到正税的过程[14]。胡克诚通过分析明代运河中宦官扮演的角色,认为宦官参与大运河的商业税收,是皇权对地方财赋征解过程的直接干预,是明代专制皇权在地方进一步渗透的直接体现[15]。王玉朋对运河道财政职能确立的过程进行了阐述,探讨了运河道的经费来源和支出状况,认为运河道的财政职能并未完全达到最初的设想,但在稽查等方面却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16]。他还研究了山东运河冬挑的来源及冬挑经费问题,认为其经历了起初由政府承担到最后交与盐商承担的演变过程,但是由于盐商无法负担高额的利息,最终导致运河冬挑陷入困境[17]。
除运河财政外,张菊对闸官产生的原因、闸官职责、闸官地位、闸官在漕运与地方社会中的影响进行了阐述[18]。石伟楠研究了明朝通惠河的管理体制,认为晚明时期通惠河郎中的设立,使得通惠河管理体制最终得到完善[19]。孙竟昊、佟远鹏则分析了济宁的河政,认为大运河能对城市发展带来空前的繁荣,但不能实现社会形态的突破[20]。
运河系统中其他河流湖泊的河政问题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主要有凌滟、孟祥晓与王玉朋的3篇论文。凌滟探讨了南旺湖权益分化的演变,认为湖田、湖产、湖水的权益虽然一直在军民、地方政府、藩王之间转换,但所有权一直由明廷控制[21]。孟祥晓分析了明清时期卫河流域的区划变迁,指出区划调整原因是中央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管控,但由于卫河流域的区位特征与其他因素相互交错,使得区划变迁变得更为复杂[22]。王玉朋对运河沿线的湖田开发政策进行了研究,指出明廷为保护运河水源对运河周围湖田开发政策逐渐收紧,但随着明廷的衰落,湖田侵占问题日益突出[23]。
三、漕运与漕粮方面
漕运自古以来被视为国家的生命线,有“得漕者得天下”之说。明清大运河的主要功能是漕运,故而运河漕运研究亦是一大热点。
沈胜群研究了旗丁在漕运过程中的社交网络,指出旗丁在漕运过程中充当了信息传递员角色,但所传播的信息良莠不齐、真假难辨,对沿岸百姓的生活产生了双面影响[24]。他还指出,嘉道年间旗丁帮派之间或者旗丁与百姓之间的矛盾一直无法得到根除,实际上反映了清廷漕运制度中的纰缪[25]。展龙对明代漕运总兵的职责、选任演变趋势、出身、籍贯、任期、离职原因等进行了总结[26]。吴士勇讨论了明代漕运总兵体制化过程,认为陈瑄在此过程中功不可没,但由于继任者的弱势,最后演变为文官任总漕[27]。张程娟分析了明代漕运卫所中藩王护卫军的模式与统辖关系,指出藩王护卫军模式与统辖关系的变化体现了明代皇帝对藩王的态度与政治动向[28]。
漕粮征解方式是漕运中的关键。胡铁球考察了明代折漕规模及漕粮折价原则,发现明代折漕规模呈上升趋势;折价原则有南北之分,南方按时间顺序分为三种模式,北方则流行“按领价折漕”[29]。吴琦、何晨对清代漕粮的“民折官办”进行了探讨,认为“民折官办”从侧面反映出清廷政策制定、实施与变通的特点:守旧中求变,施变中仍旧[30]。李成从民间文献入手分析明代麻城永折漕额的分派问题,指出明代麻城改折的成功,实际上反映了基层势力对地方政府的影响力[31]。阮宝玉研究了明清时期江西、湖广的漕粮运输方式,认为“仪兑”制度的出现,不仅表明了长运法施行后民运与军运的复杂关系,更是认识明清漕运组织转变的重要视角[32]。吴滔对明廷施行长运法后遇到的冻阻问题进行了研究,他发现,明朝后期冻阻已不仅是单纯的自然现象,而且是明代漕运系统中需要面对的制度性难题[33]。杨家毅以漕运仓储为背景分析了通州城的历史地位,认为通州城无论是城市格局还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俱以粮仓为中心,甚至可以说通州城是一个依靠漕运仓储兴起的城市[34]。
在漕运制度及改革方面,徐宝成阐述了清代漕运的剥船官制、剥船船制、剥船管理的利弊及清廷治理措施[35]。徐晓光、刘家佑分析了清代漕运的法律制度,认为清廷漕运法律制度完备,不仅保障了漕运正常运转,而且有利于解决因漕运而引发的社会问题[36]。张程娟从瓜洲闸坝的更替着手,指出其细微变化对明代漕运制度及财政产生的重大影响,同时也反映了不同群体间的利益之争[37]。另外她还分析了明中后期的漕运派兑改革与卫所分帮机制。王宗沐定“分帮派兑”之制,尽管他的后继者在“定派”与“轮兑”之间摇摆不定,但均内含追求定制之精神[38]。郑民德研究了清代漕粮入京监督机制,认为大通桥的监督不仅保障了入京漕粮的质量,还体现了清朝统治者以满制汉的统治策略[39]。王羽坚、王思明对明代漕运中“随船土宜”政策的实施情况进行了考察,虽然“随船土宜”政策在实施之初并没有解决之前的问题,但明廷经过不断调整优化,使得“随船土宜”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繁荣了运河沿线的经济[40]。钮希强指出,嘉道时期腰牌在漕运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清廷漕运之颓势[41]。另外他还从旗丁佥选、帮船修造、漕粮受兑、舵丁管理、漕运耗费等方面介绍了扬州卫三帮漕运档案[42]。
运河系统中其他河流的漕运问题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主要有孟祥晓、张景瑞和高元杰3位学者的5篇论文。孟祥晓从“保漕”的角度,考察了明清卫河地位的变迁与涉漕吏民的群体形象[43-44]。另外,他还从漕运水源管控的角度探讨了其对卫河沿岸水稻种植的影响,认为这种变迁反映了漕运、卫河用水与水稻种植之间的互动关系[45]。张景瑞从“通漕”的角度考察了泇河的开凿过程,发现泇河的开凿除了要解决开凿过程遇到的技术难题,还要处理官僚体系内部治河理念的分歧及地方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46]。高元杰围绕黄运关系,通过研究黄河迁徙对运河漕运造成的影响,指出官员的阻拦和统治者的保守是导致改漕治河思潮一一落空的原因[47]。
四、大运河区域经济与城镇问题
大运河的贯通使得南北交流空前便利,极大促进了运河沿线经济的发展,有些地方甚至依靠运河带来的机遇形成码头或城镇。这些地区依“运”而兴,也随“运”而衰。
大运河对经济贸易的影响。沈胜群对清代京杭运河周围的流动市场形成原因进行分析,发现丁舵利用自身漕运之便随身携带大量的土特产在漕船上进行货物买卖活动,久而久之,漕船发挥了流动市场作用[48]。王羽坚、王思明同样讲到了“随船土宜”,但主要是从农产品的角度出发,对所交流的农产品进行了细分。表面上看,这只是南北农产品的交流,背后则是南北生活习惯、饮食文化、思想观念的碰撞与融合[49]。范金民从物货流通的角度分析15世纪至19世纪苏杭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提出流通税收的升降成为苏杭地区经济发展快慢的重要指标[50]。
运河对沿途城镇码头的影响。陈喜波、贾濛对明清时期张家湾码头的兴衰进行了探析,描绘了它凭借运河经历了从寂静到繁华、但又随着运河改道而回归寂静的历史过程[51]。许哲娜、喻满意从市场空间和社会空间两个角度入手,展现了运河如何影响吴江地区市场的扩展、城镇的发展及群众的信仰[52]。朱年志以夏津县渡口驿漕运仓储和驿站的完备、佛寺林立以及官员文人在大运河留下无数诗作的事实验证往日渡口驿凭借大运河成了繁华之地[53]。郑民德对东光县运河河工河政、商品经济以及东光县的兴起衰落进行了阐述,并对如何保护运河城镇,弘扬运河城镇文化提供了方案[54]。他还对运河城镇盛泽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再次为如何保护运河城镇,弘扬运河城镇文化提供了方案[55]。李德楠、吕德廷将民变、风水、舍利塔、徽商这四个看似不相关的事物进行联系,对万历后期的运河城市临清进行了重新解读[56]。
王银海从城市建设与运河的关系出发,发现无论是城市规模还是基础设施建设都是以运河带来的城市发展为前提,最终揭示出临清的城市建设规律:“官-民”二元共建城市理论[57]。杨梦对运河沧州段沿线的城市空间分布情况进行了探究,分析影响城市空间分布的因素,以期能够为运河沧州段沿线城市的保护与规划提供帮助[58]。刘士林则从运河与诗性文化的角度研究运河城镇,认为江南运河城市既不同于江南城市,亦不同于江南乡村,它凭借运河实现了物质上的丰盈,又凭借江南诗性文化实现了精神上的丰盈[59]。
另外,与运河相连的卫河流域,近年也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孟祥晓从城水空间差异与地方因应入手,对卫河流域的城镇进行了研究。认为城水空间类型的不同导致了河流对城镇的差别影响,决定了地方社会迥异的措施因应,形成了不同地域独特的人文景观[60]。
五、与运河相关的社会群体、个体人物研究
大运河的畅通,不仅促进了沿岸地区的经济发展、城镇的繁荣,更影响着沿岸群众的生活与生计,故沿岸民众的生存状态与生活面貌亦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内容。
关于运丁、纤夫等底层人员的研究。张叶通过对明末清初淮安地区运河徭役变化的研究,指出运河徭役的改革不过是明代一条鞭法的延续[61]。吴欣对纤夫的来源、管理、工食的数量及劳动时间的长短都进行了阐述[62]。吴琦、李想提出清代依漕而食者数量庞大,包括运丁、水手、纤夫、脚夫、泉夫、行商以及官府人员等形形色色的人群。他们依漕而食的同时,也带动了地区的繁荣。但随着运河漕运的衰落,这个庞大群体也成为了严重的社会问题[63]。董慧源从生产领域、消费领域、文化教育领域、娱乐领域和宗教信仰领域分析妇女的日常生活。与之前相比,京杭大运河区域的妇女比之前有了更多的选择,社会对她们的束缚也开始减少,家庭地位开始提高,她们逐渐融入社会的各个方面[64]。丁修真对几名举人经运河北上参加科举途中的所见所闻进行剖析,认为明清时期的举人通过大运河将个人的命运同社会、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65]。龙圣从明清时期京鲁运河盗贼的抢夺种类、形成原因、防治方法及不能根除原因四方面入手,对明清时期京鲁运河的盗贼情况进行了详细描述[66]。孟祥晓对明清时期直鲁豫交界区的动乱进行了研究,提出三省交界处动乱频生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不仅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恶化相关,亦与政区间的各自为政及河流的流动性有关[67]。
关于运河沿线商人方面的研究。郑民德提出徽商依“运”兴起,遍及运河南北,经营范围广阔。他们也积极融入运河区域社会,通过会馆、公益活动、入仕为官等途径提升徽商的影响力,使得徽商成为运河区域一支重要力量[68]。郭琪以江南运河为研究对象,分析明清时期徽商对杭州城的影响,提出明清时期徽商在杭州的商业活动对徽州本土,以及营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清晰的双向互动关系,二者共生共荣、相辅相成[69]。杨泽幸从客商形成的历史背景、客商的音乐参与、客商的音乐空间三方面入手,得出客商的音乐生活实际上是山陕商人的地域认同和徽州商人的“儒商”自我认同[70]。
关于运河区域宗族方面的研究。凌滟对宋礼、白英的立祀过程及宋、白后人的宗族建构过程进行研究,提出宋、白二族实际上是利用国家对运河的重视及官僚内部的矛盾来壮大自己[71]。吴滔分析了“黄溪史氏”走出“役困”的历程。黄溪史氏通过制造和传播《致身录》,对其先祖进行美化,最终将其先祖成功供奉于嘉兴府和苏州府的乡贤祠,从而彻底走出长期阻碍该族发展的困境[72]。郭学信分析了明清时期聊城八大家族的崛起过程、兴盛原因及八大家族的特点。提出明清时期八大家族的兴盛与大运河的畅通及聊城运河区域的政治优势密切相关,亦与八大家族自身的特点相关[73]。
关于个体人物方面的研究。卢海鸣认为,陈瑄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漕运总兵官,整治京杭大运河并且改革漕运制度,是明代京杭大运河复兴的关键性人物[74]。郑民德以崔溥的《漂海录》为中心、胡梦飞以克拉克的《中国旅行记》和权近的《奉使录》为中心研究国外人眼中的大运河文化[75-77],对中外运河的记载进行比较,有利于拓展研究思路,加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六、大运河区域文化方面
大运河的贯通促进了运河区域文化的繁荣,同时在建筑、音乐绘画、信仰、小说行记、饮食服饰、审美观念等方面形成自己独具一格的鲜明特色,因而也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出现了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
在建筑风格方面,刘苏文对运河沿岸清真寺的建筑风格进行分析认为,由于大运河的影响,明清时期运河沿岸的清真寺已经具有中国特色[78]。张雪从运河沿岸道观、佛寺、清真寺以及神庙的独特建筑风格入手,展现了运河文化的包容性[79]。边继琛则从佛教古塔的角度展现了运河沿岸佛教建筑风格的中国化[80]。
在宗教交流方面,来琳玲解释了明代京杭大运河与佛教、伊斯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互动关系[81]。史习隽讲述了明清时期淮扬地区与江南地区的天主教传播[82]。李冰从日本出明使臣策彦周良所著的《入明记》入手,提出运河沿岸佛教具有与世俗社会联系紧密、儒释道三者高度融合等特点[83]。张燕认为,运河沿岸的伊斯兰教呈现出“以儒诠经”的特点,将伊、儒融会贯通,形成中国化的伊斯兰教思想[84]。
在音乐绘画方面,王多指出,京杭大运河的贯通使得佛教音乐、道教音乐与运河沿线的民间音乐相结合[85]。商蕤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阐述了运河沿岸宗教音乐与民间音乐的融合[86]。 姜丽、王静怡发现源自山东西部的戏曲随京杭大运河进行水路传播,使得山东戏曲进入了繁荣期[87]。孙志虹认为,由于京杭大运河的贯通,具有“宫廷风”的天津杨柳青年画传播到了苏沪地区,且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南派”绘画风格[88]。孙璐、康康对扬州博物馆所藏年画进行分析,提出扬州年画与我国传统年画立足农业的形象不同,扬州年画具有精英文化特点[89]。
运河的畅通不仅使中外文化得以交流融合,同时也促使了本土信仰的传播。郑民德认为,运河的畅通使得具有“水神”之称的真武大帝受到推崇。真武大帝庙宇遍及山东运河区域,对运河区域的经济、文化都产生了一定影响[90]。胡梦飞通过梳理金龙四大王信仰的起源、庙宇分布、信仰群众及其影响,发现金龙四大王信仰与漕运及河患密切相关,且具有强烈的官方色彩[91]。他还以高邮地区为中心,探讨了运道对信仰正统化的影响[92]。沈胜群则追溯了清代旗丁崇祀文化的形成过程,发现旗丁祭祀文化既受民间信仰影响,亦受传统文化影响,且清廷一直参与其中,这也表明了清廷希望重塑国家祭祀体系的深意[93]。
在小说行记方面,王珏从小说“白蛇传”的故事出发,对明清时期江南运河两岸城镇的社会生活进行了探究[94]。张美琪对运河沿线小说创作数量、叙述内容及作者居住地进行总结,并对运河小说何以如此集聚进行了分析,提出运河小说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对挖掘丰富的大运河历史文化和弘扬大运河文化都具有重要意义[95]。董宇婷认为,“三言”“二拍”及《金瓶梅》《红楼梦》都与大运河有着紧密的联系,其中描写的众多运河场景是研究及传承运河文化的宝贵财富[96]。徐永斌从文人治生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文人治生促进了明清江南运河区域戏曲小说的发展,同时指出,读者的接受程度和市场的反馈情况又对文人的创作提出了贴近大众和符合市场的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戏曲小说题材和艺术性的变化[97]。张梦琪总结了四十余种清代运河行记,深度挖掘和展示了清代运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以及独具特色的运河文化[98]。郑民德认为,明清小说以城市空间及其政治、商业、社会文化环境来强化小说的艺术感染力与情节吸引力,既是对现实情境的客观描述,又在文学创作与艺术塑造上有所提升,充分体现了小说源于现实、高于现实的艺术特点[99]。他还将明清小说中描述的运河城市临清与淮安进行比较,发现这两座城市既有各自鲜明的特点,亦有共性[100]。顾克勇从明清世情小说角度考察了邸报在运河的传播,认为明清小说家借助运河之便,将邸报写入小说中。同时,世情小说也凭借运河之便得到畅销,这使得邸报内容得以广泛传播[101]。
在饮食服饰方面,胡梦飞详细描述了山东济宁饮食业的发展历程[102]。李芳菲、姚伟钧认为,大运河的贯通为山东运河区域带来了交通上的便利,使全国各地的食材集聚于此,饮食材料得以丰富,促进了餐饮业的兴盛,进一步推动了当地饮食的多元化[103]。付雅雯、梁惠娥、邢乐对清代江南地区服饰的传播者及传播途径进行了汇总,认为传播者主要有负责漕运的旗丁、南来北往的商人和外国旅行者,传播途径主要有贸易传播、人际传播和纸质媒体的传播[104]。
在审美观念上,吴蔚提出江南运河文化的高度繁荣是在优渥的自然条件和市民积极活动双向作用下实现的,文人的审美趣味受大众文化的影响[105]。
在教育方面,舒方涛对山东运河区域的书院进行了梳理,认为良好的区位因素是书院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山东运河区域的书院有着完善的管理体系,且同社会形成了良好的互动。随着运河的断流,区位优势丧失,山东运河区域的书院也随之衰落[106]。
另有一些学者从文化遗产的角度对不同地区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进行了分析,其中有涉及明清大运河的内容,如:于澜对南运河文化带的建设与发展路径进行了研究;郑民德探讨了运河文化带区域的遗产保护与利用;贾兵强对大运河河南段的研究态势进行了总结[107-109]。
七、区域运河生态与环境问题
清代,河工物料经历了柳枝、芦苇、秫秸的转变。高元杰以清代黄运地区为中心,从环境史角度考察河工物料的演变与区域生态植被变化的关系,以及河工物料采办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他认为,河工物料的演变清晰地反映了黄运地区自然植被的变化,这种转变造成了环境问题,导致了百姓的贫困与生态的破坏,也是运河沿线农村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110]。肖启荣通过分析明清时期下河地区的农民生计与淮扬水利工程的维护,探讨农民、政府对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情况,指出政府应顺应农民生计方式与环境的约束,将运东稻田的维护摆在水利维护的首要位置,以征收赋税,维持行政的运转,影响着淮扬运河与淮扬运河地区水利工程的维护[111]。赵珍、苏绕绕分析了北运河杨村段的水环境,发现清廷在进行剥运过程中,无论是剥船置备、起剥定例,还是剥船的生产都要完全适应运河杨村段的水环境[112]。
在其他河流方面,孟祥晓研究了明清时期卫河流域生态与农业状况,发现卫河流域砖窑业的发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城镇防御,促进了沿线城镇经济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田地被破坏、植被被砍伐的现象,对卫河流域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113]。他还对卫河水灾特点与地域环境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指出清代卫河流域水灾的特点与其地域环境条件是一致的,是该区域各种自然要素综合影响的结果[114]。
八、结论与展望
漕运、河工及盐政为明清两朝的国之大事,故而与之关联的明清大运河有关内容一直是学界的关注重点。近年来,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深入人心,以及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提出,使得明清大运河文化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
总体来说,近五年明清大运河的研究呈现出研究下沉、视角多样等特点,但也存在着研究区域不平衡的问题。从搜集到的文献看,2018—2022年相关论文成果共有114篇,2018年至2022年依次发表13、21、21、36、23篇,除2018年稍弱外,其他年份均保持高位运行态势。从内容上看,河工河道13篇、河政10篇、漕运24篇、大运河区域经济与城镇13篇、社会群体与个人17篇(妇女与举人研究各1篇)、大运河区域文化32篇(教育方面1篇)、区域运河生态与环境5篇。可见,在明清大运河的研究中,运河文化与漕运的研究成为最大热点,运河生态环境虽逐渐被重视,但研究成果依然薄弱。对沿河居民生计、社会样态以及商人、妇女、举人等各类与运河相关的特殊群体及其相关面相等内容仍有待深入。
大运河不仅是一条流动的河流,还是一个流动的社会,更是不同区域典型文化交融与互动的场所,其关涉人员、区域社会、文化特点、社会治理等诸多层面,均应予以多层次、多视角研究,唯如此,才能更好地传承与弘扬大运河文化,讲好大运河中国故事,塑造好中华文化丰富立体的典型形象。自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和大运河文化保护与传承利用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出现了大运河研究热潮,但研究对象以京杭大运河本体居多,而对与之相连、共同构成运河网的其他河流湖泊关注程度不够。在本研究所遴选的114篇成果中,关于运河本体的研究有100篇,而对其他相关河流湖泊的研究仅有14篇,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大运河并非仅指一条单线河流,而是由干流和众多支流水系共同组成的水运网,各部分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相关支流不但承担了运河补水的任务,而且是该区域通航运河干流的重要通道。也正因这种高度互依的关系,才保证了漕运的安全和运河系统的正常运转。因而,这些支流和相关区域社会应为大运河研究的题中之义,亟须学者在未来的研究中给予更多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