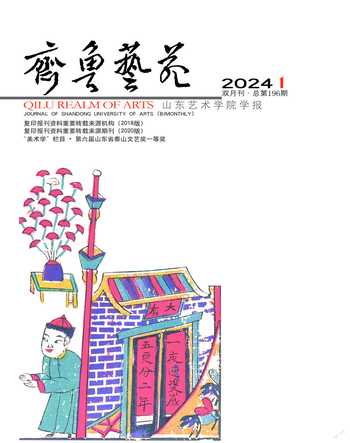瓦尔堡图书馆的缪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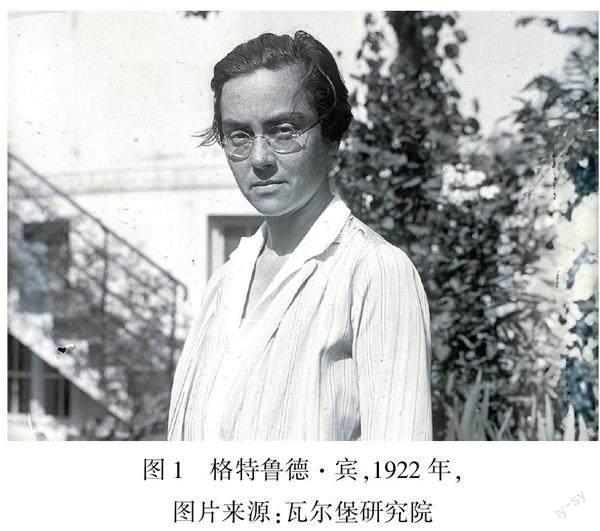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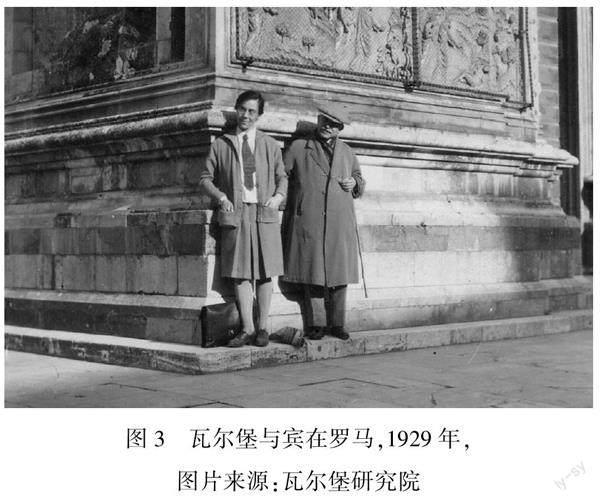
摘 要:西方艺术史在学科的建立以及经典理论的贡献上皆男性学者为主,社会历史因素以及学科内部长期累积的性别偏见使女性艺术史家一直处于边缘位置。在当下的瓦尔堡研究热潮中,格特鲁德·宾被认为是瓦尔堡思想最佳诠释者之一,目前国内尚无文章专门考察这位重要的女性学者。本文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结合瓦尔堡研究院昔日同事的描述尝试勾勒出宾的生平画像;其次,从宾与瓦尔堡的密切合作中分析其研究特点以及对瓦尔堡的影响;最后,结合时代背景考察宾在瓦尔堡图书馆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的女性力量。
关键词:格特鲁德·宾;瓦尔堡方法;艺术史;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J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236(2024)01-0075-09
20世纪初,瓦尔堡图书馆(Kulturwissenschaft Bibliothek Warburg)以先进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和独特的书籍摆放形式声名远扬。图书馆创办者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的文化科学(Kulturwissenschaft)研究范式吸引了许多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如欧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埃德加·温德(Edgar Wind),弗里茨·扎克斯尔(Fritz Saxl),他们都是瓦尔堡学术圈成员。在这个以男性为主导的研究机构中,还有一位特殊的人物——格特鲁德·宾(Getrud Bing)。在瓦尔堡的相关研究中,她被描述为私人秘书或瓦尔堡研究院的负责人,更值得注意的是她是这个学术圈子中唯一的女性学者。E.H.贡布里希把宾看作是瓦尔堡学术圈的“缪斯”,她与扎克斯尔是瓦尔堡图书馆及其思想发展和传播的关键性人物。[1]
自20世纪70年代掀起的瓦尔堡研究热潮中,这位对瓦尔堡图书馆做出巨大贡献的女性的功劳几乎被埋没.笔者认为导致这一现象有如下两个因素:一是宾的留下文字作品不多,亦没有其个人传记;二是瓦尔堡个人魅力的光环遮蔽了围绕在他身边的学者。直到近五年来,随着性别研究和女性主义批判思潮影响的扩大,对瓦尔堡和汉堡学派的考察开始发生转向,学者周围的女性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中。先后有卡罗尔·梅涅(Carole Maigné)、劳拉·塔克(Laura Tack)和伊丽莎白·西尔斯(Elizabeth Sears)从不同角度对宾和瓦尔堡方法及图书馆进行考察。(参见:Elizabeth Sears. Keepers of the Flame: Bing, Solmitz, Klibansky and the Continuity of the Warburgian Tradition[C]//Raymond Klibansky and the Warburg Library Network. Intellectual Peregrinations from Hamburg to London and Montreal.edited by Philippe Despoix and Jilliam Tomm.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18.)此外,賓昔日在瓦尔堡图书馆以及研究院的同事,E.H.贡布里希、D.J.戈登(D.J Gorden)、巴克桑德尔(Michael Baxandall)等,都对这位优秀女性留下深刻印象,在其去世后共同为她撰写了回忆录,为侧面了解宾的提供了一个契机。
本文在上述学者的研究基础上结合宾与同事们之间的书信记录尝试勾勒其生平轨迹,以及对其学术工作做描述性研究。特别是1928—1929年瓦尔堡在意大利期间,在宾的帮助和启发下,促使他将注意力放在对《记忆女神图集》(Bildatlas Monemosyne)的制作。对格特鲁德·宾的考察虽为一孔之见,或可填补瓦尔堡以及学派相关研究的隙缺。
一
关于格特鲁德·宾的早年经历,无论在瓦尔堡研究院的档案记录,还是关于她的回忆录里都相当零散,很少有人了解她在来到瓦尔堡图书馆之前的生活,甚至连宾本人也甚少谈起。因此,笔者只能对宾的青年时期的生活和教育经历做简单的介绍。(从2018年开始,国外学者开始对瓦尔堡周围学者的详细考察,其中包括对格特鲁德·宾的生平介绍:Carole Maigné. Kollege Bing [J].Revue germanique internationale, CNRS e ditions, 2018.)格特鲁德·宾的家族在汉堡当地颇具影响力,在汉堡和巴黎两地之间经营着大量的奢侈品进出口业务。她从小就受到艺术的熏陶,家族中最有名的是她的叔叔齐格弗里德·宾(Siegfried Bing),他率先在巴黎引入日本艺术,是新艺术运动(Art Nouveau)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并于1895年创立了新艺术沙龙(Salon de lart Nouveau)。
优渥的家庭条件未能给格特鲁德·宾带来一帆风顺的教育。1916年,她获得了德国大学入学资格,并于1918年期间在慕尼黑学习哲学、文学和心理学。大战期间,她不得已中断学业,在汉堡的一所男子中学担任代课老师。战争结束后她重返校园,标志着她学术生涯的开始。
1920年宾在汉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这是一所当时新成立不久的研究型大学,聘请了卡西尔和潘诺夫斯基担任哲学系和艺术史系主任。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尤其对犹太裔的青年女性来说,想完成学业最理想选择就是汉堡大学。在当时德国所有的大学中,这所新成立的学府在校女性数量最多。1921年,宾在卡西尔和罗伯特·佩奇(Robert Petsch)的两位导师的指导下,撰写了博士论文《莱辛的必然性概念:一篇关于莱布尼茨和莱辛哲学讨论的文章》(Der Begriff des Notwendigen bei Lessing: ein Beitrag zum Geistesgeschichtlichen Problem Leibniz-Lessing)。宾出版的作品非常少,(宾的文字作品大多以合著的形式或以书籍前言的形式出现:Bing, Gerturd, The library Association Record[M]. London: The Warburg Institute, 1934; Bing, Gerturd, Fritz Saxl. A memoir, in Fritz Saxl (1980—1948): A volume of Memorial Essays from his Friends in England[M]. ed. Donald James Gordon. London: The Warburg Institute, 1957.)这篇博士论文是了解宾的学术研究唯一窗口。在论文附带的简历中,宾的自我介绍透露了她的不幸遭遇:
我,格特鲁德·宾,生于1892年6月7日,是已故商人莫里茨·宾及其已故妻子艾玛·宾(本姓乔纳斯,汉堡人)之女。[2](P7)
选择莱辛作为研究主题对于这位年轻的博士生来说是一项挑战。论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莱布尼茨的哲学理念;第二、三部分着重阐述了莱辛的美学理论和哲学与宗教观念;最后用莱辛的两部戏剧《艾米莉亚·伽落蒂》(Emilia Galotti)(1772)和《智者纳坦》(Nathan der Weise)(1779)来补充她的哲学分析。从论文构框架可以看出她有坚实的哲学研究基础,并对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情有独钟,为她将来成为一名“瓦尔堡式”(Warburgian)学者埋下种子。
宾的博士论文充满了浓郁的理性主义色彩,她认为莱辛的美学思想受到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启发,这在他的美学和宗教哲学观念中都很明显:艺术作品中表现出的特殊性是一面永恒的镜子。[3](P56)这种特殊性在宇宙中的时空位置决定了它的表象,因为艺术作品中的必要的基本形式与一般真理相关,常以历史的形式再现。宾撰写此文的目的不仅考察莱布尼茨对莱辛的影响,更着重于莱辛戏剧中对艺术理论的隐喻,即艺术家是创造性天才,使其作品符合世界上的法度秩序。莱辛戏剧中有一种矛盾的力量,而在视觉艺术中,这些经常被视为矛盾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命运女神”(Fortuna)母题。在研究身为剧作家的莱辛是如何将上述原则转化为实践之前,宾重点关注了他的宗教哲学取向。这是对人类伦理地位的要求,这也是莱辛戏剧作品的一个标志。
1922年,瓦尔堡在克鲁茨林根接受治疗时扎克斯尔成为代理瓦尔堡图书馆馆长,在他的带领下图书馆的学术活动日渐繁荣,开展了一系列合作项目,繁忙的工作让他不堪重负。3月23日他写信给瓦尔堡,表达了要吸纳新成员入馆的愿望。在导师卡西尔的推荐下,30岁的宾被安排到瓦尔堡的图书馆工作,负责图书编目并协助扎克斯尔出版学术刊物以及组织系列讲座。宾与图书馆的联系看似水到渠成,而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这个机会可谓来之不易。20世纪初德国的许多城市反犹主义盛行,犹太裔男性学者在大学中常受到排挤,女性想顺利获得教职几乎是不可能的。宾进入图书馆工作对她的整个人生来说都是决定性时刻,这使她身处20世纪最优秀的艺术史与文化史研究中心。1924年,瓦尔堡回到汉堡,宾直接成为其助手。瓦尔堡对她和扎克斯尔的付出表示感谢。[4](P169)1926年,瓦尔堡图书馆完成从“私人图书馆”到“公共机构”的转型,作为研究型機构正式向社会开放。(根据艾米丽·莱文的考察,瓦尔堡私人图书馆时期,图书馆的日常维护主要依靠妻子玛丽·瓦尔堡,瓦尔堡夫妇经常召集学者夫妇(如古斯塔夫·泡利夫妇)举办小型的讲座进行交流。)[5]瓦尔堡图书馆成立后鲜有女性学者来访,因为她们大多数不得不因为家庭中止研究工作。瓦尔堡对女性做研究有自己的看法,他在日记中写道:“(女性)即使不结婚,她们离开图书馆的几率也很高。”[6](P54)虽然瓦尔堡从未对社会结构中的性别角色发表过意见,但在格特鲁德·宾来到图书馆之前,他从未真正接纳女性进入他的思想世界。
宾对文学与哲学的关注是她今后成为瓦尔堡思想最佳诠释者的前提之一,据D.J.戈登回忆:“在瓦尔堡研究院,那些在图书馆时期就参与建设的朋友里,只有宾真正关心文学。”[7](P20-21)宾一直对莱辛研究着迷,来到图书馆后,扎克斯尔送了她一本相关专著,宾在回信中写道:“非常感谢你送的莱辛作品,它非常有趣,有神学的性质。”(Warburg Institute Archive (以下简称WIA), General Correspondence (GC), Bing to Saxl, 29/08/1922.) 宾一直希望继续自己的研究,可惜图书馆繁忙的工作让她无暇顾及,于是写信给瓦尔堡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我非常希望到冬天时就能把图书馆整理好。这样我可以少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更专注地参与馆内的研究。最近,潘诺夫斯基偶然读到了我的博士论文,他鼓励我继续“拯救”(Rettung)莱辛的艺术理论,他认为,当今的研究对其有误解。(WAI, GC, Bing to Warburg,5/07/1926.)
在回信中,瓦尔堡表示支持并鼓励她订购一些关于莱辛的文献。宾仿佛天生就能理解莱辛的作品中自由与秩序、感性与理性交织的复杂性,展现了她作为艺术史学者应有的理性特质。根据宾的描述,瓦尔堡曾把自己说成是莱辛的学生:他认为莱辛在历史上试图回答的问题,即表现方式的问题,在每一种情况下都结合了语言和图像。[8]这深深影响了瓦尔堡对表现运动与激情的古典图像的思考,在瓦尔堡晚年对《记忆女神图集》的编辑过程中可见一斑。(瓦尔堡晚年与宾一起编辑图集的过程中,自叹一直处于莱辛的影响下:“每当反思我的思想活动的深层次意义的时候,我意识到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有必要对莱辛的论点进行纠正。如果有人在学校向我预告了这一点,我会责备他:在我看来,即使与莱辛相提并论,也似乎是一种亵渎的假设。在随后的几十年中,我在文化科学基础上,对莱辛或温克尔曼的古代奥林匹亚之声学说进行了修正。今天,这项工作尚未完成。” 参见:Warburg, Aby et al. From the Arsenal to the Laboratory [J].West 86th: A Journal of Decorative Arts, Design History, and Material Culture, 2012, 19(1)。) 哲学专业出身的宾,其艺术史修养给贡布里希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回忆录中这样说道:
瓦尔堡将缪斯之母记忆女神(Mnemosyne)题写在图书馆的门楣上。若将格特鲁德·宾比作缪斯女神,她可能会笑,但这种类比能体现一些重要的东西。她与同事并肩而行,知道如何激励他们。虽然她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理性的,但她确实非常有艺术才能,对音乐和许多画家有着深深的热爱,尤其是提香、伦勃朗和委拉斯开支。[9](P11)
宾对瓦尔堡提供的支持不限于一般秘书的辅助性工作,还有智性上和心理上的互补,这一点得到后来许多学者的印证。莱文从卡尔·格奥尔格·海泽(Karl Geory Heise)记叙的回忆以及信件中考察认为,宾强大的理性特质能在瓦尔堡精神状态不稳定时给予必要的帮助。史学家阿纳尔多·莫米里亚诺(Arnaldo Momigliano)將宾对瓦尔堡心理上的影响比喻为“驱魔”,认为她与不可捉摸的心理恶魔保持着适当的距离。[10](P26)宾对瓦尔堡在心理上的支持,以及研究兴趣上的默契在1928—1929年的意大利之行中尤为明显。
二
瓦尔堡这次意大利之行只有宾和一位随从陪伴。瓦尔堡的得力助手不止一位,而他为何选择宾作为这趟旅行唯一的助手?这或许与图书馆的“铁三角”组合有关。从图书馆成立到瓦尔堡去世前,扎克斯尔、宾与瓦尔堡稳定地推动着图书馆的发展。三人以日记(Tagbuch)的形式进行沟通,记录图书馆的日程及学术上的讨论细节,并以《瓦尔堡图书馆工作日志》(Tagebuch der Kulturwissenschaftlichen Bibliothek Warburg)出版。莫米里亚诺将这三人的组合戏称为“研究院的第二个三位一体”(la seconda Trinità del Warburg)。(第一个三位一体是研究院徽志中的“Mundus-Annus-Homo”(宇宙-四季-人), 参见:E.H.Gombrich etc.In Memoriam:Gertrud Bing (1892—1964)[M]. London: The Warburg Institute,1965,P24。)
从1926年开始,瓦尔堡与扎克斯尔的关系变得紧张,《日志》的推进受到阻碍,原本的三人讨论变成瓦尔堡与宾之间的对话,此时宾还充当起瓦尔堡和扎克斯尔之间沟通的纽带。《日志》中瓦尔堡对宾的称呼可以反映他对宾态度的转变,从最初的Frln.Bin到Bingia(Bingiam,和Bingiae),或者(Kollege)Bingio,再到Herr Kollege Bingius,Herr Bingius,和College Dr.Bing 或College Bing,(德语中以e结尾的单词为阳性,Kollege Bing 即(男)同事宾;Herr释义为对男性的称呼先生;College释义为高等学校、大学,这意味着瓦尔堡认可宾在研究上的专业性。名字词尾的转换是瓦尔堡对宾幽默的戏称。)从“女士”到“(男)同事”再到“先生”和“博士”,宾在瓦尔堡眼中逐渐“男性化”,从另一个角度说,则是对其能力的一种认可。此时的瓦尔堡已经打算将自己的研究交到下一代学者的手中,原本他寄希望于扎克斯尔,而此时他认为宾是他最信任的人选。瓦尔堡在日记中写道:“宾能激发出我心底无条件的信任感与尊重。”(GC, Warburg to Saxl,1927,5,20, McEwan, Fritz Saxl, o.c, p.119.)
瓦尔堡这次旅行主要有三个目的:为1929年1月19日在罗马赫兹亚纳的演讲做准备;对乔尔丹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作品进行研究;为《记忆女神图集》的图版编纂收集资料。第一站来到博洛尼亚,他们的目光被解剖剧场(Anatomical theatre of the Archiginnasio)天花板的天文与医学主题装饰雕刻(图4)吸引。该剧院由建筑师安东尼奥·莱万提(Antonio Levanti)设计,天花板和墙壁装饰于1647—1649年完成,中间悬浮着医学之神阿波罗的形象,周围是木刻的占星象征图像。宾对这些装饰雕刻非常感兴趣,她激动地写道:“我要写一本关于意大利天花板装饰雕刻的书。”[11](P64)他们仰望着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中的宇宙,观察人类试图超越自我的种种再现艺术,尝试捕捉动态的“思维空间”(Denkraum)。[12](P260)乔尔达诺·布鲁诺是16世纪重要的思想家,瓦尔堡将他看作欧洲思想的“触角”,他的理论是文字与图像、宇宙学与艺术史结合的化身。瓦尔堡对布鲁诺的兴趣最早可追溯至1910年,直到1928年前后,他开始痴迷于对布鲁诺的研究。(在1928年瓦尔堡写给卡西尔的信中,他表明了自己研究布鲁诺的目的:“这个人(布鲁诺)的重量级地位对我来说越来越重要。他的认识论批判(Erkenntniskritik),隐藏在诸神对抗天魔的象征主义背后,实际上是对纯粹无理的批判(Kritik der reinen Unvernunft),我可以立即将其置于历史背景下,与我的心理学图像材料(《天体乐声》1589)相结合。参见:Johnson, Christopher D.Memory, Metaphor, and Aby Warburgs Atlas of Images[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97.)布鲁诺曾在《驱逐趾高气扬的野兽》对话录中用十二星座寓意旧道德,布鲁诺的理论可以帮助瓦尔堡支撑对文艺复兴时期占星术象征,以及对“纯粹非理性”的认识论和心理学批判。在笔记中,瓦尔堡用隐喻的方式巧妙地表达了他与宾之间的关系:
回想起来,格特鲁德·宾和我的功能就像Y型的占卜棒,一旦“进入地狱” (ad inferos)的冲动加强,或“进入天堂”(raputus in coelum)的画面显现出来,它就会在在普纽玛(Pneuma)中倾斜。[13](P219)
他们一起研读布鲁诺的理论,这根“Y型占卜棒”的组合体现了前所未有的默契。在那不勒斯,他们一起参观了的圣多梅尼科马焦雷教堂(San Domenico maggiore),布鲁诺曾在那里接受教育。[14]宾发现教堂的浮雕代表了黄道十二宫和异教诸神,这是否影响了布鲁诺的占星学信仰是瓦尔堡接下来思考的问题。在卡普亚,他们参观了密特拉神庙(图5)。瓦尔堡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矛盾性”,可以揭示文艺复兴时期的图像中从古代继承下来的极具张力的表现手法。布鲁诺是日心说的倡导者,瓦尔堡和宾意识到这与米特拉神(Mithra)存在一定联系。
米特拉崇拜中血淋淋的公牛祭祀有宇宙学意义,米特拉崇拜和布鲁诺的天空星座都以太阳为中心。布鲁诺反对迷信和占星术,打破了原本的中世纪宇宙学说。瓦尔堡用“世界剧场”(theatrum mundi)这个古老的隐喻来形容布鲁诺的反叛:“乔尔丹诺·布鲁诺把宇宙视为一个剧场,在他引爆星体之后,引导员才指示位置。”[15](P197)这句话的意思是布鲁诺的理论挑战了古老的地心说。是什么让布鲁诺突破传统的藩篱?宾在关键时刻给出了非常肯定的答案——Synderesis(良知)。这个重要的哲学概念是宾为《驱逐趾高气扬的野兽》做的注释:“Sinteresis/ siehe/ ed. Gentile / II, p.13. n.2.(良知/请参见/非犹太的/II, 第13页)。”[16](P201)象征“智慧之光”的朱比特“被无常的命运束缚”,在“良知”的驱使下,决心清除天界无知、迷信、贪婪和类似的恶习,重建道德。瓦尔堡对布鲁诺的痴迷是一种精神上的确认,他相信布鲁诺描绘的宇宙图景,夯实了他对文艺复兴时期占星术象征主义以及心理学上的认识。1929年7月回到汉堡后,瓦尔堡打算开展一系列布鲁诺的讲座并补充说道,若没有格特鲁德·宾的帮助,他永远不可能继续“文化学科式的类型图集”(kulturwissenschaftliche Typenbild)的研究。
宾关注布鲁诺的理论不单是为了协助瓦尔堡,还是她本人对莱辛的延伸考察。她把人类与命运的斗争作为一种伦理宗教现象来对待,通过与瓦尔堡的合作,星辰宇宙与命运的关系对她来说逐渐清晰。虽然长期担任瓦尔堡的私人秘书,但她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学术研究,虽然未能出版个人成果,但她把自己对人类与命运的关注投射在与瓦尔堡一起编辑的《记忆女神图集》之中。这次意大利之行使宾更接近瓦尔堡的灵感之源,两人之间的思想联系更紧密。如果说扎克斯尔帮助瓦尔堡打理图书馆等外部事务,宾则具有一种从内部(von innen heraus)理解瓦尔堡理念的能力。[17]可以说,在宾的帮助下,瓦尔堡重新找到了在佛罗伦萨时的创造动力。
“助手”宾发挥的能量远远超过这个称谓给人留下的一般印象。她在瓦尔堡学者圈子里中一直扮演着“服务者”的角色,无形之中限制了她的个人学术追求,反映出世纪之交的欧洲女性知识分子的困境。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女性追求事业困难重重,宾依然坚持接受教育并在瓦尔堡图书馆工作,这种勇气值得赞许和钦佩。这与恩里克塔·弗兰克福特(Enriqueta Frankfort)对宾的简要描述相一致:
格特鲁德·宾身型娇小,皮肤黝黑,戴着一副眼镜,表情严肃,但笑起来却很亲切,她的目标、勇气和人性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某种程度上,格特鲁德·宾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一个以男性为主的世界中找到了一个基点,在那里她可以表达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培养自己的智性。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个阻碍她自身发展的地方,因为她主要是以男性学者同事的助手的角色占据这个位置。[18](P17)
或许,在不了解当时的社会环境与她的教育背景的情况下,冒然认为她只是瓦尔堡图书馆中一个默默无闻的助理,这种看法未免有失偏颇,而且还剥夺了宾为自己的事业而拼搏所应得的尊重。
三
要客观完整地勾勒出宾的形象,不仅要参照同事们对她的记忆,还要从瓦尔堡的研究中捕捉宾留下的痕迹。在意大利瓦尔堡和宾的目光不仅仰望宇宙星辰,还关照微观个体,确切地说,是关注个体在变幻的宇宙中所持的生存立场。他们以马奈的作品《草地上的午餐》(图6)为切入点,草地上斜躺的人物让人想起马安东尼奥·雷蒙迪(Marcanonio Raimondi)的铜版画《帕里斯的裁决》(The Judgement of Paris)(图7)中右侧的古代河神形象,其灵感来源于对古代石棺的描绘。雷蒙迪作品中的河神对背景中的奥林匹克诸神作出了恐惧和热情的反应。瓦尔堡将此与他当时正在研究的两极性(狂躁—抑郁)的联系起来。(瓦尔堡在1929年3月20日写道:“在非休息状态下的能量倒置:河神在崇拜中无法站立……休息的人不想要它:懒惰的人,怠惰(Acedia)的宣泄。”参见:Johnson, Christopher D. Memory, Metaphor, and Aby Warburgs Atlas of Images[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2,P21.)瓦爾堡在同一时期写的关于“行动生活”和“沉思生活”之间关系,也是在对马奈的研究中产生的:
有时在我看来,似乎在我作为一个心理历史学家的角色中,我试图从自传式反射中的形象中找出西方文明的精神分裂:一边是狂喜的“宁芙”(躁狂),一边是哀伤的“河神”(忧郁)。高敏感的人将试图在这两极之间找到一种风格,使他们能够积极参与到生活中对比的老游戏:行动生活和沉思生活。[19](P135)
这段话体现了瓦尔堡对个体在宇宙中的地位的典型看法:在一个似乎从迷信和压迫中解放出来的宇宙中,人在抑郁和狂躁之间游走。因此,他认为西方世界的命运是一种精神分裂,在两种生活中摆荡。这种“极性”(polarity)反映在《记忆女神图集》图版48中(图8),它的标题是:“命运女神,人类自我解放的阐释象征”(Fortuna, Auseinandersetzungs symbol des sich befreienden Menschen)。根据档案记载,这幅图版由瓦尔堡和宾共同完成。
图版48从左到右是命运女神的三种拟人化形象:(a)为带轮盘的形象、(b)为航海形象、(c)手持丰饶角。像宁芙一样,命运女神是运动的化身。在文艺复兴时期对命运女神形象的再现中,她在海上漫步,而风则自由地挥舞着她解开的帆,有时她像桅杆一样带着帆,作为风之女神或海之女王,她最终仍然难以捉摸。她脚踩天球试图保持平衡,这种盲目的命运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以看似武断的方式有时候会带来繁荣,有时则是灾难。图版展示了在文艺复兴晚期,改变突发事件的力量仍掌控在命运女神的手中。
瓦爾堡痴迷于文艺复兴时期“仙女”(Nympha)主题的研究 ,对“女性”的描绘进入了他的思想中心,这其中一部分原因来自宾的影响。她熟稔瓦尔堡手稿,对他语言的细致解读让她成为瓦尔堡写作风格和语言运用的研究者。在瓦尔堡去世后,宾第一个成就是1932年整理并出版了《阿比·瓦尔堡丛集》(Aby Warburg Gesammelte Schriften),并为其撰写了前言和索引。此外,宾很早就开始策划撰写一本瓦尔堡传记,可惜的是这项任务直到她去世前都未能完成,写好的原稿也全部销毁,撰写的任务交给了贡布里希。
随后,宾还面对日益严重的反犹太主义。随着1933年国家社会主义者的崛起,这位女性在图书馆的搬迁中倾尽全力,将自己与图书馆的命运紧紧绑在一起。1933年12月,在这扎克斯尔和宾的组织下,赫尔米亚号(Hermia)轮船满载瓦尔堡图书馆的六万册图书驶向伦敦,宾的命运似乎在二战后才逐渐稳定下来。在这动荡的岁月里,命运女神继续在思想领域指引着她。宾对个人与命运抗争的方式非常着迷,并试图在可能出现的非理性力量的旋涡中站稳脚跟。1944年,二战即将结束时,瓦尔堡图书馆更名为伦敦大学的瓦尔堡研究院,宾继续担任她的助理院长直至1955年。1946年,她成为英国公民。院长扎克斯尔1948年去世后,接替他的是亨利·法兰克福,不幸的是他于1954年意外离世,宾于1955年成为研究院的负责人以及伦敦大学古典传统史教授,并于1959年退休。宾的命运现在似乎紧紧地与英国绑定在一起了,但她对祖国的思念却从未消失。
来到英国之后,宾除了本职工作以外,在战争期间还在协助来自德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寻求庇护者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她的帮助下,大量的学者在英国和美国找到了学术职位。同时,宾还承担起与流散到世界各地的瓦尔堡学者的联络工作,并持续关注着图书馆未完成的出版项目,如潘诺夫斯基、扎克斯尔和克里班斯基合著的《土星与忧郁》。除了出色的组织才能,宾的参与感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巴克桑德尔回忆道:“她完全专注于与之交谈的人。与她一对一交谈的人,无不欣赏她这种特别关注的感觉。”[20](P16)作为图书馆中第一位女性学者,宾给后来的弗朗西斯·耶茨(FrancesYates)留下深刻印象,在《记忆的艺术》(The Art of Memory)的序言中耶茨说到:
现在,《记忆的艺术》终于完成了,对已故格特鲁德·宾的记忆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在前期,她阅读并谈论我的草稿,持续关注我的进展如何,时而鼓励,时而劝诫,以她强烈的兴趣和独到的见解不断激励我。她觉得如精神图像、图像的激活、通过形象把握现实这些问题——在记忆艺术史上一直存在的问题——与阿比·瓦尔堡(我是通过她才知道的)所关注的问题非常接近。我永远无法得知这本书是否如她所期待那样……我把这本书献给对她的记忆,对她的友谊深表感激。”[21](xiv)
耶茨简短的几句话概括了格特鲁德·宾在工作中强烈的“使命感”,她自始至终全身心地投入到发扬瓦尔堡的思想遗产的事业中,密切关注后辈的进步,并亲自参与他们的研究项目。1964年,格特鲁德·宾突发疾病于7月3日去世。“瓦尔堡,我们的幽灵:在内心某处,难以把握,不为人知。” [22](P14)迪迪-于贝尔曼(Georges Didi-Huberman)形容瓦尔堡的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宾。宾的确是一个幽灵,它至今还在随着对瓦尔堡遗产的研究游荡,这个幽灵不时会来纠缠我们,但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似乎很难说清。但可以明确的事,她以“自我牺牲”的方式为图书馆全心全意的付出,而在今天对瓦尔堡遗产的研究中她却像游弋的幽灵。恰恰是这种如“幽灵”般的神秘,似乎成了格特鲁德·宾作为女性学者在图书馆生存的动力。
对许多人来说,格特鲁德·宾既是瓦尔堡的“缪斯”,也是“现代的宁芙”,亦是用灵感与友谊使人们行动起来的动态力量的化身。连接过去、未来和现代的河流已汇成深海,只有命运女神能以高超的技巧驾驭它。宾以她自己独有的方式在图像阐释的空间中航行。无论如何,宾是一个多面手。作为一名哲学家和文学家,她是瓦尔堡图书馆“铁三角”之一,在研究上给出关键性意见的女性学者。作为一个流亡的犹太裔学者,她不甘心自己的苦难命运,人们可以把她的生活解读为与命运的斗争,在美丽、真实,尤其是善中追寻自由。
参考文献:
[1]Michael Baxandall. Is Durability Itself Not Also a Moral Quality? [J].Common Knowledge, 2012,18 (1).
[2][3][11]Tack, Laura. Fortune of Gertrud Bing(1892—1964) [M]. Leuven-Paris-Bristol: Peetres, 2020.
[4]McEwan, Dorothea. Fritz Sax, Eine Biografie [M]. Wien-Kln-Weimar: Bhlau Verlag,2012.
[5][6]Levine, Emily J. PanDora, or Erwin and Dora Panofsky and the Private History of Ideas [J].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2011 , 83(1).
[7][9][10][18][20]Gordon, Donald James,Ernst Gombrich etc. In Memoriam: Getrud Bing (1892—1964) [M]. London: The Warburg Institute, 1965.
[8]Warburg, Aby, Christopher D. Johnson, and Claudia Wedepohl. From the Arsenal to the Laboratory [J]. West 86th: A Journal of Decorative Arts, Design History, and Material Culture 19, 2012,(1).
[12][英]E. H.贡布里希.瓦尔堡思想传记[M].李本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13][15][16]Johnson, Christopher D. Memory, Metaphor, and Aby Warburgs Atlas of Images[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2.
[14]Warburg, Aby. Giordano Bruno and the Chapel of Andrea Carafa di Santa Severina in San Domenico Maggiore [C]// Maurizio Ghelardi and Giovanna Targia. Philosphy and Iconology (1-2008). Napoli:Bibliopolis, 2010.
[17]Enrst Gombrich. Gertrud Bing zum Gedenken[M], London:The Warburg Institute, 1962.
[19]Ruprecht, Lucia. Gestural Imaginaries: Dance and Cultural Theor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9.
[21]Yeats Frances A. The Art of Memory[M].London:APK Paperbacks, 1966.
[22]Didi-Huberman. The Surviving Image Phantoms of Time and Time of Phantoms Aby Warburgs History of Art[M].Translate by Harvey Mendelsohn. Pennsylvania: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17.
(責任编辑:刘德卿)
收稿日期:2023-05-25
作者简介:李晨雪,女,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美术史。
doi:10.3969/j.issn.1002-2236.2024.0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