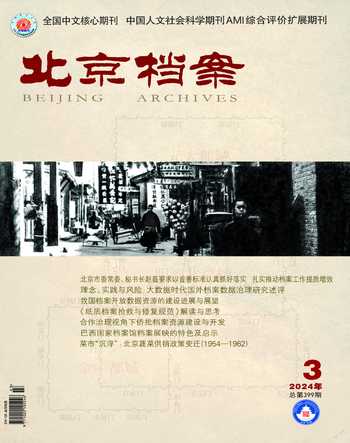菜市“沉浮”:北京蔬菜供销政策变迁(1954—1962)
王子彧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北京市人口数量不断增多,北京蔬菜供销存在供应不足、季节性短缺、某一蔬菜品种滞销现象等问题。为解决蔬菜供销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响应“为首都服务”的口号,北京市委市政府对于蔬菜供销政策不断进行改革,从“收购包销”、垄断蔬菜批发到“统购统销”、改造个体菜贩。个体菜贩的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国家逐渐将蔬菜业纳入国家计划经济轨道,而与此同时,蔬菜自由市场却屡禁不止。
关键词:“统购统销”供销合作社 个体菜贩 场外交易
Absrtact: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th the recovery and develop? ment of the economy and the increasing popula? tion of Beijing, the supply and marketing of vege? tables in Beijing suffered from insufficient sup? ply, seasonal shortages, and poor sales of a cer? tain type of vegetables. In order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and respond to the slogan of "serving the capital", the Beijing Municipal Party Commit? tee and Municipal Government reformed the poli? cy of vegetable supply and marketing continuous? ly such as "acquisition and underwriting", state monopoly of vegetables wholesale, "unified pur? chasing and marketing", and transforming vegeta? bles vendors. The survival space of self- em? ployed vendors has been squeezed, and the state has gradually brought the vegetables indus? try into the orbit of state-planned economy. Al? though the free market of vegetables sales has been repeatedly banned, it could not be prohibit? ed completely.
Keywords:State monopoly of purchasing and marketing; Supply and marketing coopera? tive; Self- employed vegetables vendor; Overthe-counter dealing
“好马赶不上青菜行”,这句话是近代北京菜贩群体口口相传的一句行话,充分反映了瞬息万变的蔬菜价格。民国时期的北京蔬菜行业由牙行垄断,菜市由经理人(牙人)所掌握,每个菜行大约雇用二三十人,分别担任“拿秤的”“写账先生”“二掌柜”、伙计等角色。每天早上四点菜市开市,来自京郊各地的蔬菜被运抵菜市后,菜行伙计协助农民将蔬菜摆列代售,但农民并不直接与零售商、小贩对接,而由居间牙人居间仲卖,成交后由买方支付牙人佣金(约20%),再由坐商或小贩售出。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蔬菜业仍由牙行控制,居民日均蔬菜量只有三两,菜价波动幅度较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人口迎来了高速增长,从解放前夕的200万到1959年的706万人,增长了253%。为了改善国民营养,增强民众体质,《人民日报》多次发文强调补充蔬菜的摄入量。[1-2]在此背景之下,人民对蔬菜的需求量急剧增加,与此同时,蔬菜供应却严重不足,供求矛盾突出。“1949年北京郊區菜田仅占3.2万亩,按复种面积计算大约有6.5万亩,年产量约5万吨,平均每人每天吃菜150克左右”[3],冬季产销淡季之时,“不少菜店无菜可供,或只有无人问津的蔫土豆、烂葱头摆在货架上”[4]。面对物资短缺和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如何在城市居民的日常饮食中确保蔬菜的供应变得尤为重要。北京市基于蔬菜的供销环节,进行了诸多尝试。1951年11月5日,北京市彻底改革蔬菜市场中的牙贴封建制度,逮捕了5名菜行恶霸。[5]1951年后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以下简称“总社”)在天桥、广安门、阜成门等地设立菜站,经营蔬菜的批发业务。以托售成交为主,自营为辅。[6]政府开始参与到蔬菜经营业务当中,同时由于首都人口的增加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蔬菜消费量随之增长,市场交易日趋扩大,原有菜市逐渐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民需求。于是政府对原有菜市进行改造,同时在人流量大的城区、乡镇新增菜市,设立菜市商业局,保障公平交易。
1953年北京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针对私营商业的调查报告中提出,“有些对国计民生关系较大的商品,如小五金、牛羊肉、干鲜果、鱼、鸭、蔬菜等,国营合作社商业应逐步扩大经营品种,稳定市场价格”[7]。为了满足市民生活需要,为首都服务,“1953年总社建立了蔬菜经理部(1955年4月29日改组为北京市菜蔬公司),统一管理城郊蔬菜批发市场”[8],逐步将蔬菜业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但此时蔬菜批发业务仍主要由私商经营,多种成分并存,蔬菜市场呈现自由经营、多渠道购销的景象。
一、1954—1956:收购包销,垄断蔬菜批发
(一)合作社逐渐接管批发业务
1953年冬,由于部分政府机关部门,如炮校、铁路食堂、清华大学等从丰台区小井、靛厂等村批购白菜数百万斤,价格有300元、450元、500元、600元不等。[9]农民从中获取了一笔不菲的收入,一些农民产生了等价出售的心理,导致1954年春天出现了白菜滞销的状况。这一状况出现以后,总社试图以210元至235元的价格收购滞销的白菜,然而仍有政府部门以高价收购白菜,结果反而招致了农民对于合作社的不满。蔬菜的高价收购引发了市场乱象,故总社向北京市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请示,“由供销合作社代购或介绍购买蔬菜,禁止各机关、部门、单位深入原产地直接购菜”[10]。
1954年1月21日,北京市委提出,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重点在菜田区,“郊区的农业生产应以生产蔬菜为中心”[11]。于是,自1954年春季开始推广“产销结合合同制”,蔬菜产销逐步走上计划化,将国营农场、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国营蔬菜生产机构与供销合作社等国营销售组织相结合,由供销社收购包销,实际上使供销合作社垄断了蔬菜的批发渠道。如北京市海淀区东冉村远大合作社与5个生产大队签订包工包产合同,并与海淀区供销合作社签订产、供、销结合合同,保证全年供应首都蔬菜814万斤。[12]自8月27日起,总社统一掌握了北京城郊18个蔬菜批发市场之后,市场上的批发业务即由供销合作社完全接管。
(二)私营菜商开始社会主义改造
产销合同的签订,节省了人力、畜力,使得农民可以安心生产,也保证了蔬菜价格在一定时期内的稳定,同时促成了对私营菜商的社会主义改造。“以三大菜市为例,3月份供销合作社的经营比重只占市场总成交量的34.5%,7月份就扩大到64.5%,22家私营菜行已相继由供销社接替了17家。”[13]对私营菜行的改造迅速推进,自1954年8月底开始,菜市场已由合作社接管,由供销合作社负责介绍、对接产销双方,同时积极扩展零售阵地,“八月份合作社所经营的蔬菜每天平均为15万余斤,零售公司每日平均7万余斤”[14]。
这一政策限制了商贩的货源,对私营菜贩的经营造成了压力,个体菜商数量迅速减少,据调查显示,“在行业中营业额下降最大,同时户数减少最多,亦即为目前营业严重困难的有:煤炭、柴薪、蔬菜等9种类型,共计7716户”[15]。蔬菜供应者大大减少,“北京市原有菜商9700户,领取购菜证者6006户,实际上市者4000户左右”[16]。与此同时,供销合作社接管批发业务后,由于蔬菜货源的单一,一些专以卖菜为生的菜商出现了经营困难、收入缩减的状况,如“前门区菜贩刘国栋,家中六口人,过去每天卖菜300~400斤,现在只能卖100、200斤,少1万多元,生活困难。宣武区菜贩时应尚过去每天卖200、300斤,现在只能卖到120、30斤”[17]。
数量众多的私营菜贩应该如何解决生计问题呢?以北京东郊区为例,共分为三种:第一种,家在农村有土地能维持家庭生活的(19户,20人),有运输工具能转为运输业的(9户,10人),有其他生活来源的(2户,3人),动员缴销营业照章,去往其他行业。第二种,有劳动能力、家庭生活较困难、历史上无政治问题、有就业证件的41户48人,由国营企业或供销合作社予以吸收安置。第三种,年老体衰或家庭负担较重,无就业证件的60户63人,转为固定或流动零售。[18]一些私营菜贩被供销社菜蔬经理部门所接收,但他们的思想并没有得到完全的改造,“有些是旧社会的兵痞流氓,有些人的来历还不清楚;旧思想旧作风相当浓厚,不少人缺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对工作偷懒耍滑磨洋工,个别人员竟变相勒索农民”。“他们旧的经营作风尚未完全改变,对农民蔬菜压级压价,农民对他们十分不满。”[19]在货源分配上,遇到某些季节性的蔬菜积压滞销时,采取硬性搭配的方式强迫居民购买,“如1955年9月海淀菜站大葱供不应求,白菜过剩,菜站于是规定要买20斤大葱得买2000斤白菜”[20]。
由于1954年冬季蔬菜供应不足,“蔬菜摊商每人仅能领到几十斤,最多百余斤,因此有些摊商因经营蔬菜少不能维持生活”[21],于是1954年末又进一步调整了对私营菜贩的管理政策,规定“个体农民在零售方面可以自销,但批发交易仍须集中到国家市场成交”;“私营零售菜商、菜贩及市民仍可到市场采购,由合作社介绍向售菜农民代购”[22],“对不能维持正常生活的菜贩,由管理处介绍给供销合作社菜站赊銷,尽量满足其经营数量,给予畅销蔬菜”[23],使个体菜贩一定程度上维持并稍有利润,减轻了生活的压力。一些家庭陷入贫困的菜贩,与民政部门对接予以救济。
(三)“收购包销”后的合作社
总社蔬菜经理部承担了全市蔬菜统一经营的任务,同时在一些乡镇建立了蔬菜收购供应站,由菜站供应给附近的机关团体、学校的饮食单位及居民。市场上的蔬菜批发业务被供销合作社接管之后,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第一,蔬菜的质量普遍下降。“如大白菜青梆大叶不修理,大葱、土豆泥土过多等等,还不如过去自由市场整修得新鲜、干净。”[24]个体农民和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均忙于追求蔬菜的数量而忽视了质量,“海淀区四季青蔬菜生产合作社送到广安门菜站的400多斤黄瓜中有四分之一是老黄瓜”[25]。第二,蔬菜的伤耗增大,损失惨重。自统一收购和分配后,由于增加过秤和保存时间及蔬菜之间的积压,因而增加了蔬菜的损耗率。“由广州运来的80万斤白菜,因为南北气候相差很多,又加包装不当,运到后没有及时采取防冻措施,结果全部受冻,有30万斤外冻里烂,几乎变成汤了。”[26]第三,为了解决蔬菜供销中大路菜数量过多而需求不足,细菜数量较少而需求过剩的状况,总社采取了“搭配供应办法”,引起了消费者的不满。第四,由于某些菜蔬滞销,供销合作社亏损严重。“如天桥菜站十月十日积压油菜2万斤,以250元收进,以100元售出;阜成门菜站十月六日剩市小白菜1万多斤,收价180元至200元,结果以10元1斤卖出去。”[27]第五,蔬菜售卖网点分布不平衡,部分地区购菜难,如首都东郊区酒仙桥一带人头攒动,然而“这里只有一个合作社分销处,买点菜、肉,也得挤进挤出排半天队”[28]。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北京市菜蔬公司采取了“优质优价”的原则,对于收购来的蔬菜进行挑选整理,分等级定价。贯彻北京市“从便利市民出发,并且参照各行业的服务对象、营业情况和分布状况,分别采取增设、撤点以及合并或集中等办法”[29]调整商业网点的相关指示,重新调整蔬菜的经营区域,在郊区等供应短缺的地方兴建中心商店及综合性商场。如在酒仙桥一带增设商场,将粮食、蔬菜、肉类及其他副食品的经营都纳入其中,“市菜蔬公司设在这里的供应组出售50多种新鲜菜,价钱跟城里一样”[30]。一些乡镇的中心商店还采取了“送货上门”的服务,这大大便利了农民的生活,满足了农民的生产生活需要。“南苑区鹿圈乡许多农民,看到这个乡中心商店派出的流动售货车带着肉、菜、小百货等来了,都很高兴,他们说:‘过去买点肉要到南苑镇,想吃点细菜也没有,这回可方便了,也不会耽误生产了。”[31]
二、1957—1962:“统购统销”,改造个体菜贩
(一)“统购统销”,产销挂钩
1956年农业合作化完成后,京郊国营农场、农业生产合作社普遍与市菜蔬公司及其所属菜站签订“收购包销”合同。[32]合同中对蔬菜的品种、上市时间、数量以及价格都做出了规定,合同内的蔬菜将由北京市菜蔬公司统一收购进行销售,农业生产合作社可以自行销售剩余的蔬菜。然而1957年,随着北京市政府将蔬菜纳入二类物资,限制农业社的自销,将蔬菜纳入了“统购统销”的体制,即对蔬菜全部实行统一收购,集中组织调拨,收购价和零售价由国家统一制定。1958年随着人民公社的建立和集贸市场的取消,郊区生产的蔬菜改为全部由国营菜蔬公司及菜站收购。
“统购统销”政策之下,产销直接挂钩的政策造成了各区之间蔬菜品种、数量的不均衡,“1961年各区各月供应的数量仍然不够平衡,各中心店之间每天的不平衡情况则更为突出。1961年4—10月合计,城近郊7个区平均每人每天供应量1.07斤,其中:朝阳、丰台超过平均供应量,其他5个区没有达到。朝阳最多,为1.17斤,海淀最少,为1.02斤,相差0.15斤”[33]。从品种上看,不平衡情况也很突出,“5月水萝卜上市量,宣武高达383万斤,崇文127万斤,东城只有14万斤,西城根本见不到”[34]。此外,在实行产销挂钩后,一些生产队之前供应全市的品种,现在固定于一个中心店分菜站挂钩,造成人为的积压、脱销。“如海淀区玉泉大队生产的毛豆、白藕和茭白,全部供应展览路中心店,销不出去,而其他地区吃不到。”[35]不同类型的菜市品種各不相同,“地处繁华闹市的大型菜市场以供应细菜为主,上市品类多达30、40种;位于交通要冲、流动顾客较多的中型菜市场或较大的蔬菜门店细菜与大路菜并重,应市品类20、30种;以地段居民为供应对象的中小型门店,一般只提供5~10种大路菜”[36]。蔬菜销售设备也不尽相同,大型菜市场和综合性副食品商店多配备坡型商品陈列架;中小型门店,设有菜床子并采用售货车流动服务。
“统购统销”政策之下,为了维持蔬菜价格的稳定,北京市实行蔬菜政策性价格补贴,然而自1957年政策颁布之后,年年亏损,“1957年,平均每斤蔬菜亏损为0.0035元”[37]。
(二)公私合营,联购分销
1955年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合作化运动作出重要指示之后,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的高潮迅速到来。在公私合营的方针指引下,北京市对于京郊和城镇的个体菜贩制定了不同的针对性举措,“郊区农村的小商小贩,绝大多数是独立劳动者,由供销合作社采取经销、代销和组织合作小组等办法,逐步地把他们纳入合作社商业网范围之内”;“城镇的摊贩数量很大,情况复杂,除委托经销、代销外,应选择典型试用联购分销等办法。”[38]在改造之前,北京人民的副食品“约40%是由私营猪肉业、牛羊肉业、鸡鸭鱼蛋业、油盐酱醋业和蔬菜业供应的。在这些行业中大多是连家铺、小商贩,经营分散、零碎”[39]。据相关调查报告显示,“1955年蔬菜行业中私营批发商平均只占11.6%,零售方面私商比重较大,1955年第四季度还占零售商的36.84%”[40]。
改造之后,私营菜商和国营批发商店建立了经销关系。一些较大的私营坐商采取了联营并店的方式准备公私合营,一些摊商在国营商业公司的领导下组成了联购联销组或联购分销组,“城区3000多户私营菜贩已经全部分别组织了联购分销组。东单区菜贩在组织成联购联销组或联购分销组以后,还实行固定区域划片供应青菜”[41]。东单区、西单区共有蔬菜行业摊贩902户,从业人员940人,这些人中工人、农民、店员转业和常年卖菜出身的劳动者占90%,淡旺季收入差距大。实行联购联销、划片供应之后,菜价统一并相对稳定,便利了居民的生活。由市菜蔬公司供应货源,也解决了菜贩淡旺季收入差距大的问题,“过去淡季时一般收入都少,有的因收入少甚至吃不上饭;现在淡季一般每月收入30元左右,生活比过去有了保障”[42]。但联购联销组内菜贩的数量超过了实际需要,每个人的实际收入则相对减少;此外,由于工资分配不合理,缺乏必要的奖励制度,再加上蔬菜业被纳入了国家计划经济轨道之中,社员经营的积极性下降,增加了商品的损耗。“东单区东观音寺组,白菜不遮不盖在院内过夜,”[43]导致白菜受冻,损耗率大大增加。联购联销后原有的从业人员往往留作管理及辅助工作人员,而蔬菜业以夫妻店与连家铺的形式居多,联购联销后家属不参与售卖活动,旺季存在劳力不足的状况。
1955年12月14日《人民日报》发布社论《进一步开展对城市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文中肯定了对于城市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同时提出“只采用经销、代销办法已经不能适应目前客观形势的需要,现在应该进一步做出改造私营商业的全面规划了”[44],呼吁对于蔬菜等从业者以小商小贩居多且资本较小的行业,坐商采取国营公司领导之下组织合作商店的方法进行改造;对于摊商通过合作小组的形式将其组织起来,然后利用国营系统进行过渡。[45]北京市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将全市3668户菜贩全部组织起来,固定区域划片供应蔬菜,[46]在组织形式上不强求联销组的统一,“使他们联购分销或个别的单独经营,适当地划给一定区域流动”[47]。各菜贩统一由市菜蔬公司进货,按照菜蔬公司的牌价出售。实现联购联销之后,国营商业公司派出采购人员到各地采购的同时,利用公私合营批发商和原来自行采购的零售商的旧有采购路线与采购关系,丰富了市民的餐桌。“今年新年货源特别充足。有些去年供应不足的东西,今年都可以大量供应。大量的白菜、青韭、冬笋、西红柿等新鲜的蔬菜,由1000多户已经组织起来的商贩分别送到居民的门口。”[48]同时,北京市零售公司和食品公司适当地调整了国营批发部门对于零售商的批发起点,货源、资金上都给予了照顾,使原先以连家铺、夫妻店为主的蔬菜业增添了品种,增加了利润,如“东单区的元恒油盐店从零售公司借了30元以后,增添了黄花、木耳、青菜等17种商品,每天卖钱额从10元上升到20多元”[49]。
1958年中共北京市委宣布“要进一步改造小商贩”[50],提高了小商小贩的组织形式,又将各种形式的菜业全部升为单一的国营企业。1959年,北京市成立了市蔬菜办公室,统一管理全市的蔬菜产销工作,实施“产销统管、计划供应”等政策以及关闭集贸市场等措施,满足了“瓜菜代”政策下人民的饮食需求。对于不能维持生活的菜贩,政府采取吸收其进入国营商业系统的举措,北京市城、近郊区财贸系统吸收了大量的小商小贩,“1958年以后共吸收了小商小贩17009人”[51]。为了精简城镇人口,支援地方工农业生产,解决经济困难,北京市采取了疏散城市人口的策略,1960年中共中央规定家在县城集镇和大中城镇远郊,本人条件又适宜于参加农业生产的小商小贩,可以精简下放到农村落户,其工资福利待遇等暂时不变,[52]一些小商小贩就此还乡生产。
三、菜市“沉浮”:“禁不了”的蔬菜自由市场
尽管1956年京郊国营农场、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已经普遍与市菜蔬公司及其所属菜站签订“收购包销”合同,然而蔬菜自由贸易却并没有就此消失。在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个体菜商、菜贩被纳入了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成了所谓的“公家人”,然而自由贸易却屡禁不止。
(一)蔬菜场外交易的不断发生
虽然北京市不断发展国营商业网,国营商业网由1955年5月底的142处发展到1955年底的331处,然而蔬菜场外贸易仍然屡禁不止。在一些区域的国合副食商店附近出现了许多无照流动小摊贩,甚至一些地区形成了无照小摊商的集散市场,如“复兴门外木樨地铁路局职工生活用品供应站附近即聚集14个小摊商。其中有鱼贩4个、肉商1个、菜商3个、腌菜商1个……”[53]这些小摊商往往经营的是国营商店没有经营的品种或价格较国营商店更低,深得居民欢迎。离菜地较近的广渠门、阜成门摊商大多都在场外交易,“估计我区有70%的卖菜摊商进行场外活动”[54]。尽管政府部门积极改进蔬菜收购办法,打击无照摊贩,如京西矿区合作社提出“私商的售价每斤不得超过定价100元,同时私商进货5000元以上,必须有进货发票(须凭农民用的自产证换发票)”[55],然而場外活动还在日益增多。
场外交易的增加导致送往供销社的蔬菜数量减少、菜价起伏大,北京市政府严厉打击无照菜贩,由工商局、商业局、公安局、民政局、税务局、供销社等有关部门组成了市坊管理委员会,对市场进行整顿管理,划定自由市场让自产自销农民与有证照的商贩入坊交易,同时清查证照,取缔无证商贩。这一举措使蔬菜价格下降,交通市容状况改善。然而许多无照小贩在城内失去进货来源后,很快就到郊区,以高价抢购蔬菜,农业生产合作社向菜蔬公司交菜积极性下降,“东郊星火社今春产菠菜7万斤,只给菜蔬公司交售1万斤,不愿再履行产销合同”[56]。丰台区出现了社员把自留地产菜高价卖给小贩后从社内买菜吃的现象。一些社员想要退社经商。一时之间菜蔬公司货源减少,小贩高价居奇,群众不满,组织起来的菜贩抱怨不断。于是1957年5月6日,北京市委宣布取消了蔬菜的自由市场,而与此同时国营商业部门并没有及时满足群众对于购菜、增加品种的需求,群众议论纷纷,“管理之后价格降低,的确是好,但是吃不上小葱了”“你们把小贩赶跑了,我们又得去排队”[57]。
(二)机关单位私自下乡采购
一些机关单位绕开合作社直接向生产队高价收购蔬菜、鲜瓜果等。“自1961年下半年以来,有96个单位私自下乡采购。共采购蔬菜94万斤,瓜果18万多斤。”[58]有的单位以高于市场牌价的价格进行采购或以物物交换的形式将国家统一分配的物资换为家畜和蔬菜,支援农村以换取蔬菜。“北京北郊炮兵学校,11月13日抽出230人到朝阳区来广营公社清河营生产队劳动两天,然后以每斤四分的价格买回胡萝卜1万斤。”[59]尽管北京市委多次下发通知谴责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私自下乡采购蔬菜等副食品的乱象,但一些单位经有关部门处理后仍然置之不理。场外交易的增加导致送往供销社的蔬菜数量减少、菜价起伏大,原有的供销社与生产队之间的交售关系被打乱,大量生产队绕开合作社,直接自销或者好的自销坏的交售,影响农业生产。国营商业对市场的原有安排,国家收购农副产品的计划也受到影响。1957—1962年,北京市多次清查证照,取缔无证商贩,交通市容状况一定程度上得以改善,菜价也趋于平稳,无照菜贩数量大大减少了,但大部分并没有就此消失而是更换售卖的品种或改为夜间售卖逃避管理。
“菜篮子”关系到居民的饮食保障和民生福祉,是一个重大的民生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北京,一方面人口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出于增强国民体质、改善民众营养的考虑,对蔬菜的需求量不断增加,蔬菜供求矛盾突出。在这一背景之下,北京市采取多种措施,不断调整蔬菜供销政策,从自由经营到“收购包销”再到“统购统销”,逐步将蔬菜供应纳入计划轨道,有效保障了蔬菜供应;然而蔬菜自由市场却屡禁不止,场外交易的不断发生、机关单位绕开供销合作社直接下乡采购、摊商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弥补了蔬菜经营网点布局不合理的问题,为城市经济发展注入了一定的生机和活力。
*本文系中国政法大学2023—2024学年硕士研究生创新实践项目“菜市‘沉浮:北京市蔬菜供销政策变迁(1954—1962)”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及参考文献:
[1]杨胜.漫谈营养科学[N].人民日报,1949-08-30(5).
[2]吴宪,周启源.如何改进人民营养[N].人民日报,1949-08-30(5).
[3][6]北京市第二商业局史志办公室.当代北京副食品商业[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534,22.
[4]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综合卷·人民生活志[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213.
[5]周一兴.当代北京大事记(1949—2003)[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44.
[7]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3)[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562.
[8][36][37]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商业卷·副食品商业志[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121,121,122.
[9][10][14][17][24]市供销社、工商局、市财委关于蔬菜供应、采购、销售及菜市场迁移问题的请示及市府的批复,档号:002-006-00171,北京市档案馆藏。
[11][13][19][22]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4)[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19,543,575,740.
[12]海淀区远大农业生产合作社通过生产计划,并向该区各兄弟社提出春耕生产竞赛[N].北京日报,1955-03-10(2).
[15][38]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5)[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22,216.
[16]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关于蔬菜市场供销情况的报告,档号:001-006-01025-00052,北京市档案馆藏。
[18][21][23][54]市财委关于对蔬菜供应、菜贩的情况和安排意见,档号:004-016-00437,北京市档案馆藏。
[20]从刘长龄事件中应当吸取什么教训——坚决清除资本主义经营思想[N].北京日报,1956-02-27(2).
[25]提高上市蔬菜的质量[N].北京日报,1956-04-28(2).
[26]大批白菜为什么冻坏了[N].北京日报,1956-02-10(3).
[27]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报告:目前菜市场存在的问题及今后意见,档号:002-006-00171,北京市档案馆藏。
[28][30]酒仙桥居民的大喜事——记酒仙桥商场开幕的第一天[N].北京日报,1956-04-13(1).
[29]本市正在有步骤地调整商业网[N].北京日报,1956-03-19(1).
[31]郊区六个区乡乡出现中心商店[N].北京日报, 1956-04-13(1).
[32]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农业卷·农村经济综合志[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8:200.
[33][34][35]关于蔬菜产供销调查材料(一),档号:001-006-02089,北京市档案馆藏。
[39]本市加强对經营副食品私营商贩的改造[N].北京日报,1955-12-11(1).
[40][47]北京市第三商业局改造菜商菜贩报告,档号:119-001-00092,北京市档案馆藏。
[41]东单区300多户菜贩组织起来联购联销昨天起实行固定区域负责划片供应青菜[N].北京日报,1955-11-20(1).
[42][43]中共北京市委财政贸易工作部关于东单区、西单区菜贩联购销以后经营情况和存在问题的检查报告,档号:001-021-00018-00001,北京市档案馆藏。
[44][45]进一步开展对城市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N].人民日报,1955-12-14(1).
[46]3668户菜贩全部组织起来,全市实行固定区域划片供应青菜办法[N].北京日报,1956-01-17(2).
[48]办年货,过新年[N].北京日报,1956-01-01(3).
[49]公私合营后连家铺经营品种增加[N].北京日报,1956-03-28(2).
[50]进一步改造小商小贩[N].北京日报,1957-03-04(2).
[51]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63)[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113.
[52]关于精简、下放支援农业生产第一线对资产阶级分子、小商小贩区别对待问题的几点意见,档号:123-001-00728,北京市档案馆藏。
[53]中共北京市委财政贸易工作部办公室1956年《工作简况》(第2号)——新市区国营商业网情况、西郊新区无照流动摊商仍甚活动、市菜市场公司新建储菜窖门小、道窄、进出库极慢,档号:001-021-00036-00003,北京市档案馆藏。
[55]市场情况简报,档号:046-002-00442,北京市档案馆藏。
[56][57]企业单位原市场管委会关于申请证明提出询问及取缔无照摊贩简报等,档号:046-002-00717,北京市档案馆藏。
[58][59]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62)[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7,8.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