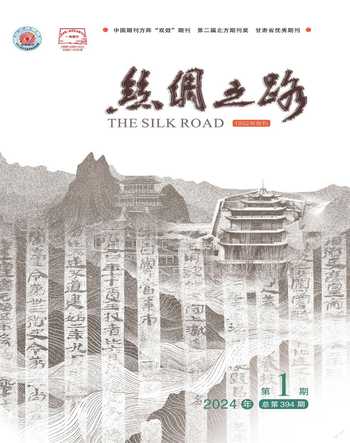吐蕃时期丝绸纹样及其价值考究
赵文琪
[摘要] 吐蕃时期棺板画上人物服饰及丝绸的使用,直观再现了当时对丝织品的应用方式与部分常见纹饰。当代藏族手工艺品存在装饰纹样陈旧、形制与纹样循环往复使用、相互借鉴抄袭等弊端。从吐蕃时期丝织品中提取出的大量装饰纹样元素,既能原汁原味地再现还原与弥补当前藏族工艺美术纹饰中缺失的吐蕃韵致,又能将当时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文化艺术图像体系部分还原,对现当代西藏美术发展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价值意义。都兰吐蕃墓出土了大量吐蕃时期丝绸残件,其中质地为锦的丝织品材质厚实,复杂花纹出现其上的可能性较大,绫、绢等材质则更易出现几何纹样。吐蕃时期缂丝传递出来自中西亚风格的气息与色彩,刺绣则更可能出自中原地区或汉族工匠之手。繝与絣虽有出现,但现已知数量仍较少。国内出土吐蕃时期丝织品有着丰富的材料及类型,对于探究丝绸之路艺术具有进一步整理分析的研究参考价值。
[关键词] 吐蕃;丝绸;纹样;藏族美术;丝绸之路
[中图分类号] K8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5-3115(2024)01-0160-07
吐蕃时期丝织品在海内外仍有保存状态完好的文物,形成了独具特色、影响后世的藏族纹样艺术,可作为解析藏族装饰纹样美术形式语言的参考佐证,还可从大量罕见珍品实物中窥见吐蕃作为丝绸之路强大帝国的华贵风貌[1]10,具有深入考察与研究价值。本文对吐蕃时期丝织品的纹样与其他时期、地域考古出土丝织品纹样的异同有所提及,然而基于突出研究主题尚未做过多具体图像学考辨比对。通过对吐鲁番时期丝绸纹样及其价值进行考究,旨在解决提取各类型丝织品纹样设计元素的组合判别要素与进行纹样源流考究,试图建立起该时期丝织品的纹样组合判别标准。
一、吐蕃时期丝织品的历史背景
丝织品便于携带,在丝绸之路上流传甚广,因而吐蕃时期丝织品混杂着来自不同民族地域文化的风格类型。已知现存吐蕃时期丝织品中,各方风格杂糅迥异,明确带有吐蕃自身风格的丝绸、明确符合吐蕃系统条件的丝织品仍有待斟酌辨别。由于对丝织品纹样的具体考究涉及多方文化内涵比对,基于该研究整体的严谨性考量,文章命题为“吐蕃时期丝织品纹样考究”而非“吐蕃系统丝织品纹样考究”相对更准确无误。
唐蕃双方有记录的使节往来近200次,唐章怀太子墓壁画礼宾图中绘有吐蕃使者形象[2],史料中还有提及贡物、方物等具体品种的文献记载。唐朝廷专门设立交易机构,用茶叶、丝绸、粮食、布帛等物品,与青海等地的吐谷浑、吐蕃、党项人交换马、牛,以弥补军用马匹及生产生活所需牲畜的不足。公元7-9世纪,吐蕃不断对外扩张,因而藏文在吐蕃统治下的地区成为官方文字语言得到广泛运用,同时藏族宗教、生活习俗也流传影响着这些地区。如作者的一部分实地考察一手资料来自唐蕃古道上的湟源古道博物馆,湟源原为唐所设鄯城县地,开元二十二年(734)改为吐蕃属地,并于湟源形成历史上著名的“海藏通衢”“茶马互市”,立碑于赤岭(日月山),以区分吐蕃界。随着唐蕃古道的开通,唐蕃之间经济往来密切,物资贸易频繁。朝贡贸易是该时期唐蕃经贸关系的一大特色,促进了双方的经济发展[3]。
唐蕃古道一直延伸至南亚次大陆,形成了通往印度的天竺道,通往尼泊尔的泥婆罗道,并将中国西部与南亚地区连接在一起,承载了东西方商品贸易、文化传播的重要功能。为充分调查研究吐蕃时期丝织品纹样,笔者重新走访了唐蕃古道。丝绸织物作为中西贸易使者,使中外贸易、文化交流得到长足发展。大量罕见吐蕃时期珍品实物,使人们了解吐蕃作为丝绸之路上强大政权的实力,并形成独具特色、影响后世的藏族纹样艺术体系,具有进一步考察研究价值。
伴随吐蕃墓所出土的吐蕃时期棺板画现有不少遗存,如在湟源古道博物馆、海西州民族博物馆、都兰县博物馆、青海藏文化博物馆等地采集到的吐蕃棺板画实物图像资料。各大展馆内陈列的吐蕃棺板画内容形式丰富、大小各异,所绘形象有保存完整者,亦有漫漶不清者。笔者所选取的吐蕃时期棺板画样本均为图像保存完好且绘有吐蕃时期服饰的丝绸纹样,其中除国内收集到的吐蕃棺板画真实出土实物白地彩绘人物牵馬图木板画、青海郭里木吐蕃墓葬1号棺板画A板、郭里木吐蕃墓葬1号棺板画B板外,另有三件流散海外私人收藏棺板画如木棺板画吐蕃贵族帷帐图、木棺板画吐蕃贵族飨宴图、木棺板画吐蕃时期贵族狩猎图等。从当时棺板画工匠的美术技艺熟练程度、整体场景的真实还原度与真实的出土吐蕃时期丝织品材料比对,可证明吐蕃时期棺板画中对吐蕃时期丝织品纹样基本做到了总体概括还原。吐蕃时期棺板画上人物服饰及丝绸的使用,直观再现了当时对丝织品的应用方式与部分常见纹饰。
传世美术作品中的吐蕃时期服饰纹样,着重于对现存当时壁画中的“场景再现”。除吐蕃棺板画外,以敦煌莫高窟、榆林窟壁画中的吐蕃人物形象场景与西藏日喀则艾旺寺、松赞干布造像为例,进一步深入细致研究了传世美术作品中吐蕃时期人物着装具体服饰形制。从而为未来研究收集整理了宝贵史料,使吐蕃时期丝织品纹样研究不只停留在丝绸残片“窥一斑”的局部细节内容上,增强了整体研究面貌的全局观和大局意识。
二、吐蕃时期丝绸纹样的应用价值
经调研发现,目前现阶段的当代藏族美术工艺品,存在装饰纹样陈旧、形制与纹样循环往复使用、相互借鉴抄袭等弊端。从吐蕃时期丝织品中提取出的大量吐蕃装饰纹样元素,既能原汁原味地再现还原与弥补当前藏族工艺美术纹饰中缺失的吐蕃韵致,又能将当时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文化艺术图像体系部分还原,对现当代西藏美术发展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价值意义[4]。此外,对吐蕃时期丝织品进行纹样考究,还能进一步促进了解当时提花机的使用方式与进行当代提花织机对吐蕃时期织物纹样的复原实践。
随着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发展,当时的西方各种织物设计图案开始影响丝绸设计,有些是主动模仿和采用西方题材进行设计[5]。作为丝绸之路的主角,丝绸产品及生产技术与艺术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内容被传播到世界各地,为东西方文明互鉴做出了卓越贡献。千余年前,丝绸之路将世界连在一起。对考古出土吐蕃时期丝织品的深度解析能使大众更深入了解历史上的重要时期,吐蕃时期丝织品以其美观、珍奇及精良工艺著称于世[6],其纹样经由四条吐蕃大道与丝路上的东西方文明交融。吐蕃时期的丝织品能弥补吐蕃文物被低估了的新国际美学价值,丰富藏族美术新图式理论。用物态化、形象化表现精神世界和审美情趣的方式是民族自信的映射,协调与冲击、多样与统一、节奏与韵律的美学法则,在少数民族服装和配饰以及丝绸织物纹样图案组成上得到很好诠释。民族文物是各族人民珍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载体,随着时代变迁,传统民族文化有的发生了巨变,有的正在消亡,通过对民族文物这一客观对象的美学因素认知,探究民族文物的审美价值及其吸引力的内在根源,进而保存和提升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与记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和谐社会、培育民族精神、彰显人文情怀、推动人类文明对话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吐蕃时期丝织品纹样研究,在藏族地区日用服饰领域图案题材设计、藏族地区新兴文化创意产业旅游产品、室内软装等领域应用价值较突出,对文创产品的开发生产应用具有较高的借鉴传承价值。
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在于人能使用符号,并借此代表(或象征)真实世界的某一方面。赋予某特定符号的含义通常是随意的,往往不标记应当代表世界上某指定物体[7]363。赋予一个设计符号的含义对于某特定文化而言是独有的,如体现在吐蕃时期丝织品纹样主纹中的联珠纹、含绶鸟纹、对兽纹、几何纹,以及辅纹中的宝花纹、宾花纹、卷草纹等。正是由以上独特元素,组成了吐蕃时期丝织品纹样的符号判别体系。此时的每一该阶段固定统一的设计符号,都具有吐蕃时期纹样设计元素的指向意义。一般不大可能单凭图像或设计符号式样来推断其在某一文化中的含义,须厘清该纹样式样是如何使用的,并从其他符号背景中综合分析。图符和丝织品本身不会直接告知它们的含义——尤其是在没有太多文献依据的情况下。科学的理论方法原理即研究者必须提供解释,可以存在几种不同的解释。如有必要,用清晰的评估程序进行检验,并根据最新资料相互参照[7]364,此为设计符号学对丝织品纹样考究的具体应用。
都兰吐蕃墓出土了大量吐蕃时期丝织残件,尤其集中在都兰吐蕃1号墓与3号墓中。笔者对整体吐蕃时期丝织品进行研究梳理,通过多年的考察过程中收集了国内外多地大量一手丝绸资料并拍摄高清照片,保存了出土吐蕃时期丝织品的真实尺寸或修复后的现状尺寸数据。通过对收集的103件吐蕃时期丝织品收藏地、年代、名称(编号)、纹样类型、质地品种、数量、收集地点等信息逐一详细整合归纳,并统计出各类型丝织品占比。对出土织物标本为何多为残件进行了讨论,结论为装饰、仪式、盗墓三种可能性或均有发生。由于锦的质地厚实,出现复杂花纹可能性较大,绫、绢等材质则更易出现几何纹样。吐蕃时期缂丝传递着来自中西亚风格的气息、色彩[8],刺绣更多可能出自中原地区或汉族工匠之手。繝与絣虽有出现,但仍较为小众。国内出土吐蕃时期丝织品有着丰富的材料及类型,对于探究丝绸之路美术具有进一步整理分析与研究参考价值。
三、吐蕃时期丝绸的主纹与辅纹考究
丝绸质地本身便给人一种温暖华美、流畅耀眼的精致华丽感,尤其是吐蕃时期常见锦的质地,加之其色彩丰富的纹样与底色交相辉映,形成让人流连忘返的视觉与触觉双重审美体验。正由于此种华贵的诱惑,吐蕃不惜发动侵略战争以掠夺这些如黄金般珍贵的丝织品。因此,吐蕃时期丝织品具有多民族、多国家共同的多元文化艺术审美属性,基于当时吐蕃疆域的辽阔、民族的丰富性,吐蕃时期丝织品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物质精神文明面貌。在纹样结构上,多以抽象解构的方式提取写生花草纹样的某些结构元素。再以织机易于接受的面积大小,于方寸间精心布局,最终呈现精巧绝伦的整体纹样构成。
吐蕃时期丝织品纹饰精美考究,无论是制作工艺还是设计形式都富有其鲜明特点。当时的丝织技术有了很大发展,由于纬线的灵活多变,织出比经锦更繁复的花纹及宽幅织物,并能充分显示丝线的光泽。因而纹样更为丰富多彩,出现了带有精美织锦的衣物并保存至今。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对话,勾勒出吐蕃王廷的轮廓,吐蕃时期丝织品展现了吐蕃王廷的实力,代表了一种融合多地域模式的独特“唐吐蕃中亚混合风格”[1]11。对纹样中的主纹与辅纹依照类型进行逐一提取、分析解读,以原创手绘的方式探讨、区别、创新前人部分研究成果,从图案、纹样源流等层面厘清吐蕃时期丝织品相对固定的特征模式,能为吐蕃时期丝绸的判别提供学理支撑。
吐蕃国力雄厚,从当时几乎等价于黄金、价值贵重的丝绸,亦可窥见一二。吐蕃时期丝织品装饰纹样的主纹包括动物紋、人物纹、几何纹等类型。本研究将其细分为禽鸟纹(含绶鸟纹、对鸟纹、其他种类鸟纹),走兽纹(马纹、羊纹、狮纹、鹿纹、异兽纹),人物纹及几何纹等类型。主纹是吐蕃时期丝织品纹样的重要主题呈现,展示了该时期审美风貌、审美追求与独具风格特色的文化内涵。
吐蕃丝织品中鸟的形象,主要种类为绶带鸟、鸟冠、禽鸟大类、鸟雀、对鸟纹,其他种类如凤凰、鹦鹉、鹰纹样等。通过相关研究,能从中进一步发现禽鸟纹样的装饰风格源流,包括中亚粟特式、萨珊波斯式、吐蕃本土式、大唐东传式。如从吐蕃出土丝织品中大宗鸟类纹样图像层面,可解析当时的时代特征与价值观念。吐蕃时期对鸟纹丝织品保存完好者尚有不少,对鸟中有含绶鸟的形象,也有一些不是含绶鸟的绶带鸟类型。吐蕃时期的丝织品中,留存图案纹样清晰度、完整度最高者为锦这一丝织品类型。有些锦织物上的纹样甚至完好如新,如现藏于湟源古道博物馆的对鸟纹锦等。已知流散海外的吐蕃时期对鸟纹锦,保存状况同样较完整。
吐蕃时期饰有马纹的丝织品通常以对马形象出现,团窠联珠对马纹类型数目较多,其余对马纹样丝织品中富有西方意匠装饰纹样风格者居多。羊的形象有位于联珠团窠纹之内的,也有作为宾花辅纹的。吐蕃时期丝织品上作为主纹的狮纹与各类型辅纹的组成元素结构形式多样,狮纹丝织品姿态生动、形象各异,呈现出多元化风格面貌。鹿纹丝织品中,有鹿造型中规中矩程式化者,有自由写生纹样,有西方意匠风格,也有纯几何图案打造等多种呈现方式。异兽纹是人们主观臆造出的兽类形象,这些非现实生活中所见动物在吐蕃时期丝织品中屡见不鲜。
吐蕃时期丝织品中的几何纹样,目前可见具体图像有菱形、矩形、直线形、多边形、圆形、三角形、“回”字纹、龟甲纹等。其他复杂图案多见于锦的质地类型,而几何纹样中则多包含绫、绢等织物质地类型品种。人物纹织锦中能进行清晰迅速判别的形象,具体可依据着装上带有吐蕃服饰翻领、窄袖、长袍等具备中亚风格服饰特征的人物纹形象。其中一部分人物纹丝织品无论是人物形象、衣着服饰,还是整体行进状态与身旁的吐蕃类型狮纹、马纹,均较好地体现了它们的吐蕃本土属性。还有一种吐蕃特征的人物形象,直接依据其五官容貌进行判别,如胡人形象的高鼻深目、须髯浓密,头顶处或有日月纹装饰。且在吐蕃及之后的很长一段岁月,至今都能在藏族地区见到这种上圆下弯月的藏族装饰符号日月纹。当吐蕃人物纹作为丝织品主体纹样出现时,同为吐蕃系统设计符号的狮纹、马纹,在其侧旁同时出现,呈现出一种人物与动物丰富组合图式的情况亦较多。
辅纹中的宾花纹是吐蕃时期丝织品的主要特征之一,宾花纹可分为中心圆式十字宾花、中心方形式十字宾花、三线型十字宾花三种类型。吐蕃时期丝织品中的联珠纹样一般存在于团窠圈内,即团窠联珠纹,团窠联珠纹在联珠纹中所占比例偏高。
宝花纹样多为源自佛教题材的装饰图案,于吐蕃中期即公元8世纪左右出现较多。与宝花纹同时出现的组合动物纹样元素有立凤纹、狮纹,盛世时期的宝花纹常见大窠、中窠等大小,证明着吐蕃王室的尊贵地位。吐蕃时期丝织品中的大型宝相花纹纹饰繁复,以对称的六瓣、八瓣为主,色彩简约高贵,透露出王室的威严气质。吐蕃时期丝织品中带有团窠圈纹的几乎全部出现在具有西方纹样风格的丝绸上,其中有一种中心略呈竖长椭圆状的八瓣团窠圈纹于本文采集的12件吐蕃时期瓣窠圈纹丝织品中出现了三次,占比25%。
吐蕃时期丝织品的组合元素呈现多元化、多样化的立体组合形态,其中有一些组合有着相同或相近的元素类型。基于这些固定化组合模式,形成了一套相对准确、与前吐蕃时期和吐蕃时期之后丝绸风格迥异的丝织品判别标准。相对稳定的动植物纹、宾花纹造型,也是该时期丝织品的判别要素之一。相关各类动物纹的形象,在吐蕃系统丝织品中能够找到组合纹样元素雷同或近似的一些织物。由此可证明吐蕃时期丝织品的身份来源、销售渠道、贸易区域相对稳定,因其购买者的喜好,逐渐形成了相对固定的丝绸需求。
吐蕃时期丝织品中有着丰富的粟特锦材料,依据其色彩样貌被分为青、绿、黄色为主的冷色系,红、黄、藏青色为主的暖色系两类[10]。在103件吐蕃时期丝织品实物资料中,以大面积红色為底色的丝织品有23件,占比22%。以红色为底色的吐蕃时期丝绸屡见不鲜,在吐蕃棺板画与传世美术作品中的服饰上也有体现。其一,说明吐蕃人衷情于红色,并有可能以红色为族属的代表象征,如传世美术作品中吐蕃人涂红的赭面这一鲜明特点。其二,吐蕃尚红的审美追求从吐蕃腹心地带曾出土的涂红砺石上可窥见一二,证明吐蕃族属的审美喜好一直延续下来。时至今日,西藏自治区的人们也似乎对鲜艳的红颜色有着某种特殊的偏好,这或许与西藏长期暴露在日光充足且纯净湛蓝天空的环境中,对艳丽的色彩更加敏感相关。在现代藏族地区的宗教圣地建筑与民族服饰中,藏红色仍为尊贵、显赫、正统的象征。
色彩美作为吐蕃时期丝织品审美重要的组成部分,与纹饰美、质地美一样,以其经年不衰的靓丽斑斓,时至今日依然动人心弦。如典雅沉淀的暗纹宝花纹,通常与其底色巧妙融合为一体,彰显着富贵、华丽、优雅的审美特质。即使是素色暗几何纹路丝绸,同样因独特的纹路质地与光泽美,在日常穿着中大放异彩、温暖人心。吐蕃时期丝织品几何纹样上出现的冷暖色相、明度差异化对比,在当今设计美学的应用中仍然经久不衰。
流散海外的一批吐蕃时期丝织品,具有保存完整如新、纹样复杂精细、品种丰富多样、呈现形制与构图别致、造型独特出彩等审美特点。纹样与人的意识形态相关联,不同的纹样代表着不同的观念文化,纹样符号各有其背后的文化含义。纹样符号本身,便带有具备一定“基因”属性的文化内涵。将吐蕃时期丝织品纹样进行数字化分类复原,可应用于各类传统或改良藏装(新藏族民族服饰)、西藏特色旅游用品、藏式布制品等藏族传统手工艺产品及西藏文创产品,实现吐蕃时期丝织品纹样在现当代的商业价值。还可在影视剧的制作中,注入真正还原史实的藏民族服饰纹样,并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
四、结语
随着丝绸之路文化的交流发展,当时的西方各种织物设计图案开始影响丝绸设计,有些主动模仿和采用西方题材进行设计。作为丝绸之路的主角,丝绸产品及生产技术与艺术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内容被传播到世界各地,为东西方文明互鉴做出了卓越贡献。千余年前,丝绸之路将世界连在一起。对考古出土吐蕃时期丝织品的深度解析能使大众更深入了解历史上的重要时期,吐蕃时期丝织品以其美观、珍奇及精良工艺著称于世,其纹样经由四条吐蕃大道及丝绸之路的东西方文明交融。吐蕃时期的丝织品,能弥补吐蕃文物被低估的新国际美学价值,丰富藏族美术新图式理论。用物态化、形象化表现精神世界和审美情趣的方式是民族自信的映射,协调与冲击、多样与统一、节奏与韵律的美学法则,在少数民族服装和配饰以及丝绸织物纹样图案组成上得到较好的诠释。民族文物是各族人民珍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载体,随着时代变迁,有的传统民族文化发生巨变,有的正在消亡。通过对民族文物这一客观对象的美学因素认知,探究民族文物的审美价值及其吸引力的内在根源,进而保存和提升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与记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和谐社会、培育民族精神、彰显人文情怀、推动人类文明对话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吐蕃时期丝织品纹样研究,在藏族地区日用服饰领域图案题材设计、藏族地区新兴文化创意产业旅游产品、室内软装等领域应用价值较突出。同时,对文创产品的开发生产应用有较高的借鉴传承价值。随着工业产业化道路的发展,从吐蕃时期丝织品的精彩藏族美术风格纹样中,可体会“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内涵,还可体会西藏贵族精英家庭鼎盛时期的辉煌文化艺术传承。对更好地开发当代藏族美术设计有一定借鉴价值,对研究宏观整体的藏族美术形式语言发展结构层次有一定的补充与推动意义。在提取出吐蕃时期丝织品纹样的装饰图案组成元素内容后,对吐蕃时期丝织品纹样的文化内涵、价值意义进行实践拓展体现。并将吐蕃时期丝织品纹样元素直接应用到现当代藏族美术、藏族设计领域中进行实践,以期达到一定的经济价值以及藏族历史文化传承与社会发展效益。
[参考文献]
[1]王旭东,汤姆·普利兹克.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艺术珍品[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20.
[2]吴明娣.汉藏工艺美术交流史[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14-15.
[3]康·格桑益希.藏族美术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5:81-214.
[4]格桑多吉.藏族传统纹样中几何纹样的类型及其文化解读[J].西藏艺术研究,2018,127(01):11-21.
[5](美)陈步云著,廖靖靖译.唐风拂槛:织物与时尚的审美游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174-178.
[6](意)康马泰著,李思飞译.青海新见非科学出土奢华艺术品:吐蕃统治区域的伊朗图像[J].敦煌研究,2020,179(01):16-22.
[7](英)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著,陈淳译.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8]徐铮.中国历代丝绸艺术· 隋唐[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22-118.
[9]首都博物馆.锦绣中华——古代丝织品文化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