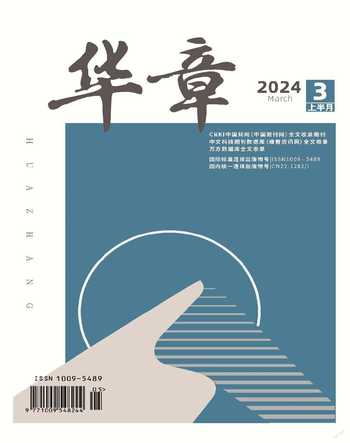试析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体现
[摘 要]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明文规定的基本原则,是刑事立法的基石。但是该原则在司法适用时,却遇到了错误入罪理念的倾向、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兜底条款的滥用等问题。而分析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争议可以总结出上述问题的存在原因。对于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解,理论上存在“一点论”与“两点论”之争,如果认为罪刑法定原则是将“要定罪处罚”置于第一顺位,就会导致司法机关只以追求定罪为目标,对兜底条款的适用也是偏向于扩大解释,会导致冤假错案的出现。所以,应当重申罪刑法定原则的根本精神,即有利于被告人精神,这是由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原则和刑事诉讼程序中被告人的弱者地位所决定的。贯彻有利于被告人精神,才能使得罪刑法定原则得到真正落实。
[关键词]罪刑法定;疑罪从无;认罪认罚
罪刑法定原则是1997年《刑法》明文规定的,以此为标志废除了1979年《刑法》的类推制度。作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在我国刑法立法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作为刑事法治的基石,也贯穿于刑事诉讼法的理念当中,如“疑罪从无”思想。可见,对罪刑法定原则进行深入理解与合理运用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我国《刑法》第三条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表述是: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进行定罪处罚;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由于该法条将“定罪处罚”置于前面,所以在我国理论界有“两点论”与“一点论”之争[1]。在司法实践当中,也存在因原审法院僵化运用法律条文而被改判的案例,比如“内蒙古王某某收购玉米案”等。此外,从《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出台可以看出,近几年的刑事立法趋势都是贯彻从严立法、预防性立法理念,积极回应社会热点事件,反映了刑法的保护法益机能。然而,保护法益固然重要,而面对日益趋重性的立法,司法实践要如何正确应用是当今面临的一大难题。因此,归根结底,还是应当回归到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涵与根本精神上来,在加快立法、从严立法的当今时代重申罪刑法定原则的理念。
一、问题的提出
(一)错误入罪理念的倾向
在刑事诉讼领域,一贯推崇的“疑罪从无”理念是从罪刑法定原则派生出来的,也反映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价值取向。但是作为各国刑事诉讼领域的“金科律令”,“疑罪从无”的思想在我国多年来都未被真正贯彻落实。而其中至关重要的原因是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存在着“疑罪从有”的观念。像佘祥林案、呼格吉勒图案等冤假错案,都是因为司法人员具有根深蒂固的“疑罪从有”的入罪理念。而与此相反的是美国的辛普森杀妻案,从中可以看出英美法系对司法程序的重视及“疑罪从无”思想的真正落实。
与此同时,“疑罪从轻”思想也是一种错误的入罪理念[2],却由于其表面似乎比较具有妥协性,所以被司法机关大量运用,甚至成为冤假错案的祸根。比如,当年具有社会轰动效应的赵作海冤案,被告人的后果虽然并未像呼格吉勒图那般严重,但是该起案件也是在未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就进行了判决,所以依然反映了司法人员的错误入罪理念与非审慎的司法态度。“疑罪从轻”的理念相较于“疑罪从有”的理念,似乎更能夠达到保障被告人权益和回应社会舆论的平衡状态,所以各位司法人员运用得心安理得,毕竟也没有造成不可挽回的结果。但是它们二者的共同之处都是偏离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理念与核心精神,面对被告人都是以一种“有罪”的心理去看待。多年的司法实践表明,“疑罪从无”思想是其他任何入罪理念诸如“疑罪从轻”等思想无法替代的[3]。
(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引发的深思
相对于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确实更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4]。我国刑事诉讼程序虽然采取控辩制的诉讼模式,但是绝大多数的法院依然是以法官为主导,审判程序就类似于走个流程,所有的调查取证工作都能在审前程序处理完毕。而现如今许多诉讼制度,如“简易程序”“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等都是为了加快诉讼效率而制定的。这些制度固然有其内在价值,但是如果在司法实践中没有被审慎利用,也只会助长冤假错案的发生。
一项制度不是生来就优秀的,必须经过社会发展的检验。因此在贯彻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同时,要明确其适用范围与条件,目的是保障被告人权益,并且强调认罪认罚的自愿性要求。
(三)兜底条款的滥用
兜底条款是一种立法技术,其在法律条文中,通过“其他、等”概括类词语对罪名的罪状进行扩充性描述,以应对立法时无法预见的事项,并加强法律条文适用的灵活性。但是由于兜底条款先天具有罪状模糊性的缺陷,因此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许多适用问题。主要可以归结为:
1.对兜底条款的机械使用
比如,内蒙古王某某收购玉米案,由于构成非法经营罪以违反有关国家规定为前提,所以原审法院因王某某未办理粮食收购许可证而擅自收购玉米,就认为其符合非法经营罪的兜底条款。该做法表面上符合法律规定,实际上却忽视了行为人本身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
2.兜底条款的打击范围过大
兜底条款是对罪名的高度抽象概况,因此给予了司法人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许多罪名逐渐有变为“口袋罪”的趋向。最为典型的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刑法修正案(十一)》出台之前,高空抛物以及妨碍驾驶等行为一般都会被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兜底条款的滥用体现的是刑法对民意的过度关切,却忽视了刑法本身的谦抑性价值并且损害了被告人利益。
二、明确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容
上述种种问题,都可以归咎于对罪刑法定原则的错误理解。罪刑法定原则源起于英国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该宪章第39条规定:“不经适合其身份的合法审判和国家法律,任何人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或不得被驱逐、施暴和被剥夺法律保护”。随后,随着各国立法的演进,最终1810年《法国刑法典》中明确规定了该原则,并被各国立法所沿用。因此,可以看出,罪刑法定原则一开始就是反对封建王权剥削公民权利的产物。由于公权与私权相比本身就更为强大,因此需要用罪刑法定原则去压制公权,保护公民的私人权利。在现代社会,所谓公权就是司法机关与国家的权利,因此确立罪刑法定原则就是为了防止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被司法机关过度压制。
当然,公民的合法权益包括被害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但是罪刑法定原则更加偏向于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对此,可以从理论上对于刑法定原则条款的“一点论”与“两点论”之争进行展开说明。由于我国《刑法》第三条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表述是: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进行定罪处罚;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支持“两点论”的学者认为,由于法条将“定罪处罚”置于“不得定罪处罚”之前,所以罪刑法定原则必然是同时规定了按规定定罪处罚以及没有明文规定不得定罪处罚两方面内容。原因在于,刑法除了要保障被告人的权益,还应当保护被害人和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毕竟刑法的作用在于平衡保护法益与保障人权的关系。甚至有学者认为,出于语序问题,所以“定罪处罚”是第一顺位,“不得定罪处罚”是第二顺位。支持“一点论”的学者则认为前述学者的观点是混淆了刑法的机能与罪刑法定原则的机能,刑法的确同时具有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的机能,而罪刑法定原则只有保障人权的机能。
笔者赞同“一点论”的观点。首先,因为在支持“两点论”的同时,就要求将“依照法律进行定罪处罚”置于优先地位。由此就产生了前述问题:错误入罪理念的倾向和兜底条款的滥用。换言之,如果将“依照法律进行定罪处罚”放置于第一位,司法机关在观念上就会对被告人产生“疑罪从有”的趋向。因为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司法机关的目标就在于通过刑法的明文规定对被告人进行定罪量刑,所以需要寻找一切证据以证明嫌疑人是有罪的,可见这个理念从一开始就十分具有偏向性。理论对实践是具有指导作用的,所以理念的确立会深深地影响实践的操作。如果将“按规定罪处罚”置于第一位,那么“疑罪从有、疑罪从轻”的观念将永远不会消失,“疑罪从无”的观念也难以确立。
其次,在对兜底条款的解释方面,现今许多实务中的做法更能体现“两点论”的适用,因此导致罪刑法定原则被僵化运用。兜底条款的存在价值在于面对无限变化的客观社会,突破法律语言的局限性以更好地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既然兜底条款本身的机能就是偏向于保护法益,那么进行适用的过程中就更加应该兼顾保障人权,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如此才能限制兜底条款的滥用。
综上所述,罪刑法定原则的定位在于保障被告人权益,基本内容也是“不得定罪处罚”,这才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内容。此外,罪刑法定原则还派生出了禁止习惯法、禁止类推适用等原则,本质上都是对“不得定罪处罚”的反应。
三、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根本精神
(一)有利于被告人是根本精神
如前文所述,罪刑法定原则偏向于保障人权,这个人权主要是指被告人的权益。而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精神就在于有利于被告人,其原因可以做出如下分析:
首先,在刑事实体法领域,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原则都能体现有利于被告人精神。比如事前的罪刑法定即禁止溯及既往,其有例外的不禁止有利于被告人的溯及既往。严格的罪刑法定是指禁止类推适用,同样也不禁止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适用。确定的罪刑法定在于强调刑法条文的明确性,如果其罪状过于模糊就反映了条文的不明确性,会违背国民预测可能性,此处的国民也主要指被告人。综上所述,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原则都贯穿了有利于被告人的理念,因此有利于被告人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根本精神。
其次,在刑事诉讼法领域,被告人的弱者地位要求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精神必须是有利于被告人。在中国的刑事诉讼领域,被害人的权利往往由国家公权力机关代表——检察院进行主张,而被告人只能通过辩护律师及自我辩护来主张自己的权利。无论是从资源渠道还是辩护能力,被告人总是处于弱者地位,其权利往往有可能被公权力机关所压制甚至被剥夺。在冤假错案中往往就具有刑讯逼供等情节,这是剥夺被告人权益最严重的表现方式。并且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的地位从被侦查开始一直到审判都比较低下,其人身财产所有信息都被公权力机关所掌握,并且出庭时需要穿囚服,被警员监押。实际上这些措施从外部表象来看就已经将被告人认定为是有罪之人,社会公众对其的评价也十分消极。
总之,被告人的弱者地位可以贯穿刑事诉讼领域,所以有利于被告人的理念十分重要。
(二)有利于被告人精神的贯彻
加强对有利于被告人精神的贯彻可以解决上述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难题。首先,坚持有利于被告人精神有助于确立“罪疑从无”的入罪理念。司法机关的目标不仅在于证明被告人有罪,同时也需查明与审理被告人是否无罪,是为了追求一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公平公正的结果。法院在定罪时遇到无法查明的案件,也应当及时适用有利于被告人原则。
其次,坚持有利于被告人精神要求审慎执行认罪认罚從宽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内在精神也是有利于被告人,但是司法实践中难免会有人滥用该制度,剥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权益。此外,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从轻量刑的诱惑下,也会选择直接认罪。所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存在实际上是降低了司法机关的取证困难性。而一味追求司法效率的同时,却往往会忽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所以在执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司法机关应当从多方面多角度维护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的利益,在最大程度上保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自愿性。
最后,坚持有利于被告人精神要求审慎适用兜底条款。在运用同类解释规则的同时,也要结合基本案件事实及罪名的构成要件,在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进行适用。司法实践中也不应当滥用兜底条款,不能为了追求诉讼效率而忽视对罪名的研究[5]。
结束语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其作用和价值还未真正发挥出来。罪刑法定原则被明确规定在刑法条文中,体现了我国刑事立法的进步。但是立法的价值在于应用,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容与根本精神不应被误读,在司法实践中进行正确运用也十分重要。在近几年刑事立法的重刑化趋向下,罪刑法定原则更应当发挥其存在价值,要求司法机关对其进行真正落实与贯彻。正如学者所说,刑法基本原则的司法化能力相对不足,不仅有损刑法基本原则的法治生命力,也必然有损刑事司法实践的公正高效运行,甚至诱发适法不当、适法错误等。立法与司法的相互促进才能使罪刑法定原则得到真正落实。
参考文献
[1]陈兴良.刑法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2]施金枝.疑罪从无原则在命案办理过程中的理解和适用[J].中国检察官,2020(6):59-63.
[3]刘宪权.“疑罪从轻”是产生冤案的祸根[J].法学,2010(6):16-21.
[4]魏晓娜.冲突与融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本土化[J].中外法学,2020,32(5):1211-1230.
[5]高铭暄.刑法基本原则的司法实践与完善[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9,27(5):13-32.
作者简介:叶红霞(1981— ),女,汉族,浙江丽水人,浙江玄畅律师事务所,四级律师,本科。
研究方向:经济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