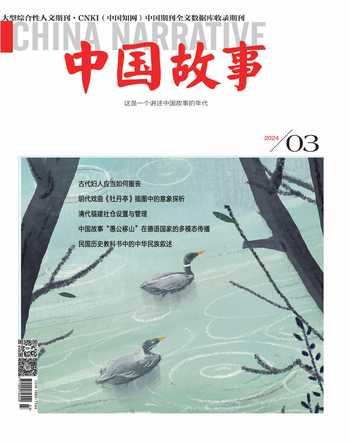从“状元入戏”管窥《西厢记》之艺术特色
赵志伟
【导读】在我国的戏曲作品中,状元戏可谓占到了很大的比例,“中状元”情节在作品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采用文献对比法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纵向分析“中状元”情节在《西厢记》演变过程中的历史变化;采用文本研读法从情节结构、人物形象、观众预期等方面,横向分析“中状元”情节在《西厢记》文本中的作用。对于把握《西厢记》的艺术特色和研究“状元入戏”这类作品有着参考意义。
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深远影响,表现出戏剧舞台艺术的完整性,达到了元代戏曲创作的最高水平。该剧讲述了书生张生和相国之女崔莺莺,在红娘的帮助下,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和现实中的种种阻碍,终成眷属的爱情故事。本文以其中的“中状元”情节作为切入点,深入探索“状元入戏”对塑造《西厢记》艺术特色的重要作用。通过研究分析,我们得以窥探“状元入戏”丰富了故事的情节,增添作品戏剧性,人物形象从粗糙勾画转向细致雕琢,不仅奠定了圆满的爱情结局,还达到了婚恋和仕途的双丰收,进而最大程度上满足了当时民众的审美需求——才子佳人大团圆。“中状元”情节作为才子佳人作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西厢记》中的“中状元”情节分析研究,以小见大,对于把握《西厢记》的艺术特色和研究“状元入戏”这类作品有着参考意义。
一、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
(一)“状元入戏”在《董西厢》中的作用萌发
在唐传奇《莺莺传》中,张生科举未中,“状元入戏”自然未发挥作用。文中讲到张生在普救寺相遇莺莺,遇兵乱救崔氏一家,对莺莺产生感情,两人在红娘的帮助下,待月西厢。张生又以“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为由离开莺莺,前往长安应试,科举未中。张生写信安慰莺莺,两人交换信物,但张生之后便断绝了与莺莺的关系,道出了莺莺是为“尤物,不妖其身,必妖于人”的论断。一年已过,张生娶了妻子,莺莺也另嫁他人。《莺莺传》的叙事结构单一,情节安排可以分为:相遇普救寺——兵围设法护卫——崔张以礼相见——张生写诗传情——崔张待月西厢——科举未中——抛弃莺莺——感情破裂。《莺莺传》讲述的是张生和莺莺的爱情悲剧故事,张生科举未中在情节结构上仅增添了悲剧色彩,并无推动作用。
到了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以下简称《董西厢》)中,一改《莺莺传》故事情节:张生和莺莺两人相见便有爱慕之情,两人在红娘的撮合下私自相会,在普救寺中张生设计相救,更是增加两人的感情,老夫人对张生大为赞许,值得注意的是老夫人的形象从此延伸而出。之后张生赴京赶考高中探花,即使如此老夫人仍再三反对,谎称张已娶他妻,崔张二人冲破封建束缚,最后以死殉情来表示反抗。《董西厢》的故事情节可总结为:相遇普救寺——解救普救寺兵围——红娘撮合待月西厢——张生赴考中探花——郑恒应婚——老夫人赖婚——崔张以死抗争——爱情圆满。
在故事结局方面,董解元一改《莺莺传》的爱情悲剧,重设崔张两人大团圆的美好结局。在“中状元”情节安排上,董解元改科举未中为高中探花,这一细微改动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两方面的改动无疑在《董西厢》的结构布局方面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中与不中发生了截然不同结果:中则喜剧,爱情圆满;不中悲剧,爱情破裂。可以说张生科举是否及第,暗喻故事结局是否圆满。
(二)“状元入戏”在《王西厢》中的作用尽显
到了王实甫的《西厢记》(以下简称《王西厢》),对于《董西厢》中张生赶考情节更是有了深入的改动,从侧面作了详细描写。如老夫人对张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我如今将莺莺于你为妻,只是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你明日便上朝取应去。我与你养着媳妇,来见我;驳落呵,休来见我。”又如在第五本开头楔子,对张生高中状元这一情节做了细致的描述:“自暮秋与小姐相别,倏经半载之际,托赖祖宗之荫,一举及第,得了头名状元。如今在客馆听候圣旨御笔除授,唯恐小姐挂念,且修书一封,令琴童家去,答知夫人,便知小生得中,以安其心。”张生赴京赶考经过了半年的时间高中状元,这一情节的交代就自然而然地满足了老夫人当初定下的要求,进而使张生成功冲破了以维护封建思想为代表的老夫人这一阻碍。
王实甫在《莺莺传》和《董西厢》的基础上补充了张生高中状元情节,并将这一情节描述得淋漓尽致,在故事情节和叙事结构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故事情节上,《董西厢》虽然加入了张生赶考这一情节,但只是一笔带过,并没有细致入微的描写;《王西厢》就将这一情节进行深入的描写,首先老夫人一方面答应过张生解救兵围后许配莺莺,另一方面顶着封建传统的思想压力反对崔张恋爱,在这两难的情况下就只能提出了让张生赶考的要求,这也就体现了“中状元”情节的合理性。其次老夫人的反对从侧面间接地推动张生赶考,体现了这一情节的必然性,也就是说张生不得不考,不考故事情节将难以进行。对穷书生身份的张生来说,参加科举考试,不仅满足了自己通过科举“兼济天下”的文人读书观,还能够迎娶莺莺,体现了這一情节的可行性。
在叙事结构上,《王西厢》一改《莺莺传》的单调结构,对《董西厢》结构进行了全面完善。结构上加入“中状元”情节,首先丰富了戏剧的矛盾冲突。由之前崔张单一的爱情矛盾提升到了张生与老夫人、莺莺、自我的多重矛盾,使戏剧产生峰回路转、跌宕起伏的效果,增强作品的可读性,使结构更加紧密紧凑,情节曲折迂回。其次为后文崔张圆满的爱情故事埋下伏笔。张生高中状元后满足了众人的要求,顺理成章地迎娶了莺莺,“中状元”情节就成了开启大团圆结局的万能钥匙。同时作者采用突转的方法,让张生在种种阻碍下高中状元,这种突转就产生了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效果,对崔张圆满爱情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二、重塑人物形象
(一)张生形象的升华
《王西厢》加入了“中状元”的情节,一改张生在《莺莺传》和《董西厢》的形象。首先张生在《莺莺传》中的形象是被贬低甚至丑化的。当张生遇到莺莺时,竟是因为莺莺长得“颜色艳异,光辉动人”的美貌,可见张生的贪色;张生在赴京参加科举未中后,收到了莺莺的凄婉回信,在朋友打听时竟然将莺莺称为“尤物”,认为莺莺“不妖其人,必妖于人”,从这样的评价可以看到张生的薄情寡义;当莺莺另嫁他人、张生另娶她人时,张生仍对莺莺心有余恋,可见张生情感不一。其中张生参加科举的结果是未中,那么在他的形象塑造上无疑是一缺点,突出了他的情薄才疏。
其次张生在《董西厢》中的形象是被赞扬和美化的。当张生第一次遇见莺莺回到住处时就寝食难安,甚至在穿衣服时颠倒正反不知所措,可见张生的痴情;兵围普救寺时张生义不容辞、自告奋勇提出退兵之策,为的就是在崔家面前有所表现并得到肯定,可见张生的多情;后来张生为了爱情竟然得了相思病,茶饭不思,可见张生的专情;在张生高中探花郎之后并没有抛弃莺莺仍然爱着她,可见张生的重情;当老夫人答应张生后又听信郑恒的话进行赖婚时,张生又选择以死相逼,足见张生坚贞不渝的爱情观。其中《董西厢》加入了张生高中探花郎这个情节,改变了传统的书生高中功名后就抛弃妻子、爱人的负心汉形象,无形中提升张生的坚守爱情的形象。
《王西厢》继承了张生在《董西厢》中的形象并有所发展。在《董西厢》中张生为了爱情悬梁自尽,以死相逼;而在《王西厢》中的张生能够和老夫人当面理论:“那一个贼畜生行嫉妒,走将来老夫人行厮问阻?”相比较而言,张生更多了一份君子形象。在《王西厢》开头,张生面对莺莺的婢女红娘时,就自报家门,以至于红娘向莺莺说:“天下有这等傻角。”增添了张生傻里傻气的形象。这里重点说明一下加入张生高中状元情节对其形象的作用:王实甫将《董西厢》中张生高中的名次“探花”提升为“状元”,增加了科举难度,暗示了张生具有更高的文化素养。张生在参加科举前抱定了决心:“小生这一去,白夺一个状元。正是:‘青霄有路终须到,金榜无名誓不归。”可见张生对科举考试的壮志雄心、志在必得以及对那份爱情的坚守。当张生高中状元后,那个之前一心求爱的青年读书人形象就过渡到了一位以步入仕途的成功人士形象。
综上所述,《董西厢》一改《莺莺传》中张生科举未中的情节为张生高中探花郎,这一改动提高了张生的身份地位,提升了张生的人物形象。王实甫在两者的基础上,将这一情节作了详细描写,层层递进地升华了张生的形象:从《莺莺传》中张生科举未中,体现了张生的才疏;到《董西厢》中张生高中探花,体现了张生的才高;再到《王西厢》中张生高中状元,体现了张生的才广。
(二)老夫人形象的立体
老夫人的形象在《西厢记》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老夫人身份的设定本身就代表了封建传统思想,她和张生的矛盾冲突就展现了两者在不同利益下的形象。“中状元”情节的加入,不仅加深了老夫人和张生的矛盾,还放大了老夫人代表封建传统利益下的形象。在《莺莺传》中仅简单描述了张生科举未中的情况:“明年,文战不胜,张遂止于京。”并没有关于老夫人的描写。到了《董西厢》中当“张珙廷试,第三人及第”后张生又回到崔家,老夫人亲问道:“张郎在客可煞辛苦?相见彼中把名姓等?几日试来那几日唱名?得意那不得意?有何传示、有何书信?”其中“把名姓等”的意思是指等候考试名单的公布,可见老夫人对张生参加科举这一行动是比较关心和重视的。当莺莺读出书信中的要旨“探花郎,第三也”时,老夫人和下人全部皆大欢喜。这一情节深刻体现出了老夫人是十分重视科举功名的,同时也是维护封建专制制度下婚恋关系的形象代表。
再到《王西厢》,王实甫对张生中状元前后都有详细的描写。在第四本第三折中,张生未参加科举时,老夫人与张生座谈中讲道:“张生,你向前来,是自家亲眷,不要回避。俺今日将莺莺与你,到京师休辱末了俺孩儿,挣揣一个状元回来者。”一方面,老夫人与张生以“家眷”相称,并鼓励张生去参加科举,可见老夫人对张生是看好的,并没有《董西厢》中的固执,反而在封建传统思想下有了让步。
另一方面,在科举文化繁荣的背景下,老夫人又是维护封建传统制度的代表,科举中第自然是挑选女婿的重要要求之一,同时作为相国之女的莺莺,身份地位自然是很高的,在特别讲究门当户对的封建大家庭中,就必须要求张生提高自己的身份地位——考取状元,才能满足老夫人的要求,符合封建传统观念。当张生考取状元后,老夫人的态度自然是“好生欢喜”,对待前来报喜的琴童更是嘘寒问暖,嘱托带好行李通知张生赶紧回来。可见老夫人在张生高中状元后相比前面作品中的形象显得更加虚伪、附和。
总之,王实甫在《西厢记》中加入“中状元”情节时,详细描写了老夫人在张生中状元前后的情态变化:中状元前:冷漠、严肃、顽固;中状元后:欢喜、恭维、附和。相对《董西厢》中的听信谗言、却未逼试的老夫人形象,《王西厢》里面的老夫人形象更增添了专制、无情、权术,突出了老夫人在封建传统思想下的固执和对功名利禄的追求,对老夫人这一鲜明形象的刻画在此发挥得淋漓尽致。
(三)莺莺形象的丰满
在《董西厢》中,张生与莺莺分别进京赶考时,莺莺嘱咐道:“……少饮酒,省游戏,记取奴言语,必登高第。专听着伊家,好消好息;专等着伊家,宝冠霞帔。” “必登高第”可见莺莺渴望张生科舉中第,取得功名。在莺莺还未知道张生考取功名时:“莺未知郎第,荏苒成疾。”可见莺莺对张生仕途的担忧。当莺莺得知张生考取“探花郎”时,“夫人以下皆喜……莺修书密遣仆寄生……”可见莺莺对张生科举中第后的激动喜悦。
到了《王西厢》,莺莺对科举和爱情的态度则是爱情第一,科举第二。在莺莺送别张生前往科举的路上时交代道:“你与俺崔相国做女婿,妻荣夫贵,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并头莲”又叫并蒂莲,并排地长在同一茎上的两朵莲花,这里用作比喻恩爱的夫妻)王实甫将“夫荣妻贵”反用为“妻荣夫贵”,并以莺莺之口说出,意为张生已是崔家相国的女婿,身份和地位都十分显赫,只要两人团圆,强过科举功名,借此表现莺莺重感情、轻功名。当莺莺得知张生高中状元后,只是让琴童带去信物,并指明含义:裹肚——守在左右,系在心头;袜儿——管着不胡行乱走;琴——感情的见证;玉簪——不要把情抛在脑后。相比较《董西厢》,《王西厢》中的莺莺得知喜讯后并没有高兴起来,而是更加担心自己的爱情,怕张生科举及第后抛弃自己,也体现出了莺莺对功名的轻视,对爱情的重视。
总而言之,《王西厢》中的莺莺形象在《董西厢》的基础上有了新的拔高:在对待爱情和功名的态度上,莺莺轻功名重爱情,更加符合了其人物性格,同时又体现出了莺莺在封建专制思想下追求爱情的叛逆精神。
三、符合当时社会的审美取向
(一)符合科举文化下的文人心态
在元代科举制度文化的影响下,剧作家把科举考试理想化,作品中的主人翁在前往科举考试的过程中往往高中功名而归,取得的考试成绩自然是非常好的,或状元,或探花。但在现实历代科举考试中,考试难度是巨大的,应试者往往落第而归,更不必说在蒙元统治下的环境中。
首先,科举制度在元朝实行时间短。蒙古族作为“马背上的民族”,主要以游牧生活为主,区别于农耕文明的中原地区,从元成祖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政权,在灭掉金朝时,才开始采用科举考试制度,但仅适用于淮河以北的汉地,之后很快这一制度就被废除。到忽必烈建立元朝,文人开始呼吁恢复科举制度,但元代统治者为了维护本民族的利益,对科举制度的态度一直是消极的。从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到元朝被灭,共162年,其中科举制仅实行了45年(1315-1336年,1342-1366年),时间很短。其次,蒙古族尚武轻文。蒙古人在游牧生活的影响下,熟练马术,蒙古族就是在这样的优势条件下用武力一统天下,自然轻视农耕、轻视文治。那么在科举制度的运行过程中,就仅限于文职人员。最后,在蒙古族的统治下,元朝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将民族划为三六九等:蒙古族为第一等;色目人为第二等;汉人为第三等;南人为第四等。科举入仕的条件也是按照这一等级制度排列,且规定不能越级考试。在等级制度的限制下,科举制度就不能全面发挥公平选举人才的作用。
总之,元代的科举制度具有实行时间短、适用范围小、等级限制大的特点。元代文人(尤其受前代科举文化影响下的读书人)在这样的统治环境下,对唐宋统治下繁荣的科举文化充满了怀念和向往,但在元代蒙古人的统治下,文人壮志难酬,对森严的等级制度和科举制度充满了无奈和失望,当这条能够通过科举改变命运更替社会等级的道路被堵死后,文人那种难以平复的心理就只有通过作品来表达。王实甫就是在上述情况下,在《西厢记》中增加了“中状元”情节,这一情节的加入符合了当时的文人心态,将自身的理想寄托在作品中的人物身上,张生高中状元无疑代表了这些文人的科举愿望。这么来看,张生参加科举高中状元也就显得合情合理。
(二)深化观众预期下的大团圆结局
1.改变人物命运和故事结局
通过三部作品的对比,可以明显发现它们各自的人物命运和故事结局:《莺莺传》——科举未中——离别;《董西厢》——高中探花——大团圆;《王西厢》——高中状元——大团圆。可见人物命运的设定和故事结局有着一定的关系, 在《莺莺传》中作者将张生的命运设定为科举未中,也正是如此张生选择了留在京中,《莺莺传》中这样描写道:“明年,文战不胜,张遂止于京。因赠书于崔,以广其意。”可以说张生科举未中就决定了崔、张的爱情是无缘的,也是无果的。《董西厢》一改张生科举未中情节,增添了科举及第的情节,人物命运设置上,张生得了第三名的探花郎,这样就在莺莺的激励作用下,满足了以封建礼教为代表的老夫人的严格要求,科举及第就成了崔张婚恋走向成功的重要因素,甚至决定了崔张婚恋走向成功。
在《王西厢》中作者同样将张生的命运设置为科举及第,不同于《董西厢》的是,将第三名的探花提升为了第一名的狀元,这一细节的改动在提升了科举难度的同时也为崔张婚恋走向成功注入了积极因素,当张生高中状元后身份地位便得到了迅速提升。虽然在后面还有一些阻碍,但不得不说“中状元”情节的加入成为崔张婚恋走向成功的催化剂。在《莺莺传》中科举落第是崔张婚恋的主要矛盾,但在《王西厢》中以老夫人为代表的封建势力成了崔张婚恋的主要矛盾,而张生高中状元无疑给崔张才子佳人的大团圆结局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2.符合各层观众预期,引起共鸣
首先,“状元入戏”下的团圆结局符合当时环境下戏剧作品的结局模式。据有关学者统计发现:元代以前悲剧结局作品比重明显高于大团圆结局作品,越靠近元代,大团圆结局作品的比重越来越高,到了元代,大团圆结局的作品达到了90%以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王实甫加入“中状元”情节,促进崔张两人走向大团圆的设计也就不足为奇。
其次,“状元入戏”符合元代下层观众的审美心理。在元代蒙古人的统治下,强烈的民族歧视政策,使得下层民众生活苦不堪言。关汉卿的《窦娥冤》就描绘了在元代统治下,下层人民任人宰割有苦无处诉的悲惨故事。下层人民就是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对现实生活充满了无奈和失望,从而寄托于戏剧作品,希望美好的才子佳人故事能够在戏剧中体现。而元代的戏剧作家就抓住了民众这样的心理,对作品进行了再创作,以符合民众的愿望。
第三,“状元入戏”下的团圆结局符合统治阶级的审美需求。在由蒙古族统治的元代,元杂剧就在无形中受到了蒙古族文化习俗的影响。学者高红梅认为“元杂剧绝大多数都是以大团圆的喜剧结局的,这与蒙古民族独特的喜剧意识不无关系”,蒙古民族作为游牧民族,经常征战在外,对于家庭的团圆就显得十分珍惜和重视。
最后,蒙古族还有英雄崇拜的风俗习惯。在我国,表现蒙古族英雄史诗的作品就有上百部,最具代表性的《江格尔》就讲述了蒙古勇士同凶残的敌人作斗争,保卫家园的故事。在这一习俗的影响下,作品中的主人翁就充满了英雄色彩,王实甫增添“中状元”情节,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张生的英雄色彩。此外,在元代的高压政策下,作者将“科举未中”改为“科举及第”,进而改悲剧结局为团圆结局,也是为了迎合统治者,美化元代统治下的社会现实。
四、结语
通过研究分析,我们得以窥探“状元入戏”丰富了故事的情节,增添作品戏剧性,人物形象从粗糙勾画转向细致雕琢,不仅奠定了圆满的爱情结局,还达到了婚恋和仕途的双丰收,进而最大程度上满足了当时民众的审美需求——才子佳人大团圆。可以说,“中状元”情节看似平平无奇,而正是此情节将《西厢记》的艺术特色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1] 汪辟疆. 唐人小说[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 (元)王实甫. 西厢记[M]. 王季思,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 孙逊. 董西厢和王西厢[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4] (元)王实甫. 西厢记[M]. 张燕瑾,解读.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
[5] 凌景埏. 董解元西厢记[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6] 徐黎丽. 略论元代科举制度的特点[J]. 西北师大学报,1998(2).
[7] 葛琦. 元杂剧大团圆结局成因研究评述[J]. 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12(1).
[8] 高红梅. 蒙古民俗文化影响下的元杂剧的特征[J].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1(2).
[9] 张萌. 明代状元产生因素与仕途研究[D]. 辽宁大学,2021.
[10] 韩晓. 明代科举与激励状元戏研究[D]. 山西师范大学,2020.
[11] 程晓清. 清代状元戏研究[D]. 广西大学,2015.
[12] 李世珍. 明代江西状元研究[D]. 南昌大学,2013.
[13] 马露瑶. 明传奇“中状元”母题研究[D]. 河南大学,2013.
[14] 魏运生. 清代徽州迁苏状元家族研究[D]. 上海师范大学,2010.
[15] 孙仁义. 浅析京剧等状元戏中的科举影像[J]. 运城学院学报,2011(3).
[16] 王颖. 略论元杂剧中的科举考试[J]. 辽宁大学学报,19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