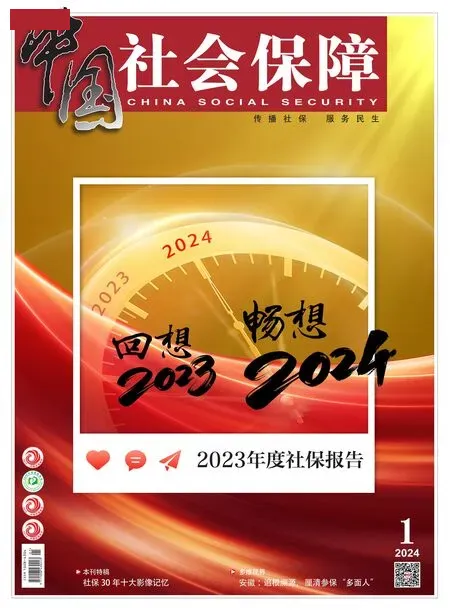数字技术浪潮下的劳动保障问题及应对
■文/王天玉
数字技术升级改变了传统就业形态,并不断拓展新的服务领域。基于网络会议和社交软件的远程劳动改变了常规劳动的场景,构造了线上和线下两套工作体系;平台用工也已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日渐成为就业主渠道之一。在人们因技术进步而享受到效率提升和服务便捷的同时,新型劳动权益保障问题日益凸显。本文分析劳动形态变革产生的新特征,以及现行劳动保障制度的短板和滞后,展望未来劳动规范治理的发展方向和要点。
数字时代下劳动形态呈现新特征
劳动灵活化突破了单位制的时间控制。灵活化及其内含的自主性是新就业形态区别于单位制从属性劳动的显著特征,实践表现通常是以灵活就业方式参与平台用工的从业者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工作,以及何时何地工作。用人单位通过工作时间控制所确立的劳动指挥、管理、惩戒等一系列权利,在数字时代劳动形态变革中被率先消解,基于用人单位组织体的社会主流就业结构也受到冲击,代之而起的是行业化、规模化的平台灵活就业以及平台在该体系中的新兴权利。时间是劳动的基本物理维度,工作时间的控制是认定劳动形态的特征之一,数字时代劳动变革以灵活化的表现形式重新塑造了劳动供需交易中的权利结构,形成了新的劳动特征。
劳动远程化突破了单位制的场所控制。学界关于远程劳动的研究基本沿用了劳动关系的分析框架,即将远程劳动设定为劳动关系下的劳动者在用人单位场所外工作的状态。由于劳动者脱离了工作场所,用人单位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手段发生改变,由此催生了区别于常规标准就业的灵活性。劳动关系下的远程劳动仅是劳动远程化的一种形式,应围绕远程化这一劳动场所因素的改变区分两种情形,一种是突破用人单位场所限制的远程化,也就是劳动关系下劳动合同履行地不限于工作场所;另一种是突破劳务供需匹配地理限制的远程化,劳务供需双方依托平台实现线上工作成果的缔约与交付。远程劳动所不能去除的是组织要素,只要组织要素是劳动的主导就必然要施加场所和时间控制。如果当前在劳动关系下以远程劳动方式工作的劳动者,能够去除组织要素,不要求紧密的团队协作,工作内容转变为特定任务,就可能发生所谓“去劳动关系化”的结果。基于技术对劳动者个体赋能以及平台劳务供需匹配机制改进的趋势,劳动关系下的劳动过程远程化将不断转变为平台式的工作成果交付远程化。据此,劳动关系下的远程劳动只是劳动远程化随技术发展的一种过渡形态。
劳动原子化突破了单位制的组织控制。当前典型平台服务项目主要由个体从业者独立完成,劳动技能要求较低。平台通过算法引导和信用担保充当了事实上的辅助者,使得劳务活动的个人属性更为凸显,可以形容为“平台中心化、个体原子化”。劳动原子化使得提供劳务及其他类型社会服务的人力单元越来越小,乃至于大量实际劳动是由个人完成的,不需要与其他人进行协作配合,事实上剥离了以往必须借助劳动组织才能实现的集体合力。劳动原子化之所以能够发生,关键原因是平台通过网络技术、数据支持和信用背书等实现对从业者尤其是灵活就业人员的赋能,使得从业者能够以个体身份对接劳务需求市场并实现快速匹配,并在平台身份验证和安全监控的保障下顺畅完成服务过程或交付工作成果。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下,从业者脱离单位制劳动组织的支持后仍有能力完成特定任务,由此突破了组织控制。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产生的原因
现行劳动法是工业化的产物,对劳动关系中用工一方有明确的组织性要求,也是用人单位作为劳动关系当事人的内在属性。《劳动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以组织体为标准对用人单位设定了组织体要件,最低限度是个体经济组织,自然人不能成为劳动关系上的用工一方。一个完整的团体性劳动过程可表现为用人单位招聘和劳动合同订立、履行、变更、终止或解除。正是基于团体性劳动这一逻辑,单位制组织体才发展出劳动纪律、管理规程等,对团体协作实施有效的组织和控制。
然而,新就业形态不再以固定时间、场所的人力集中与分工产生工作成果和社会服务,而是以动态变化的灵活就业方式实现大规模的个体分散劳动。所谓个体性劳动是指有劳动能力的自然人个体通过互联网平台承接工作任务,在网络和数据技术支持下,独立或主要依靠自身完成特定劳务的活动。个体性劳动打破了自然人只能依托组织体就业以获得团体赋能的单一、主流就业渠道,在组织体之外通过便捷、低价、高速接入移动互联网的方式获得了平台的技术支持,自然人能够独立地参与到网络化的社会分工体系中,并在服务评价体系下日益凸显劳动的个人化特征。
同时,社会分工单元从组织体解构为自然人个体或松散的自然人合作体。除网约车、外卖、即时配送、家政等基本由从业者个人完成的平台运营模式之外,网络主播、视频制作者等亦会根据工作需要获得他人辅助,但以临时性合作为主,较少形成长期独占劳动的结合关系,此为个体性劳动下从业者主要依靠自身并与他人形成松散合作体。此类松散合作体相对于单位制组织体具有高流动性和低成本的特点,因此很难转化为用人单位形式的社会分工单元。据此,松散的自然人合作体既不是单位制组织体的雏形,也不是个体性劳动与团体性劳动之间的过渡状态,而是一种个体性劳动的衍生形式。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对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3391号 (社会管理类287 号)提案的答复》(以下简称《答复》)指出,新就业形态人员大多通过平台自主接单承接工作任务,准入和退出门槛低,工作时间相对自由,劳动所得从消费者支付的费用中直接分成,其与平台的关系有别于传统的“企业+雇员”模式,导致新就业形态人员难以纳入现行的劳动法律法规保障范围。在数字技术蓬勃发展的浪潮之下,法律需要超越组织体下劳动控制与从属的认识局限,正视个体在技术赋能下通过网络平台直接参与社会服务,承认个体在劳动过程中的自主安排与差异性,不再强行将已经灵活化、远程化和原子化的个体统一到时间控制、场所控制和组织控制中。
如何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八部门于2021 年7 月16 日联合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在现行“劳动关系—民事关系”的“二分法”之外提出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的情形”,开拓了“第三类劳动形态”的制度空间。数字时代劳动权益保障应着眼于“新业态劳动权益清单”,建构基于劳动基准的底线保障,并随着技术发展和行业演进增设权益规范。当前,劳动基准制度建设应从以下3 个方面发力:
第一,规范平台定价权,合理确定平台任务单价和抽成比例,形成良性的利益分配格局。平台企业在平台内拥有绝对的定价权,其他市场参与者没有与平台进行议价的能力。因此,应围绕任务化订单定价来设计最低工资标准,以从业者接到某一订单为起点计算该订单完成的总收入与总时间之比。在确定强制性最低工资标准基础上,着眼于长期的劳动定价机制,应通过集体协商等方式建立行业性、区域性平台用工价格调整机制,根据行业发展动态提升任务单价。
第二,控制劳动强度和工作总量,防范过度劳动及其衍生的外部风险,积极探索新业态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平台有能力依托大数据测算完成单个任务的一般性劳动强度,据此建立任务总量及劳动强度的梯度控制和提醒制度,并进行多平台就业情形下的工作总量弹性控制。通过引导从业者建立理性的收入预期、限定大型平台的任务连续性及总量,将多平台就业的工作总量控制在一个相对合理的区间内。同时,以出行、外卖、即时配送、同城货运等行业为重点,扩大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采取政府主导、信息化引领和社会力量承办相结合的方式,建立健全职业伤害保障管理服务规范和运行机制。鼓励平台企业通过购买人身意外、雇主责任等商业保险,提升平台灵活就业人员保障水平。
第三,建立算法知情与集体同意规则,推进工会组织维权工作覆盖数字领域。在平台算法治理方面,新就业形态算法规则应在公开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透明度,将算法公开与平台解释义务整合为算法知情,并将算法解释设定为平台义务,平台须按照《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中关于算法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原则向社会公众作出解释。算法在用工领域的影响具有群体性,甚至超越具体的法律关系,对参与用工的各类劳务提供者产生大致相同的效果。我国于2021 年12 月修订《工会法》,明确了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不以劳动关系为前提,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集体协商机制,在个人算法知情权的基础上建立从业者集体的知情与协商权利,且只有经过协商才能以书面形式证明达成集体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