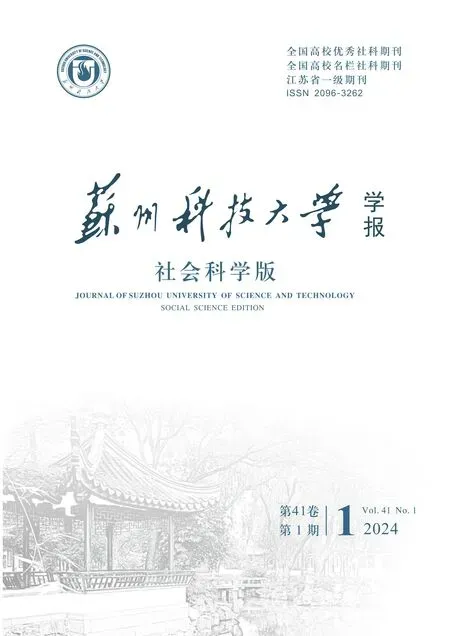战后延安文艺精神在上海的迂回传播(1945—1949)*
黄思颖
(中国民航大学 乘务学院,天津 300110)
抗日战争结束后,上海由国民党接管。“日本一投降,国民党即派员接收各种文化设施,颁布所谓《管理收复区报纸、通讯社、杂志、电影、广播事业暂行办法》,设立机构并利用它手中掌握的特权,竭力控制上海的文化、舆论阵地”[1]4,并多次发布禁止进步报刊、书籍发行以及管制进步戏剧的文件[1]705-729。上海再一次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也成为国共两党争夺文艺舆论宣传的据点。[2]虽然和平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但内战还是终究打响,国民党倒行逆施,逐渐失去人心。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推进与共产党的接连胜利,中共慢慢加强对文艺领导权的争夺,尤其是对“中间状态”的自由知识分子的争取、教育和改造。于是,延安文艺精神及解放区的文学从重庆等大后方传入上海。这是一种迂回传播。在这种隐形的传播方式及宣传下,上海的文化人尤其是“中间状态”的自由知识分子渐渐感知到中共文艺领导的“教育”和“压力”。面临新的历史环境,他们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一、延安文艺思想对“中间”文艺刊物的渗透:以《文艺复兴》为例
《文艺复兴》是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影响颇为广泛的大型文艺刊物之一,创办者是郑振铎。在1946年1月10日创刊号的《发刊词》上,郑振铎写道:“我们不仅要承继了五四运动以来未完的工作,我们还应该更积极的努力于今后的文艺复兴的使命;我们不仅为了写作而写作,我们还觉得应该配合着整个新的中国的动向,为民主,绝大多数的民众而写作。”[3]6因而,《文艺复兴》的文学理念是对“五四”时期“民主”“启蒙”传统的延续,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而工作,为民主的实现而工作”[3]7的名义下,秉持着“兼容并蓄”的风格。不少研究者都注意到《文艺复兴》这种“包罗万象”的编辑理念,认为这是一种区别于“流派意识”的“园地意识”。如认为“《文艺复兴》是一份颇具包容性的刊物。像郑振铎主编的一系列著名文学期刊一样,它的意图,不在造成文学流派,而在为新文学发展开辟园地。这种有别于流派意识的园地意识,是现代文学期刊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4]。不过仍有一些研究者看到了“中间”刊物《文艺复兴》逐渐受到中共文艺思想规约的趋势,认为《文艺复兴》的转向与结局“是战后广大民主主义文学活动的一个缩影”,他们的文学理念势必会受到左翼阵营的影响与教育,在被改造之后“方能得到延安文艺权威的接纳,融入新中国文艺一体化的‘大军’”[5]。此外,还有研究者通过刊物后期在《编余》中对作品“艺术/知识性”频繁强调背后的动因考察出,这是刊物主编在面临“延安文艺”思想改造时造成的精神危机,这种“普遍的精神危机,正是杂志《编余》中‘焦点的转移’的现实背景。一边是不可抵抗的改造话语,一边是无法磨灭的精神底色。历史情境的遽变迫使他们做出改变,纾解自身的‘撕裂’之感。于是,从现实批判内转,强调作品的‘知识/艺术性’便成为他们的解决之道”[6]。
《文艺复兴》刊载的多数文艺作品确实与中共革命的、大众的文艺路线有一定距离。尽管它也发表了丁玲等解放区作家的作品,但所占比例不大,多数还是以“艺术”“审美”为原则的小说、诗歌与散文。但是《文艺复兴》无法完全避免左翼文艺理论的规制和渗透。在1946年1月10日的创刊号上,《文艺复兴》刊载了刘西渭关于茅盾《清明前后》的书评。早在20世纪30年代,李健吾便以“刘西渭”的笔名创作了一系列书评,多数发表在《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上,逐渐形成自己的批评理念。他曾在1936年出版的《咀华集》跋文中阐述了自己对于批评活动的认识:“批评的成就是自我的发见和价值的决定。发见自我就得周密,决定价值就得综合。一个批评家是学者和艺术家的化合,有颗创造的心灵运用死的知识。他的野心在扩大他的人格,增深他的认识,提高他的鉴赏,完成他的理论。”[7]他一直秉持着“印象主义”的批评原则,在个人审美的基础上漫谈感悟、进行点评,没有统一的文艺理论支撑,点评之处完全是个人当下的感受与心得。在这则书评里,刘西渭却运用了“社会批评”的方法,对茅盾的《清明前后》大加赞扬且肯定了它的社会价值,认为它同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曹禺的《蜕变》一样是“时代的反映”,是“一面明照万里的镜子”:“以一种科学的自然的方式去看。科学,让我重复一遍这两个字,科学。他看见的不止于平面,不止于隔离,不是一个意境,不像矿石一样死,湖水一样平,而是一个有机的生命的构成。他对于社会的看法不是传奇式的故事的猎取。牵一发而动全局。他从四面八方写,他从细微处写,他不嫌猥琐,他不是行舟,他在造山——什么样的山,心理的,社会的,峰峦迭起,互有影响。”[8]《清明前后》书评的表述依然是三十年代“刘西渭式”的文字,可是观照事物的角度发生了变化,他从时代、社会的层面来衡量《清明前后》的价值,这对于长期以“艺术直觉”来评价文本的刘西渭不可谓不是一个转向,而这转向的背后也暗含了深刻的政治缘由。1945年11月10日,重庆《新华日报》副刊室召开关于《清明前后》和《芳草天涯》两个话剧的座谈会。这是中共中央派遣胡乔木、何其芳等人来重庆传达延安整风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精神的一个重要举措,会议中胡乔木化身“C君”对两个剧本进行指向性总结,基本肯定了《清明前后》的社会意义,否定了《芳草天涯》的“非政治倾向”。(1)C君首先否定了《清明前后》是“标语口号”作品,然后讨论整个戏剧的“大方向”:“今天后方所要反对的主要倾向,究竟是标语口号的倾向还是非政治的倾向?有人以为主要的倾向是标语口号,公式主义,我认为这种批评本身,就正是一种标语口号或公式主义的批评,因为它只知道反公式主义的公式,而不知道今天严重地普遍地泛滥于文艺界的倾向,乃是更有害的非政治的倾向……假如说《清明前后》是公式主义,我们宁可多有一些这种所谓‘公式主义’,而不愿有所谓‘非公式主义’的《芳草天涯》或其它莫名其妙的让人糊涂而不让人清醒的东西。”他又评价《芳草天涯》:“这个剧中的感情便是接近那不值得宣传的一种。有人或者说这就是刻划这种不能解决的人间悲剧或知识分子弱点的作品,我不敢同意这个说法。人间‘最大的悲剧’既不是所谓‘床笫间的悲剧’,而知识分子之表现为‘弱者’的地方,也不在‘床笫间’,而是在社会斗争中间。可以说,《芳草天涯》正是一个非政治倾向的作品,和《清明前后》恰成对照。”(《〈清明前后〉与〈芳草天涯〉两个话剧的座谈》,《新华日报》1945年11月28日)而刘西渭在此时做出与座谈会同样的判断,并写成书评发表在《文艺复兴》上,与战后大后方国统区在延安文艺精神下进行“内部整肃”形成呼应。
此后,1946年6月第5期的《文艺复兴》又刊载了梅林的重庆文艺界“抗战八年文艺检讨座谈会”的记录稿。这个座谈会于1946年4月22日由“文联社”留渝的工作人员组织举行。会议上,艾芜、臧克家、阳翰笙、杨晦分别就抗战期间的小说、诗歌、戏剧、文艺理论的得失进行了汇报,此后,大家又对今后文艺的形式与内容向何种方向开拓进行了讨论。与会的大多数作家都认为应当加强文艺的“政治性”,切实实行“文艺大众化”,创作与人民结合的“人民文艺”。[9]可以说,这正是《讲话》在国统区内部的深层讨论。如此重要的座谈会纪要没有发表在重庆任何一个中共的机关刊物上,而是发表在上海具有“中间色彩”“兼容并蓄”的《文艺复兴》上,更加表明中共领导人在重庆等大后方进行“文学清理”的同时也进而向上海推进的愿望,而《文艺复兴》以及与之相关的文艺作者正是中共所要争取的对象。其实,在重庆进行“文艺检讨”后的两个月内,上海文艺界也顺势展开了讨论。1946年6月17日,《上海文化》杂志社举办“战时战后文艺检讨座谈会”,《文艺复兴》的两个主要创办者李健吾和郑振铎都受邀参加,会上二人分别总结了沦陷时期上海的文化状况。而会议结束前,郭沫若专门对今后文艺工作者的努力方向提出意见。他指出:“为了配合当前的客观形势和要求,今后的文艺作品,应强调其政治意味,这是无容多说的。文艺作品的主要条件有二:第一为对象,即为谁写;第二为题材,即写什么。关于第一点,即对象问题。在目前情形下,由于客观环境及知识程度的限制,我们不可能以广大人民大众为对象,所以还是应该以大部份(分)的知识青年为对象。关于第二点,即题材问题,当前的政治现实,就是最好的题材。至于上海的作家,更可以就地取材,例如官商勾结的米粮操纵问题,民族资本的破产问题,美国货的大量进口问题等。”[10]这其实是《讲话》的一种因地制宜的表达。在上海特殊的环境下,文艺无法完全为工农兵而作,因作家们没有实际体验,无法真切创作关于工农兵的故事。郭沫若虽然看似将“对象”和“内容”都作了调整,但根本上还是延续了《讲话》的“客观主义”与“现实主义”精神,以及“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原则,要求文艺应当真实反映当下政治现状,与现实生活的实际斗争相结合。
在“战时战后文艺检讨座谈会”三个月后,1946年9月,《文艺复兴》又登载了徐迟的《从重庆带回来的问题》。徐迟于这一年3月从重庆回到上海,经历了六个月的“再教育”(2)徐迟在《田园将芜胡不归——再教育之一章》中写道:“(到上海)第三天起我就感到了忧郁,激愤,叹息着自己的空虚,我开始摸索,竟一直摸索了六个月之久。”(王凤伯、孙露茜《徐迟研究专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1页)在回顾自己的文学之路时,徐迟说:“我在我好姐那栋华厦中连续地住了六个月。这是中国近代史中最令人困惑,最矛盾,最忐忑的六个月。……这六个月的路程和经历,我自己称之为‘自我的再教育’。”(徐迟《我的文学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440页)徐迟感到“忧郁”“矛盾”,是因为在大后方文艺“规范”影响下形成的“自我规诫”与“消费”“奢侈”“海派文化”充斥的上海产生“冲撞”,于是一种“道德的自律”使他对上海的文艺界提出自己的意见。和思想的“冲撞”。他说:“从重庆回到上海之后,似乎感到这样的一种不同,我们在重庆所考虑的问题,在这里并未被考虑。生活都有了改变了,然而思想究竟是不能够突然中断的。”[11]187这个“不能中断的思想”便是徐迟在重庆时期进行的对文艺问题的思考和讨论,实际也就是延安文艺精神对大后方进步文艺界的“教育”,而徐迟在重庆无疑是“被教育”的对象。早在重庆文艺界展开对《清明前后》和《芳草天涯》讨论的时候,徐迟在1946年1月2日的《新华日报》上发表《在泥沼中——向文艺界的朋友们和读者贺新年》一文,他认为茅盾的《清明前后》是主题先行的产物,当抽象的思想先于生活而存在,创作使生活努力靠近思想的时候,写出来的东西也终究是有“限度”的,进而他提出,创作应当从“愿意”出发而不是从“应该”出发。[12]文章引来了从延安至重庆的何其芳的批评。(3)何其芳在1946年2月13日《新华日报》上发表《关于现实主义》一文,对徐迟的观点作了全面的批评,并阐述了自己关于“愿意”与“应该”的观点:“我们的创作过程是否就这样干脆地分为两类,不是从‘愿意’与‘生活’(或者‘搏斗’)出发,就是从‘应该’与‘概念’出发?我觉得并不这样简单。”而徐迟在经历了如此的“教育”与在上海所见所闻的思考之后,转变了自己此前的思想。在《从重庆带回来的问题》中,他提出作家所要创作的“必需的艺术”,应该是“争取民主”“反特务”“关乎生存”的,而不是“奢靡”的海派艺术与文化。[11]187-188实际上,“民主与生存”的“必须艺术”又何尝不是一种“主题先行”的表达。进而,徐迟顺势指出:“要把大部份(分)的奢侈品的创造转化为必需品的艺术的创造,先要寻求‘为什么人?’的解决。”[11]188他引用了《文艺问题》(4)徐迟在《重庆回忆》一文中叙述:“记得是在一九四四年里,却不记得是在哪一个季节了,一本小册子开始传出。那是一本三十二开,三十页左右,用黄色土纸印刷的薄本子。一张白矾纸作封面,上写《文艺问题》四个毛笔字。那就是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大后方的初版本。”(王凤伯、孙露茜《徐迟研究专集》,第32页)中的论述:“我们的文艺第一为着工农兵,第二才是为着小资产阶级。”[11]188面对上海的文艺情况,徐迟有力地揭示道:“我们会发现的,在昨天的大后方,今日的上海这一带,为小资产阶级的文艺都已提到第一位去了。我们是否仅把工农兵的读物降到第二位呢?我们根本没有工农兵的读物。我们根本抹杀了工农兵要求读物这件事。”[11]189徐迟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作为重点,即使已经“写不下去”,也仍旧在不断地重复强调。这实际上是将《讲话》的核心内容通过《文艺复兴》反复转述,从而达到强化的效果,说明延安文艺精神已经从重庆等大后方向上海进行着“潜移默化”而又“强势”地推进。
综上可知,左翼文学界在战后大后方进行的每一次重要的文艺活动,基本会在上海形成影响与反映,而《文艺复兴》的上述文章以及在上海召开的关于“文艺检讨”的座谈会便是延安文艺精神向上海迂回传播的一种方式。郭沫若、夏衍以及接受过“教育”和“改造”的徐迟等人从大后方来到上海,也为对上海的作家进行“教育”提供了条件,郭沫若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无疑是此“教育”的一次“预演”。
二、左翼文学界对上海进步作家的批评与团结
徐迟在《从重庆带回来的问题》里说道:“‘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纷(分)歧,对立,不团结并不在这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无原则的问题上。’这句,可谓绘声绘影,道破了曾经在大后方发生的理论纷争,可能也道破了将在上海一带发生的若干理论纷争。”[11]188在徐迟的想象中,战后在重庆等大后方上演的一系列“文艺为什么人而作”的理论纷争终将会在上海上演,而事实确也证明了徐迟“断言”的正确性。
1946年12月13日在《新民报(晚刊)·夜光杯》上刊载了署名“莫名奇”的《刻画着梦的时刻——评巴金先生的〈长夜〉》,文章指责了“说梦的文章”以及此类文章中“虚无缥缈”的情绪,并且指名道姓地对巴金提出批评,认为巴金是这种“新伤感主义”作家的代表:“为什么以名家如巴金先生都去写这种文章呢?答案,巴金先生自己就说了,是:‘我坐着,我一直坐着’,坐着的文章,无怪其站不起来了。……在交通(广义的)不便的今日,文学家们只好‘隐’或‘躲’在自己的小屋子里,为静寂损坏了头脑,是只能刻划梦的时刻罢!新伤感主义的文学是很有前途呢!”[13]这是对不少作家文本中的忧郁倾向、不能反映广大现实、不能联系生活和实际行动的一种鞭笞。发表此文的第二天,14号的《新民报(晚刊)·夜光杯》又刊载了该作家的《该抓来吊死的作家》。在这篇文章中,莫名奇借高尔基的言论用更加激进的笔调批评了伤感、抑郁的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认为这些作家“该捉来吊死”,并且举例“如周作人之自号苦茶斋与苦雨斋主人之流,作滴出毒汁似的作品,则真真该杀了”[14]。此时,莫名奇的态度愈发激烈,甚至上升到人身攻击的地步。如果将这两篇文章连起来看,就会发现莫名奇批评的是一种文坛现象。他将巴金与“周作人之流”联系起来,认为他们的文章通病是太过抑郁,不够“关心生活”,无法“投射光明”。仔细看,这一观点虽然迎合左翼文艺理论,但是言辞太过莽撞。1947年1月19日《联合晚报·夕拾》发表了耿庸的《从生活的洞口……》,对莫名奇的文章进行呼应。耿庸借用鲁迅的话,说巴金等作家不过是“做戏的虚无党”,“既不敢明目地卖身投靠,也不敢面对鲜血淋漓的现实”[15]。面对这种情况,巴金再也无法坐着了。他在1947年2月11日的《大公报》上发表了《〈寒夜〉题记》以作回应:“我不想替自己辩护,我还要奉上我这本新作《寒夜》增加我的罪名,同时我静候着莫名奇先生耿庸先生之流来处我以绞刑。我不会逃避。我该向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和联合晚报副刊《夕拾》的编者们道贺,因为在争取自由争取民主的时代中,他们的副刊上首先提出来吊死叫唤黎明的散文作家的自由。这样的自由连希特勒、墨索里尼甚至最无耻的宣传家戈培尔之流也不敢公然主张的,虽然他们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16]尽管巴金回应的态度是这样坚决,在大的环境及延安文艺精神的渲染下还是“妥协”了。1947年《寒夜》初版时,巴金对作品进行大幅修改,“对人物多方面的修改其实也牵涉到对作品主旨的理解。这些修改突出了主人公的理想与这种理想的不可能实现的悲剧冲突;突出了周主任和吴科长所代表的官僚阶层对主人公的心理压迫。而对女主人公的更为同情,也淡化了她与这个家庭的破碎之间的联系。……修改后更突出了作者恨制度不恨人的主题意向”[17]。这一修改使作品更加贴近现实,批判社会的力度增加,伤感的调子减少了许多,说明作家还是受到这些批评者的影响。
与此同时,李健吾也成了被批判的对象。1947年1月11日,他的《和平颂》(5)《和平颂》是根据希腊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的《公民妇女大会》改编的三幕剧,描写了因“战神”贪恋战争而迫使阳间的男人们不断参加战斗,进而全部死亡,于是由妇女们组成的女性协会便派阳间仅剩的一名男人“皮鞋匠”去阴间将这些男人们带回来。可是皮鞋匠没能完成使命,会长此刻恍然大悟,唯有发动女性本能的力量才能将自己的男人们从战神手中“夺回”,于是女人们发动了“不合作运动”,男人们起而逐走战神。此剧本自1946年12月15日起在《文汇报·浮世绘》连载。改名为《女人与和平》在辣斐剧院上演,而当天《大公报·文艺》和《文汇报·笔会》同时出版“公演特刊”,巴金、郑振铎、臧克家、洪深、柯灵、叶圣陶等人分别在两个报刊上发表文章表示祝贺与赞颂,可是祝贺的声音过后,却有了不一样的反响。1947年1月20日,《女人与和平》上演不久,《评论报》便刊载了青真和王戎的剧评。青真认为,在反对内战如此严肃的主题下,剧作者居然为了迎合观众与商业运作,用了戏谑的形式,“把观众从现实拉向想入非非的笑料里去”;并且对于作家拿女人开玩笑,将女人变为“道地的玩具”,进而停止战争的这种“构想”表示“愤怒”。[18]王戎则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上,认为“李建吾先生这个戏,与其说是由于现实的感受,就不如说是依靠了‘妙手自得之’的灵感和神来之笔而完成来得恰当;因为如果是激于现实的感受,我怎么也想象不出李先生会那样的轻飘飘,色迷迷的嬉皮笑脸”[19]。由此可以看出,他们都是基于戏剧对于现实的严肃性而对《女人与和平》进行的批评,是左翼文艺理论指导下的评论。一个月之后,《大公报·戏剧与电影》发表了曰木的批评文章,曰木认为作者“特别强调了两性关系”来表现要求和平的愿望,本身就是“自私”的[20]。由此可见,这些评论者普遍认为李健吾的反内战主题并没有问题,但用一种低级甚至色情的方式呈现就非常不严肃了。这可以说是正常范围内的戏剧讨论,直到安尼的剧评发表,言辞变得异常激愤,评论也变成攻击:“我只觉得,当前的艺术工作者,正与当前的政党一样,有两个不同的倾向,一是真正为有益于人民大众的目的而工作,一是挂羊头卖狗肉,实际只为自己的利益而工作。”[21]在安尼的概念里,李健吾无疑是那种“只为自己利益”的艺术工作者。此刻李健吾终于没办法安静了,在1947年2月23日的《文汇报·笔会》上发表了《从剧评听声音》,为自己的戏辩解,声称是因为剧院支持不下去才这样写,对那些“叫好”的声音也毫不掩饰地指出是自己联系的。[22]这样似乎有点“傲骨”的回应引起左翼作家兼中共党员楼适夷的不满,他专门写了《从答辩听声音》,认为李健吾这种用“逗笑”的方式吸引观众的做法“杀死了艺术,阻塞了话剧的前途”[23]。这对于“剧坛盟主”与新剧启蒙者、推进者(6)李健吾认为,剧作家是占有启蒙的严肃地位的,中国话剧是“富有革命精神的运动体系的暗潮和反应”,而自己作为参与过话剧运动的编剧,更是“前进的文艺之士”。(张向东《民国作家的别材与别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331~342页)的李健吾来说,是相当严厉的指责。李健吾看到此文后表示“接受教训”,并且写了一篇《敬答适夷兄》,和楼适夷的文章一同发表在1947年3月3日的《文汇报·笔会》上,后面还有编者唐弢的《赘言》。不久,李健吾又专门写文解释自己写那篇回应文章的原因:“我现在必须说明我为什么写那篇《从剧评听声音》,因为我觉得朋友们在只是东鳞西爪地引出我的意见——因为是意见,大家明白,见仁见智,自然会引起相反的意见,那我是绝对接受的。但是,有一点,我一直引为伤感情的,就是安尼先生的指摘态度,所以我那篇东西只特别提出他来‘回敬’,而且非常冒火。”[24]态度相比此前的《从剧评听声音》是平和多了。
而唐弢将李健吾和楼适夷的论争文章同时发表的做法还是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1947年3月10日的《文汇报·新文艺》周刊发表了荒野的《“一团和气”》,同时指责了李健吾和唐弢,认为李健吾的这种“沉默作答复”是“市侩的另一种作风”,而唐弢作为编者允许这种现象存在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25]除此之外,唐弢也遭到了耿庸、曰木等人的“围剿”。早在此前就有人为《笔会》上常常发表波德莱尔的译作提出意见,认为他的文章与精神不应当在这个时候的中国被赞美(7)林焕平写作《波德莱尔不宜赞美》发表在1946年12月28日的《文汇报·笔会》上。另据耿庸的回忆录,他也写过文章对此加以批驳(耿庸《未完的人生大杂文》,第186~188页),只是笔者一直未能找到这篇短文。。为此唐弢特意写了《编者告白》作出解释,提出即便波德莱尔的诗“神秘”“晦黯”,可是他的精神里“还有基本的一点,他不安于当时的现状”。[26]可这还是召来了文学青年的不解和“谩骂”。耿庸先在《联合晚报·夕拾》发表《论“从屠夫的袖底”和鼻子的装饰》,引用胡风的话批判唐弢,接着创作《伟大的扑空——〈举一个例〉》寄给《文汇报·笔会》,依旧用激烈的笔调指责唐弢和巴金的“堕落倾向”,唐弢未予发表。[27]耿庸进而又创作了《略说“不安”——兼致唐弢君》,发表在由郭沫若挂名实则由杨晦主编的《新文艺》周刊上。与他的文章同时发表的还有曰木的《从文艺界的恶劣风气想起》,继续批评李健吾和他的《女人与和平》。杨晦发表这两篇文章的原因,耿庸有过回忆。当耿庸在《文汇报·笔会》那里碰了钉子之后,便将《略说“不安”——兼致唐弢君》寄给了《文汇报·新文艺》,进而迎来了杨晦的接待:“他接着就说,从前鲁迅先生说左翼文学是唯有的文学,现在也大体是这样,但是在这样的文学世界里,情况却是复杂的,与现实要求不协调的、近似于抗战时期出现的文学‘与抗战无关’的理论与实践,正在上海以不作理论喧嚣的方式进行着与反内战反迫害无关的文学实践就是其中的一种现象。……他说明,他是由于觉得,对于文学界中种种存在于生活态度、创作思想以至作家关系上的氛埃一般的风气,看来得靠相对说来没有成见、没有顾忌、生气虎虎的有见解的青年一代来冲破、冲垮,因而才说这些话的。但他感叹对这种风气的冲破‘很难很难,需要顽强的、一代又一代青年的韧性。我很希望这样的年轻人踊跃上场’。”[28]189由此可见,杨晦作为一个坚定的中共文艺思想的拥护者,是希望借由青年的力量来“规正”上海的文学状况,因而可以说,他的发文是有意为之。另外,在杨晦为《新文艺》写的“编者的话”——《论战与团结》中也能看出他对于彼时在上海上演的各种论争的态度:“现在,却是论战应该展开的时候到了。文艺界的现状是显得那么散漫,那样薄弱无力。文艺上的道路虽似明显而确定,文艺上的许多问题却不能完全解决,文艺工作者对于文艺问题的意见也正陷于纷(分)歧,甚至于基本的出发点也还有些弄不十分清楚。……我们要公开地来讨论问题,然而,我们更要有意地避免人事的纠纷。在‘新文艺’跟读者相见的时候,正赶上我们文艺界在起着一些纷争。我们接到了针对着这些纷争问题的投稿,假使人事问题不应该牵动我们选稿标准的话,我们不能不登出这些文章来。”[29]于是,之前一系列大大小小的论争在此刻汇总,矛头直指巴金、李健吾以及唐弢等需要团结的进步作家。在自己“挂名”的营地上出现了这种文章,引起了郭沫若的注意,他创作了《想起了砍樱桃树的故事》(8)文章先借华盛顿在童年时期不小心砍掉父亲的樱桃树的故事来比喻当下的文艺风气,认为文学青年不应当在“教条”下“乱砍”和“误砍”;接着郭沫若还肯定了巴金等人的功绩,并向他们道歉。来平息这场风波。关于这两篇文章发表的后续情况以及郭沫若的处理,耿庸和唐弢都回忆过。耿庸回忆,唐弢对《新文艺》的编辑杨晦发文表示不满是起因,认为“社方怎么允许干出在自己报上打击自己人这种事”,唐弢等人“从经济上威胁社方”,提出辞职,若不同意辞职必须当面道歉,杨晦不愿道歉,最后由郭老出面向唐弢等人道歉。[28]193-196此外,耿庸还提到了一个细节:
这天他(指吴清友)一来就对我说,昨天下午他在郭沫若家,谈话中,郭沫若忽然问茅盾在内的在座的几个人:“你们知道耿庸是什么人吗?”吴清友即回答“耿庸是很用功很热情的青年,他就在我那里”(吴清友是宣怀经济研究所所长)。我问郭沫若没说为什么事问我吗,吴清友说:“郭老只说一句‘是我们自己的青年朋友就好’,不晓得他什么意思。”我告诉他大概是因为他挂名编的《新文艺》发表了我的一篇东西。才过了一两天,杨晦打电话来说,郭沫若写的文章已经拿来,日内见报。[28]194-195
由此,郭沫若似乎是迫于“团结”的无奈,才将批评的箭靶指向青年,因而在撰文前,还反复确认是不是“自己的青年朋友”。而唐弢对此的回忆却是耿庸和曰木的文章见报当天,郭沫若夫妇就去到唐弢的住处道歉,可惜当时唐弢不在,于是郭沫若便写信给唐弢,“信里提到《新文艺》上的文章,说是‘牵涉到多方面的人事关系’,他决定说点意见,‘文章难写,但想勉力写出。’”于是就有了《想起了看樱桃树的故事》,事后,郭沫若还写信给唐弢予以安慰。[30]目前没有见到另一个当事人杨晦对此事的回忆,因而不能判断孰是孰非,可是郭沫若给唐弢的第一封信的手稿现已经被收入1979年10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印行的唐弢《回忆·书卷·散记》的卷首页。[31]因而唐弢的回忆似乎更加接近历史真相。但不论郭沫若是真心批评这些“冒进”的文学青年还是迫于无奈和压力作此处理,一定是经过多方考量,一方面要团结这些尚未被“定性”的“中间”作家,将他们争取到“自己阵营”中;一方面更要在党内“清理”思想。仔细观察这一时期引发论争的青年,王戎、耿庸、曰木等人,他们都或多或少与胡风有着联系。他们要么常常在胡风主编的刊物上发文;要么在抗战时期接触到了胡风的文艺理论,并受之影响;要么在文风上与胡风有许多相似之处。[32]而胡风于抗战时期就被认为是左翼文学内部的一个异端,因而此举既是维护和扩大统一战线的举措,又可以进而肃清左翼文学内部的其他倾向。
仔细回忆这时期在上海上演的论争,被批评的对象多是政治上支持革命、支持中共,又在艺术上有自己独特风格的知识分子,他们一直是中共要争取的对象;而举起批评武器的,多是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发表他们作品的“营地”——《新民报(晚刊)·夜光杯》《联合晚报·夕拾》以及《文汇报·新文艺》,也基本是中共领导下的刊物。《新民报(晚刊)·夜光杯》“起先由吴祖光编,……吴祖光很快就走了,由袁水拍接任”,袁水拍是中共地下党员,“当时在中央信托部工作”[33]。关于《联合晚报》的性质,高崧的《关于〈联合晚报〉》以及陆诒的《从〈联合日报〉到〈联合晚报〉》[1]195-205都有详细的记录。而关于《文汇报·新文艺》周刊的创刊原因,当时为郭沫若助理之一的陈白尘也有过回忆:“当此时也,伪国大召开,国共和平谈判破裂,解放战争已经开始,特别是中共代表团即将撤退了,不能不作的一种战略部署。即在文化阵线上集中优势兵力,开辟一个新的文化阵地。”[34]这些都是中共领导或者由中共党员主编的有着进步思想的刊物,因而青年们的批评应当是得到党内至少是党领导下的这些主编支持的,事后由郭沫若对他们进行教育,是为了达到团结各方的目的。而这些进步作家在被批评后确实也收起锋芒,李健吾躲回书斋不再似此前那样有“傲骨”;巴金修改了《寒夜》,并在1948年再版本的《后记》中,删除了此前《题记》中关于那些论争的内容;那些跟胡风接近的文学青年,于1948年在香港关于“现实主义”和“主观论”的激烈讨论中悄无声息。这背后指出了一个事实,那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统解放区的文学精神正悄然在上海蔓延,而蔓延与传播的方式便是通过“批评”与“反批评”来扩大影响力。
综上,可以说巴金、李健吾、唐弢等人及《文艺复兴》的命运是战后广大“中间状态”知识分子及其创办的文艺刊物在上海的一个缩影。抗战胜利后主要集中在上海的大量“自由主义”作家,通过创办《文艺复兴》及《文艺春秋》等刊物,发扬“五四”时期追求民主的政治理想,以及追求人道与自由的文学理想。民主的政治理念使他们成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争取和团结的对象,但主张文艺自由的理念却使他们面临左翼阵营的批评、教育与改造。但这种改造的方式与解放区的“整风运动”和大后方国统区的直接论争都有所不同,而是通过大后方传来的论争在上海的文艺刊物形成回响,或通过在大后方经过教育与改造的知识分子在上海进行“再教育”。由此,经过一系列批评与反批评,延安文艺精神在上海形成一种迂回的传播方式,在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得到教育与改造,进而得到延安文艺权威的接纳,融入新中国文艺一体化的“大军”。而延安文艺理论在抗战胜利后对国统区进步文艺界的渗透与清理,也为中国共产党确定此后文艺的发展方向和路线做好基础性的准备工作。正如郭建玲所说:“从某种意义上说,1945年前后国统区进步文艺界的内部整合标志了四五十年代转折时期延安革命文艺以强力重组、命名并因之建构一种文学新秩序的开始。”[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