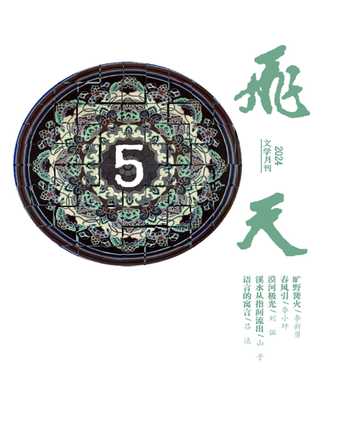路过哪里,哪里便会长满青草(评论)
人邻
之前没看过山子的诗。朋友转来她的诗让我读读,说是一个很年轻诗人的作品,有潜力,刊物有意要推一把。
最初读这些诗,没太读进去。放了一段,再读读,读出一些意思。最初的不能读进去,是习惯性的思维,亦是如今的人太忙,难得静下心来,花时间细读一个未经确认的新人。反省一下,也因此跟几个诗人朋友说,读诗要有警觉,尤其是读新人的。一个人读得久了,习惯了,会有审美上的固守,难得进入新的诗歌感受。人亦是无意义的忙,难得清净,会无意识间排斥。
安静下来,细细读这些诗。山子自然是笔名,二十出头的人,一个女子,用这样一个笔名,取自然意味,也简略,想必是有自己的想法。至少,这个笔名不矫情。也并不像另一些女诗人,在笔名上特别强调女性意识。
她的这些诗,一首一首读过去,慢慢读出她的清灵有味。一些诗句语言的处理有跳跃,有些跳跃也偶有突兀,似乎之间的牵连,无迹可寻。这可能是作者的问题,但也可能是我的问题。但是思维跟了过去的,豁然一下,知道原来诗意如此,惊喜一下。诗人毕竟是年轻,跟我的按部就班,语言循序的按住,逐步推进,诗意的加深,不一样。
先看《清明帖》。诗人一上来写:“清明过后,雨是如此的新”。这是诗人清明祭祀所感。“清明过后”,寻常语。“雨是如此的新”,却别有意味。为何是“新”?祭奠亡者,是旧,一年一年,越来越旧。年年落下的雨水,如同“年年岁岁花相似”,却是“岁岁年年人不同”,每每的“新”。其“新”,是相对于生命的逝去,不能复返的“新”。一个“新”字,用得好。而后,诗人继续写——
我们的亲人
昨日亲吻木窗的蝴蝶
尘埃
一如昨日尘埃
可菊
总会长出新的菊
旧日尘埃里,又是一个“新的菊”。 一旧一新,即岁月,亦即无限的一刹那。所有的惦念、不舍、无奈,就在这样的诗句里了。
《雨夜》的语言表现,有其新妙处——
楼底下有很多小孩子
他们穿着雨鞋在跳舞
水泥地板盛开
一朵一朵烟花
对于人们习以为常的对某些物和形的无感忽略,这是富有想象力的句子。雨花,写到的诗人很多,可是联想到“烟花”,殊少。这个“烟花”,诗的结尾再次出现——
知道吗
明天去往远方的
也是一朵一朵的烟花
“烟花”是虚幻之物,甚至是虚无。诗人由小孩子脚下溅起的“烟花”联想到“远方”亦是“一朵一朵的烟花”,意在迷蒙,亦是对于未知的假设和想象。这是一个小女子在试图体味虚无?也许,至少这个年龄还不该。可是,这其中也许并非全然是诗人提前对于虚幻的感悟,亦可能是诗人对于另一种虚无美的感悟。“烟花”,难道不是一种美么?即便其中有着虚幻的意味。
前面提到诗人语言的跳跃,语言的跳跃是省略了中间无谓的过渡,其间预设了桥梁,看似没有桥面一样,但有桥墩,有桥墩和桥墩之间影子似的牵连。初看似没有,思维跟了过去,就有了桥。这里的问题,也是诗人的艺术功力,是如何在语言的“桥梁”过渡上,在跳跃上,尽可能保留适当的陌生感,这种陌生感会带来读者的阅读喜悦和冲击力。但其关键是,既要引着读者读过去,随着诗人巧妙保留着的顺“理”成“章”的线索隐秘,也要在这种跳跃中,需要适度的陌生感(阅读的适度阻碍),以微妙的语言把控,忽然彰显,渡己亦渡人。
拜访去年的书信
杯子里的夕阳就高兴起来
这两句是诗人《故》里面的句子。“书信”“杯子”“夕阳”,瞬间的感觉链带过去,联想完成,诗意完成。这样的写法于笨拙的我来说,几乎是不可思议,但是年轻的诗人就这样写了。猛然一下,似乎阅读带不过去,慢慢读,真的如此。心境如许,万象灿烂。
《戒指》的语言,有些句子似乎有些纠缠,比如这两句——
抬头
我们仍是多年的恋人
“我们仍是多年的恋人?”是很奇怪的说法。既是“恋人”?如何“仍是”?是,还是不是?也许就是“抬头”的一瞬,再次相互的凝视,使得两个人之间再次认定着这种感觉。“我们”“仍是”。一个“仍是”,从回憶到眼前,一切看似不指明,不确定,但就是这一个“仍是”,让人知道,一切难以回避,一切还是。
诗人也有几首诗,只是感觉,读来有点无着的感觉。无着的感觉,也可以算是一种懂。诗,就是这样。年轻一代的诗人,思维亦会与我等写了几十年的诗人不同。他们觉得在感觉上够了,诗意的完成也就够了。
年轻诗人看似无着的语言灵气是随处可见的——
黏土的耐心
足够温暖行人
我脚底的泥巴
你去往哪里
我的影子就落在哪里
——《秋》
明月楼啊
我手心的建筑仿佛活了过来
——《日记》
再读读《雨夜》——
我灵敏的爱意
混合着
雨水的青草
“灵敏”与“混合”,“爱意”与“雨水的青草”,词语之间的碰撞,一碰就弹开,若即若离,造就了轻灵有味的诗意。《秋》《难过》这些诗,也同样是只攫取一瞬间的感触,更注重自己的心理私密感受,一味写去,不大顾及所谓的阅读。但这些诗有如蜻蜓点水,一点即飞去,留下了水纹的层层漫漶。
诗的读解,历来是麻烦的事情,纠缠不清的。有论者评论斯蒂文斯的诗,指出他的诗“是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这样的指认,还不是中国诗歌所谓的“羚羊挂角”,而是在另一个诗的维度上谈论斯蒂文斯的诗。斯蒂文斯的诗,有其不可解的玄学意味。国内诗人喜欢并且津津乐道多是《坛子》《观察乌鸫的十三种方式》等。但其可能更为重要的一些诗,则很少为我们的诗人提及。弗罗斯特亦是。我们经常读的是《牧场》《雪夜林边驻足》《不能走的路》,而更多地放弃了他的诗歌异质的那一部分。山子年轻,如何研习这些,从中汲取,形成自己更为深入的诗意面貌,还有待来日。
诗人山子亦有《高歌》《钥匙》这样的阅读起来相对指实的作品。这些诗作为同一个作者,她在写作这些诗的时候,内心有着如何的考量?写“形而上”和“形而下”,亦可以交互,都可以造就上佳的诗。诗人需要根据具体的诗意,让其各自有深入拓展,而不是早早画地为牢。山子这些诗,也许是她诗歌拓展的明证。
山子也有一些诗,是近乎匪夷所思的结尾。也许是她的把控失灵,也许是她有意识的试验。我在她的《难过》里,读到了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诗意。不管怎样,诗人面对自己的作品,都需要警觉。她也有一些诗,有着儿童一样的气息。她笔下的《喷嚏》,亦有一点微妙的趣味。
每个诗人要紧的是,写好自己的每个年龄段。山子的年龄,是写好自己的青春懵懂,写好初醒。欣喜的是,在她的诗里,我们有所读到。她的《蓝》里面有这样的句子——
去海边吧
我们都做新鲜的孩子
这看似寻常的句子,是诗人的懵懂也是初醒。世界是不断地新旧循环,也是不断地新鲜,而这个新鲜需要不断的外力加持,诗是其一。人是喜新厌旧的动物。诗歌更是。比起新鲜,所谓的深刻是可笑的。陈丹青曾谈论过一幅梵高的画,好像是《海边的孩子》。这幅画应该是梵高的未完成稿,甚至孩子的面部,只是近乎胡乱涂抹的几笔色块。画面上是一个混不吝的十四五岁甚或更小的孩子,无所谓地站着,浪荡,玩世不恭,对万物不屑一顾那样,陈丹青却觉得好得不得了。问题在哪里,其实就是一股完全的生命之气,生命的原初气息,无所谓美与不美。
对于山子来说,下一步的写作,最为重要的是如何在语言把控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中,保持住这股生气、生命的力量、人性的自然美,这是关键。
自然,她也还需要在语言上有耐心的甄选组织。在诗意的场景里,要寻找到那唯一的一个词,唯一的句子,唯一的诗句安排。
来日方长,祝福山子,好好写吧。写出独独属于自己的诗。
题目“路过哪里,哪里便会长满青草”,引自诗人的诗《路过》。
责任编辑 郭晓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