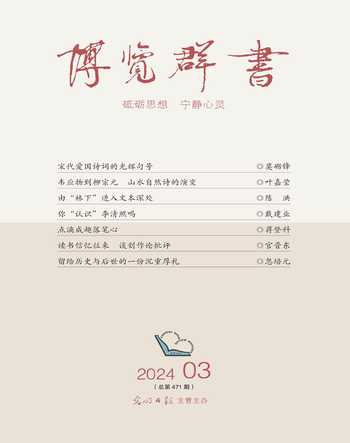《论语》仅仅是一本修身之书吗
李静
我们“学”《论语》,而《论语》第一篇的第一条章句就是讲的“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而“学”成什么呢?这条章句的最后落在了“君子”上——“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所以,當我们以今人对“君子”的理解来定位《论语》的时候,常常会把《论语》简单地讲成一本关于“个人修养”的书。虽然这么讲也不能说错,但是却没能真正地“立其大旨”,没能从根本处理解《论语》的义理。那么,《论语》中所讲的“君子之学”是什么,君子“修身”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
按照儒学自身的讲法,《论语》应该是一本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书。如果用西方的学术概念来说,《论语》应该是一本“政治哲学”著作。《论语》中提到“君子”,有的时候强调的是“有德者”,有的时候强调的是“有位者”。但是,放到先秦的历史语境中,《论语》中的“君子”更多的是“有位者”。那为什么很多人会误解《论语》只是一本修身之书呢?那是因为先秦儒学一直强调的是“有位者”须“有德”,应该“德位相应”,才能实现“纳上下于道德”(王国维语)的政治理想。例如:
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
这一条章句出自《论语·子张》,能“劳民”的自然是“在上位者”。但是,“在上位”的“君子”只有取得了百姓的信任,才能让百姓心甘情愿地去做事,不然百姓会认为是在位者凌虐自己。
《论语》一共20篇,最后以《尧曰》收束。朱子在《论语集注》中曾引用程门弟子杨时的话说:
《论语》之书,皆圣人微言,而其徒传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于终篇,具载尧舜咨命之言,汤武誓师之意,与夫施诸政事者。以明圣学之所传者,一于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于终篇,亦历叙尧、舜、汤、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这段话说的是,杨氏认为《论语》一书以尧舜汤武,以及施之于政事者为终篇,表达了孔子于《论语》中所传之大旨不外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已矣。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理解《论语》中的“学”“孝”“仁”,乃至于“君子”这些概念,都要放在“政事”这个大前提大主旨之下才能从根本上理解《论语》在讲什么。
举一个例子,《论语·学而》的第三条章句是: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这是一条大家都很熟悉的章句,如果我们只是认为这是一条普通的言行训诫的条目,当然也没有太大问题。但是,放到儒学的话语系统中,我们联系先秦相关的典籍来理解这条章句,就会更为恰切。如《诗经·小雅》中有一篇作品就是《巧言》:
乱之初生,僭始既涵。乱之又生,君子信谗。
祸乱初生,是因为谗言受到宽容。祸乱再次发生,是由于君子听信谗言。《尚书·皋陶谟》里面也有一句:
能哲而惠,何忧乎驩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治理者有智慧且能普惠民众,何必担心驩兜的扰乱,何必将三苗流放,何必畏惧花钱巧语的佞人呢?结合《诗经》和《尚书》里面的文献,我们就可以理解到“巧言令色”在政治生活,而不仅仅是在个人品德中的破坏意义。
如果大家对“巧言令色”这一条章句的解读还未完全信服的话,我们可以看看钱穆先生对“夫子温良恭俭让”那一条章句的解读: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论语·学而》
子禽问子贡,夫子每至一邦都能与闻(参与)其国的政事,夫子是如何做到的呢?是他求来的呢,还是别人主动求教于他呢?子贡回答道,因为夫子具有温和、善良、恭敬、节制、谦逊的品德,所以别人会主动求教于夫子。钱穆先生解释说:“亦知人间自有不求自得之道。此与巧言令色之所为,相去远矣。”所以,“巧言令色”与夫子之“温良恭俭让”对读,可见出章句背后“为政”的指向。
因此,把《论语》放到先秦的历史语境中,放到儒学的思想背景下去理解,才能更深入地把握《论语》的义理。如果把《论语》讲成“心灵鸡汤”,其实是像买椟还珠一样可惜的事情。我们不妨来做一个小试验,读者可以先去看《论语·微子》这一篇,如果只强调“个体修养”,我们是无法真正理解《微子篇》的意义,无法理解孔子为什么会“怃然而叹”的。
《论语·微子》篇中记录了许多德行高洁的隐士与孔子(或孔门弟子)的对话或交流。如果只是把《论语》当做一本讲“个体修养”的书,我们就完全无法读懂《微子》篇的教义,无法理解孔子为什么会做出与那些德行高洁的隐士不同的人生选择。听到隐士的规劝,孔子只能“怃然而叹”,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
我不是小鸟不是野兽,所以不能与小鸟野兽同群为伍,以维系自我品性的高洁。我是人,就应该与人为群,这是“人”的必然性。现在天下大乱,道德沦丧,怎能坐视百姓有倒悬之忧,而不奋起拯救呢?“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不能为了一己德行的清洁而忘天下,这恰恰是儒学的道德选择,即其“仁心”之表达。基于此,钱穆先生才会说:“本篇所记古之仁贤隐逸之士,皆当与孔子对看,乃见孔子可去而去,不苟合,然亦不遁世,所以与本篇诸贤异。”所以,如果将《论语》只理解为单纯的个体修养之书,是不能理解儒学的高度与宏阔的。
受西方个人主义的影响,我们现在常常把“个人”与“社会”、“个体”与“国家”对立起来。但是,在儒家看来,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人群之中,“人”的一部分属性是要在“群体”中才能表达出来。同样的,个体的幸福与德行也只能在“群体”中才能达成。如果只强调“个体德性”,如果没有对“国”与“天下”的理解与关怀,“个人修身”则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免走入偏狭与干枯,是不可能最终完成的。
当然,要理解到这个层面,改变大家原来的想法,需要我们将《论语》严谨地放到儒学的思想系统中,尤其是“经学”的系统中去进行理解,一点一点地深入到《论语》的文本与章句中去慢慢体味儒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旨。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