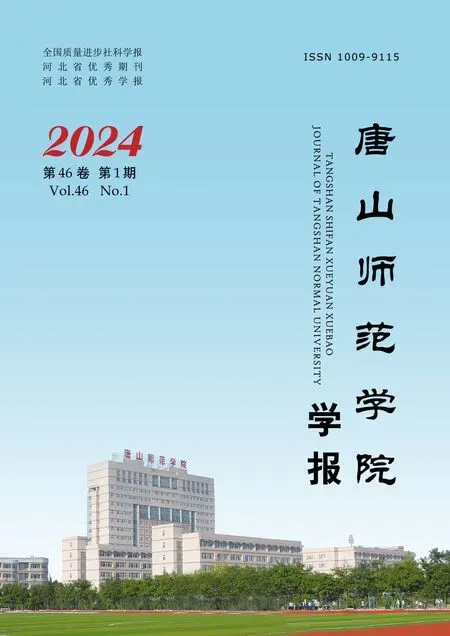《庄子》隐逸思想新解
夏资强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中国隐逸思想源远流长,《庄子》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源头。过去诸家探究《庄子》隐逸思想,多以“隐居不仕”定义“隐逸”,所得结论在“仕”与“隐”(不仕)之间偏向于“隐”这一面。如此阐释不仅在义理上与《庄子》文本不甚相合,而且在论述方式上也值得商榷。本文着力回归文本,对《庄子》隐逸思想进行新的解读。
一、《庄子》隐逸思想的普遍解读与问题
(一)“隐居不仕”解析隐逸的局限性
“隐逸”一词,首见于西汉。在《汉书·何武王嘉师丹传》中,何武将“吏治行有茂异”[1]3484与“民有隐逸”[1]3484对举,认为二者都是“职在进善退恶”[1]3484的刺史应当召见的人。《后汉书·冯岑贾列传》曰:“(岑熙)迁魏郡太守,招聘隐逸,与参政事,无为而化。”[2]663岑熙既然招募“隐逸”参与公府政务,那么就意谓着“隐逸”是尚未入仕者。据此而言,此两处“隐逸”皆指不为官、隐在世间的有德之人。同时,在所举例子中,可发现有“民”与“吏”、“逸”与“政”两则对举语句,此即预示着“隐逸”与“仕”之间存在对立关系。在中国“学而优则仕”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士人视“隐逸”为仕途的反向道路,就此而言,“隐逸”与“仕”是一组具有对立意涵的概念。
学者主要以身隐,即“隐居不仕”来剖析《庄子》隐逸思想。一般看来,有着“隐居不仕”行为的人就是隐士,以此在乱世求全身与精神自由,隐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特殊意义的存在。然而,人终究是活在人世间。在古代典籍中也留有魏牟“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3]980的感叹,有“岩居而水饮”[3]648的单豹因“饿虎杀而食之”[3]648而“不终其天年”[3]179的隐寓。显然,“隐者,固非徒隐也”[4]120,“隐居不仕”这一行为在保全自身与精神满足上不能彻底,不具有根本的意义。
关于“隐居不仕”的行为与隐逸思想两者的关系,可以借助“言意”来解读。“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3]944隐居不仕是外在行为,故属“言”;隐逸思想是内在支撑,故属“意”。要透过“言”来领悟“意”,而不是用“言”定义“意”。因此若用“隐居不仕”来定义《庄子》隐逸思想,则眩于“隐居不仕”之辞,而遗庄生“逍遥”的真谛与破除是非的超拔精神。在此方面,谢大宁先生之说值得重视:“隐士之所以为隐,其本质仍只是在追求某种人生超越价值的贞定,舍此便无以名之为隐,至于隐居之形,不过是成全其人生价值之一手段而已。”[5]21谢先生认为,隐逸思想的本质是追求超越价值,这与《庄子》主旨亦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因为《庄子》所追求的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3]20的“逍遥”理境,同时它也是《庄子》隐逸思想的超越追求。
(二)《庄子》隐逸思想的解读
在学者看来,《庄子》隐逸思想的目的在于精神逍遥与保全自身,而达成此目的则需要通过“隐居不仕”的行为实现。概言之,庄子是在肯定“隐”而否定“仕”,同时也是保持名节而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并从中推导出庄子教导世人归隐,以便全生免祸并获得逍遥自由。如孙旭鹏认为“庄子的隐逸思想正是对这一社会境况的生动反映”,而这社会是“处于动荡状态”的,故而庄子的目的“是在当时恶劣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保存自身”[6];刘梅、肖中云认为庄子是在“危机四伏的战国时代”背景下提出“他的隐逸思想并践行他的隐士人格的”,目的在于“以求得精神世界的舒展与张扬”[7];许晓晴在“‘仕’会给生命本身增加束缚,使人不得自由逍遥,会给人的生命造成危害”的基础上,认为庄子采取隐遁方式以寻求心灵无累、躲避危险[8]。
“龟曳尾涂中”与“或聘于庄子”是《庄子》名篇,从内容上看,庄子是拒绝入仕的,认为入仕有戕身害命之虞,不仕(也就是隐)则能远祸全身。是以面对君主礼聘,庄子“持竿不顾”。这直接说明庄子拒绝出仕,从而保全自身。此种解读虽然可在《庄子》文本、庄子所处的时代获取支持,但却也存在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庄子不“入仕”,是否就是偏执于“隐”,庄子是如何实现不入仕与存世的内在统一?
在此情形下,林云铭与宣颖的解读值得借鉴。首先看林注:“此段言知道者安于贱而不知有贵,然即于贱而自得其贵也。”[9]343“知道者”虽置身纷乱杂遝之世,但能拨开虚妄盘结的假象而凝视着整全圆融的“道”。因此,“知道者”处贱而不叹己贱,处贵而不高己贵,不固执于一端而封限本有的自由视野,能以开放心态观照万物。再看宣颖之说:“国爵为殉名者所羶慕,胡又以此为证焉。”[10]319他认为此节之意是不为名利所囿限、做到“无名”。概言之,此两则故事中的庄子意在道,以道超越仕隐对立,而不是劝解人们归隐。
在《达生》篇“单豹”故事中,单豹亲近自然、远离名利,虽然善养其形,但远离人世造成的不谙世事,让他未能远离威胁,终为饿虎所食而魂归邙山。单豹之弊,在于“不鞭其后者”[3]648。王夫之释“后者”为“难忘之情牵曳不舍”[11]401,并认为它源于“人性之所迁、情之所安”[11]401,可知“后者”就是心知所致的偏执。心有所偏执而竞逐之,生命便丧却天德本真。若欲去单豹之害,则应“鞭其后者”。在《山木》篇“杀不能鸣之雁”的故事中,蕴涵了“不材”“处夫材与不材之间”“乘道德而浮游”[3]670逐一递进的处世哲学。显然,庄子认为“不材”或者率循中道路线都有所不足。“道”作为最高处世哲学在此提出。
因此,《庄子》是以具体的事诠释无限的道,庄子的视野不局限于某一具体行为,而是超脱具体的对立、指向着具有终极意义的“道”,实现对具体层面的超越。《庄子》的隐逸思想并不在于劝解人们隐居不仕、逃避现实,而是超越现实生活,复归于道。
二、隐逸复归于“道”的旨归
(一)“仕”“隐”对立肇端于是非观
在《庄子》中有多处“仕”与“隐”的相关论述,如《让王》篇中拒绝出仕与禅让的故事,《秋水》篇中“龟曳尾涂中”的论述,《列御寇》篇中“或聘于庄子”的描述。“仕”与“隐”是在动荡的现实中士人所采取的不同生活方式,根本上是士人面对社会现实的不同心态、不同价值。《庄子》关切“仕”或“隐”,其目的并非着重于人的行为本身,而是廓清世情世俗对“心”的遮蔽与干扰,由此领悟深层次的“道”,即“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3]72。因此,《庄子》隐逸思想的目的是涤除“仕”与“隐”的执迷,不断寻求自我超越,回归自然与天真,从道的高度对人生遭遇作合理的重构与诠释。
在世人看来,“仕”与“隐”是一组对立概念,这在《庄子》文本中有多处体现。《让王》篇曰:“孔子谓颜回曰:‘回来!家贫居卑,胡不仕乎?’”[3]979在这则故事中,颜回是以隐士身份出现的。在孔子看来,入仕可以获得财富、取得功名,有助于理想实现。基于此,孔子对颜回隐居陋巷、不求仕进之举着实不解,并询问他为何不出仕为官?此外,《让王》篇描述了王子搜逃丹穴、魏牟隐于山林、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山等轶事。这些人都有入仕机会,但是都没有出仕。究其原因在于认为入仕是灾祸之源,远离仕途方可保全自身。
由此可知,这些“隐士”产生了认知上的定限,亦即所谓的“偏见”。人一旦有所偏见,就会产生价值取舍,进而制定各自的是非标准。“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3]198肝胆之间的距离是否如楚越般遥远,则端看个体以差异或相同的观点去衡定;万物是否各有差别,亦端赖个体以差异或相同的角度来衡量。陈赟先生说:“主体所经验的事物,往往并不是作为对不同观看者保持同一性的‘事实’,而是内蕴着主体基于自身‘成心’的‘解释’。”[12]成心亦指成见或偏见。可见人们对事物会有差别看法,并不完全取决于事物本身,而在于个体的态度和看法。个体的态度和看法的形成原因,是在“与接为构,日以心斗”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因此,《庄子》书中有关“仕”与“隐”的探讨,实际上就是通过分析个体的态度与看法,换言之就是对“成心”视角的探讨,因此可以将《庄子》隐逸思想视为是《庄子》关于是非之争的另一种延续。《庄子》谈“是”“非”,不是让人们偏执于“是”与“非”,而是要超越“是”“非”对立、回返于“道”。
(二)超越是非以复归于“道”
由上文可知,“仕”“隐”对立也就是“是”“非”对立,而“是”“非”又起于“成心”。“心”本虚静明澈,在形产生后,“心”为形所牵引纠缠,偏于形而有“成心”。随着“成心”的出现,“是”“非”观念也接踵而起。依乎“成心”,以己之所在为此,以人之所在为彼,遂有彼此之分;进而以己之所想为是,以人之所想为非,便生是非之别。彼此之分、是非之别,都是由“成心”而来。成心使得人对事物的认识偏于事物某一局部或某个侧面,而不知事物所处的全部或整全样貌;持成心观照对象,不仅影响到对象在主观中的真实呈现,也会将这种偏执的认识投射到被观照的对象本身,使对象受到主体自身的遮蔽。此即是“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3]579。“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3]69《齐物论》中儒墨两家的争辩,即是各据成心俗见而交相非,最终导致了世间的是非错乱。但世间本没有是非对立,因为“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3]76“以道观之,何贵何贱,……万物一齐,孰短孰长?”[3]587
陈少明先生对此有精辟诠解:“人世间的是是非非,不在于物,而在于心。物之不齐,是其自然状态,只要你不用势利的眼光来打量它们,就没有此是彼非的问题。泯是非就是放弃一切利害得失的计较,入手处在‘我’。”[13]在陈先生看来,世间种种对立与冲突,其根源大多在于“成心”。这一观点可以在《庄子》文本中找寻到诸多证据:人不能游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3]46是由于“蓬心”所致;因为“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3]69的“成心”作祟,所以有世间的纷扰与情绪反复的现实;“外乎子之神,劳乎子之精”[3]229,亦是人依乎成心,作茧自缚而已。“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3]81从“未始有物”到“有物”再到“有封”,从万物之间的“不同”中引申出“是非”,这是“道”每下愈况的过程,亦即是“道”不断分化与堕落的过程。由此可知,“成心”是使整全浑然的世界逐渐分化为一曲杂多的罪魁祸首。
庄子清醒地认识到“成心”的存在及迷惑作用,《庄子》提出了“吾丧我”“是非两行”等修养工夫。此工夫就是要消解“成心”,使“心”复归于灵动,让耽于“是非”的“心”复归到不知“有物”与不知“有封”之境。《齐物论》篇首即“吾丧我”,丧我就是荡越成心,复归天真本德的工夫。同篇又指出,个体需要秉持“是非两行”的方法,不应追逐是非大小,而要握道枢以应无穷;不应趋利避害、喜求缘道,而要和是非以休乎天钧,俾使有封有畛、破裂亏损之道,复通为一;这种“是非两行”的应变手段,其实就是化掉黏滞、超脱拘执之法。唯有聚焦并荡越“成心”,使“心”从纷扰迷走中挣脱而出,领会“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变,以游无穷者”[3]19-20之乐,才能超然物表、无所黏滞。
当主体不再纠葛于人间世一切人、事、物的关系时,便是在“心”上做到了无己、无功、无名。一切放空而归于无有,消解“己”“功”“名”的系累,即可实现物我冥合、物我对立消解等等,才能在“心”中呈现出来。由之呈现出的样貌就是“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3]315。人若能荡越“成心”,就能使“心”不为万物所裹挟纠缠,同时又能够使“心”面对万物做到物来顺应,如此万物之来与去不会使“心”产生波动,而能始终保持着虚静明澈的状态。如此自能“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己以养中”[3]168,“心”不仅不受“成心”俗见指使簸弄,而且也能适性逍遥。
由上可知,《庄子》围绕着“仕”与“隐”展开的是一个解消“成心”而指向着“道”的命题,其欲阐发的是人间世虽有“仕”与“隐”的对立观念,但这并不妨碍在“心”上超脱“仕”“隐”对立、从而对万物之变皆“不将”“不迎”,最终达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逍遥理境。即得道者立足于“道”的高度等量齐观地看待万事万物:“夫道,覆载万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3]416亦是在荡越“成心”后才拥有的阔达视域。对于拥有这样阔达胸襟、开放视野的得“道”者而言,世间的合离成毁皆不能使其“铙心”[3]465了,因为世间的合离成毁,本就是“道”“自化”的过程,于“道”而言本无亏无盈,也没有得失毁誉。
三、恒反自然之性
(一)《缮性》篇中的隐士
隐士一词出于《缮性》篇,其言曰:
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3]558
在世人看来,隐士是透过伏身、闭言、藏知等方式保全自身者。然而《缮性》篇作者连续使用三个“非”字加以否定。显然,既不认同常识,也不认为这类隐士是“古之隐士”。“古之隐士”之“古”字暗示与“今之隐士”的不同。郭象注曰:“莫知反一以息迹而逐迹以求一,愈得迹,愈失一,斯大谬矣。”[3]560今之隐士透过遁迹方式复归于道,郭象认为他们是“愈得迹,愈失一”,这种做法是缘木求鱼,适得其反。而古代的隐士以消除欲望、实现求道得道为最高追求。
(二)超越是非而反其性
复归于道,亦是复返于自然之性。徐复观先生曰:“道由分化、凝聚而为物;此时超越之道的一部分,即内在于物之中;此内在于物中的道,庄子称之为德。”[14]369又曰:“在根本上,德与性是一个东西。”[14]373在《庄子》哲学视域下,道为最高存在;道以无为而无不为的方式创生万物,万物生成后,超越的道是降在物间、内在于物的,这就是物的德;就个体而言,其具有的特质,叫做性。换言之,在《庄子》哲学架构中,道、德、性虽然有表述不同,但内涵一致。因此,隐士复归于“道”的过程,也是复返自然之性的过程。
“性”内在于事物之中,不能将“性”理解为外在现象来认识,毕竟它是超越于物的。虽然它具备认识与把握的可能性,但是“成心”是不能认识的。因此隐士回返自然之性,就需要消弭“成心”。“性”源自于超越之道,然而由于“成心”的普遍性,逐次使得自然之性在对物质的执取与是非的争辩中受到斫丧,最终流荡失真而有“残生伤性”的情况。
在了解“性”原初质朴的面貌与流荡失真的因由后,如果要复归本性,就需要积极主动地践履超克“成心”的精神修养工夫。“当时命”时,隐士“反一无迹”,郭象注曰:“反任物性而物性自一”[3]559;“不当时命”时,隐士“深根宁极而待”,成玄英疏曰:“既而深固自然之本,保宁至极之性”[3]559。无论是“当”抑或是“不当”时命,古之隐士都能勘破成心、放下执着。消解成心对心灵的系缚,做到“不以辨饰知,不以知穷天下,不以知穷德”。因此,《庄子》的精神修养工夫针对的就是“成心”,在超越“成心”的分别与执着后,即可“反其性”,亦即是复归自然之性。
《庄子》隐逸思想的实质在于超越世间的是非、回返自然之性。南伯子綦(南郭子綦)曾曰:“吾尝居山穴之中矣。当是时也,田禾一覩我,而齐国之众三贺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卖之,彼故鬻之。”[3]849他自叙,早年隐遁山林竟为世人所赞慕推崇;他归隐山穴、灭迹匿端,反而声名远扬、为世情所累,愈发不能从名缰利锁的囚笼中解脱出来。早年不能从世情中挣脱出来,想必是精神修养能力不足,在潜意识层面仍留有鬻声钓世之念。这意谓着早年的南郭子綦仍有“成心”,所以无法从世情俗知挣脱出来。但随后他却能“吾丧我”,超脱仕隐对立,得见“天籁”而体“道”。其原因正如成玄英所言:“得道之人,忘心知之术也”[3]979,即荡越心知,使得自然本性得以如如朗现。反观魏牟,其身虽“在江海之上”[3]980,但其心却“居乎魏阙之下”[3]980,他精神痛苦的原因就是陷溺于成心的泥淖中不可自拔。一正一反,恰证《庄子》隐逸思想的实质在于消解成心、回返自然之性,而不在于劝解世人归隐。
四、结语
综上可知,《庄子》隐逸思想的要义是消解“是”“非”对立,不执迷成见,从而免受心灵戕害而优游闲处。它不是让人拱默山林、不担责任,而是要在“心”上作去蔽工夫,从而超脱是非对立,回归天真本德,达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境界。庄子身处动荡与混乱的战国时代,面对战祸连绵、混乱不堪的社会现实,提出的隐逸思想看似怪异、消极,实则蕴含勘破世间是非、复返天真本德的至高追求,表达了他对逍遥境界的期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