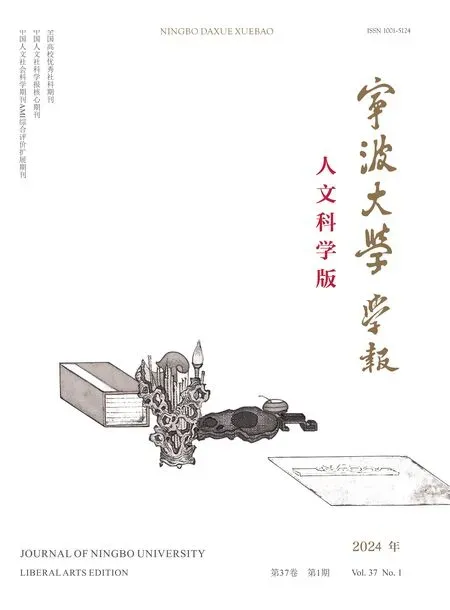卡尔·贝克尔相对主义史学思想的生成
王 娟
在美国史学史上,卡尔·贝克尔(Carl Becker,1873—1945)不仅在实证研究中取得了卓著的成就,而且系统阐述了相对主义史学思想,为史学理论向后现代主义的演进提供了一个醒目的路标。对于后世研究者来说,无论是欣赏,如哈里·埃尔默·巴恩斯(Harry Elmer Barnes)的《历史写作史》(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还是批判,如莫里斯·曼德尔鲍姆(Maurice Mandelbaum)的《历史知识问题》(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Knowledge),都不可能绕开卡尔·贝克尔的名字。
关于贝克尔的相对主义史学思想,在国内外学术界向来颇受关注,研究成果不可谓不丰富。国内学者偏向于通过贝克尔的个别著述,分析其相对主义史学思想。学者们将贝克尔纳入美国相对主义史学脉络中来考察,研究贝克尔的写作意图,比较了贝克尔与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Turner)、查尔斯·A.比尔德(Charles A.Beard)等人的观点异同,评价贝克尔相对主义史学思想的性质与影响。相对而言,美国学者对贝克尔的研究更为丰富。首先,学者们基于贝克尔史学思想产生的历史语境和学术语境,考察了贝克尔史学实践的背后意图。其次,围绕贝克尔的具体著作,学者们剖析了贝克尔的相对主义史学思想,解释了贝克尔史学研究从客观主义到历史相对主义的转变。最后,随着美国学界对相对主义的批判,学者们基于贝克尔史学思想的嬗变过程,论证其史学性质。至于贝克尔相对主义史学思想的内涵,学者们将其概括为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历史事实的主体性、历史研究的意义三类。也就是说,历史学家的主观因素与历史实践是分不开的,历史学家的写作必然受到当时社会环境和思想脉络的影响。历史学家对事实的选择与关系建构,既取决于当时流行的科学概念,又取决于历史学家的先入之见和价值判断。历史学家的职责,一方面是要使普通人的历史理解与实际发生的事情保持合理的和谐;另一方面是要借助历史书写引导读者的现实生活,为他们提供一些看问题的视角和思维[1]。
关于他的相对主义史学思想的来源和形成,多年来也有较多的讨论。较早涉猎这一问题的人,诸如盖伊·斯坦顿·福特(Guy Stanton Ford)、乔治·H.萨宾(George H.Sabine)、利奥·格什伊(Leo Gershoy)、路易斯·戈特沙尔克(Louis Gottschalk)等,大都是贝克尔的学生和朋友。贝克尔在推出《近代史》(Modern History,1935)一书以后,被贴上了“共产主义者”的标签,他的这些学生和友人便出面替他辩护,强调他秉持自由主义立场,其著述乃是出自他个人的经验和思考,是他作为一个历史学教授的自由与责任的产物[2-5]。20 世纪50 年代以后,夏洛特·史密斯(Charlotte Smith)、库欣·斯特劳特(Cushing Strout)和伯利·威尔金斯(Burleigh Wilkins)等学者,从贝克尔的史学思想本身出发,指出他的相对主义理论是从实用主义哲学中发展出来的产物[6]111-112,[7]37-38,[8]94-95。切斯特·麦克阿瑟·德斯特勒(Chester McArthur Destler)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贝克尔的相对主义理论复制了克罗齐《美学》(Aesthetic)中的观点[9]。他强调,贝克尔的相对主义灵感和思想基础来自欧洲大陆,而克罗齐的影响即便不是原动力,也至少是主要动力[10]。德斯特勒的观点又引出了学界新的不同意见。1957 年,戴维·W.诺布尔(David W.Noble)指出,贝克尔的相对主义并非来自欧洲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而是受到比尔德两种历史(“作为现实的历史”和“作为知识的历史”)概念的启发[11]。直到1970 年,海登·怀特(Hayden White)还在与德斯特勒辩难,坚称贝克尔直到1922 年才读到克罗齐的著作,如果要寻找贝克尔相对主义思想的源头,应该追溯到他的老师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和詹姆斯·哈维·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12]。
显然,以上学者都相信,贝克尔的史学思想拥有某种直接的思想或理论的源头。其实,这种单一的线性起源论思维并不能触及贝克尔史学思想形成的复杂性。贝克尔作为史学相对主义思想的系统阐述者,其思路和观点的形成不可能是一个单向吸纳和发展某种理论的过程,而具有相当复杂的社会语境和思想脉络。如果从贝克尔的成长经历、思维方式、学术师承和学界氛围、时代背景等方面着眼,或许能更好地理解他的理论关怀和思想进路,从而更清晰地描述其史学相对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
一、中西部成长经历——相对主义史学思想的种子
1910 年,卡尔·贝克尔发表《超然与历史书写》(Detachment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一文,首次明确提出相对主义史学思想[13]3-28。然而,当时历史相对主义在美国历史学界还没有很大的影响力。正如彼得·诺维克(Peter Novick)所言:“贝克尔不像他同时代的人,不需要战争的催化,也不需要放弃社会乐观主义,就能把他变成一个彻底的相对主义者。”[14]贝克尔之所以能比同时代的多数人早几十年提出历史相对主义,部分源于他在美国中西部的成长经历①。这些经历给他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印上了深刻的烙印。
1873 年,卡尔·贝克尔出生在美国中西部爱荷华州黑鹰县(Black Hawk County)的一个农场里,11 岁时全家搬至附近的滑铁卢小镇。这个地方远离东海岸美国文化中心。1910 年,贝克尔在《堪萨斯》一文中对比了东西部人的特点。他将东部人看成是“坐在熟悉角落里的人”,西部人是“热切希望探索未知世界的人”[15]。在去康奈尔大学上学之前,他从未离开过这座小镇。这种勇于探索、乐于进取的社会氛围,深深地影响了贝克尔的思维习惯,他将美国边疆的开发看成一个过程,称赞新旧文化的碰撞,期待新事物的出现等。这种习惯形成了贝克尔敢于质疑与挑战传统的性格,这种性格推动了贝克尔对科学历史学的绝对客观的质疑,而这恰是其相对主义史学思想的起点。中西部的环境氛围还塑造了贝克尔的实用主义理念,这种理念也成为其相对主义史学思想的重要基础。他在回忆起这段早年岁月时说:“我很高兴能作为一个卑微的‘工人’,用一个麦考密克式(McCormic)的自动割捆机,每天在40英亩的燕麦田里劳作10 个小时。这种务实的追求不断地出现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16]11正是这种务实的追求孕育了贝克尔的实用主义理念②,使他认为历史应该对某些当前的、实际的目的有益。
实际上,贝克尔早期的相对主义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他那个时代正统观念的批判,而不是试图产生一个独立的历史理论③。他既不相信历史研究的绝对客观,也不相信基于枯燥考据写作的历史作品有实用价值。他的历史相对主义既质疑了科学历史学的核心假设,还否定了科学历史学的现实意义。可以说,贝克尔在20 世纪初发表的2 篇文章,既是他从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历史事实的主体性、历史研究的实用价值等多角度思考历史相对主义的早期成果,更是他后期“两种历史”“什么是历史事实”“舆论氛围”(Climate of Opinion)、“似是而非的现在”(Specious Present)等理论内涵的基础。这一切都应该理解为对一种生活方式、一类环境条件的自然而然的思想反映。
贝克尔的中西部成长经历还培养了他对写作有趣故事的爱好。阅读的过程中,他萌发了成为作家的梦想,发现了“优秀作品”“有趣故事”“好书”与“有影响力的书”之间的差别[17]。这种差别启发了他后来区分“可读的历史作品”“好的历史作品”“有影响力的历史作品”的意识,并最终演变为他对历史作品实用价值的关注[16]33-34。在贝克尔阅读的作品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威廉·迪安·豪厄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和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书籍。他从前者那里学到了观察“作家笔下的人物及其所处环境”,分辨“亲历者的经验”和“作者自己的观察”[8]33;从后者那里学到了区分作者的主观性与材料的准确性,寻找动机的差异与人物形象、情节之间的联系[6]126-128,[7]79。这些思考是贝克尔对文字作品真实性的最早怀疑。它们推动他反思:作家是否能够把自己置身于任何人的生活和情感之中?人类对过去生活的诸多研究是否完全正确?这些怀疑又使他对具体行动背后的人物心理、情感动机产生了兴趣[18]22-25。
这些阅读为贝克尔的相对主义史学积累了大量的原始思想材料。他不仅隐约意识到作品的实用价值,还有意识地思考了写作者的主观性、亲历者言行的动机与作品的真实程度等问题。当他的梦想逐渐从写作有趣故事转变为以史学为志业后,这些由文学阅读所引发的思考也转入具体历史领域研究。这种转变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贝克尔在文学写作上遇到了困难。他以一种自认为是文学风格的方式写作,但并没有写出他向往的那种有趣故事[18]22-24。不过,写作是贝克尔一生中最持久的兴趣,他对如何写作的思考延续了许多年。这种思考连接了他从“想成为小说作家”到“成为历史学者”的过程,加深他对“过去实在”和“活的历史”的体会[17]。其次,历史与文学的天然亲近性,使得贝克尔关于文学写作的思考可以直接运用到历史研究之中。这可用贝克尔给写作的定义加以印证,在他看来,“好的写作是充分有效地表达写作者想表达的事实、想法或情感”。而这一切的要点是,写作者“必须有自己的东西要说”,且“以自己的方式说出来”,因为写作者必然受到某些约定俗成的思维方式或刻板的表达方式的制约。最后,特纳和查尔斯·霍墨·哈斯金斯(Charles Homer Haskins)对贝克尔的指导,激发了他学习历史的兴趣,鼓励了他的史学相对主义思考。
贝克尔在中西部的卫理公会教徒生活也引发了他对基督教要义的怀疑,树立了他敢于谨慎怀疑、勇于接受新事物的人生态度。这是贝克尔敢于质疑科学历史学的客观性,逐渐形成相对主义史学思想的重要前提。贝克尔对宗教的警醒是由家乡的宗教狂热所引发的。用他后来的话来说,他的家乡是深受“卫理公会威胁的核心地带”[16]124。贝克尔曾在不同的地方多次提及他参加过的两次布道。一次是范内斯(Van Ness)牧师的布道,在布道中范内斯谴责了伏尔泰的无神论。针对这一行为,贝克尔讽刺道:“这并不是因为了解伏尔泰,而是想借助他在滑铁卢和爱荷华州的盛名让孩子们加入卫理公会。”[19]这种讽刺是以对基督教有神论的怀疑为基础的。另一次是厄普代克(Updike)牧师的布道,布道词是“我该如何解决我的疑惑”,他的答案是,“任何信条都可以用它能被转化成生活的程度来衡量”,“其要点是,与其对任何事情都没有积极的信念,不如谨慎地怀疑,即使是基督教”[18]19。这两次布道是贝克尔有意识地思考宗教问题的开端,滋养了他敢于质疑权威的精神。
到威斯康辛大学上学后,贝克尔对宗教的怀疑逐渐聚焦到宗教“证言”问题。当发现宗教对生活之谜的解答越来越不能令人信服时,贝克尔开始把宗教信仰看成一种强烈的个人行为,“只有他自己和上帝才知道”。他开始思考,所有的教会都要求成员“证明”他们的宗教经历,但当亲历者和目击者意见不一致,或他们的宗教经历无法局限在圣经和某一特定教会官方承认的过去事件时,该如何评定[18]17-21?他对宗教中证言问题的思考,加深了他对历史事实的主体性的理解,对他相对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也有借鉴意义。他对宗教经历的分析与对历史事实的思考有相似之处:我们为什么要相信目击者对事件的叙述?什么时候我们应该认为他们值得信赖?“经历/事实”应该被分解到什么程度?这种分析应该在什么时候停止?当年轻的贝克尔在思考这些宗教证言问题时,就已经在模拟分析历史依据与历史事实的关系。这一点他在评论《巴特勒主教和理性时代》(Bishop Butler and the Age of Reason)时已经确认:“关键的问题不是证词,而是人们接受证词的倾向(以此来确定这种或那种事件)。”至于历史研究,其关键问题就不再只是史料的真伪,还有史料背后的某种东西[20]。这种背后的东西是贝克尔始终感兴趣的内容,并以“舆论氛围”的概念呈现在其相对主义史学思想体系中。
贝克尔的早期经历塑造了他的中西部思想意识,这种意识是贝克尔质疑科学历史学的局限的前提,又是贝克尔历史相对主义的起点和价值目标。贝克尔的早期经历还培养了他对阅读和写作的爱好,这一爱好为其相对主义史学积累了大量的原始思想材料,之后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转化成了具体的史学研究。贝克尔的早期经历也引导了他对宗教的积极怀疑,这一思考不仅树立了他的人生态度,还类比了历史研究的分析过程。这既为贝克尔提出相对主义史学思想做了思想准备,又为其相对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借鉴。这些因素在贝克尔的头脑中相互交织,进而形成特定的思维模式,成为其相对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性影响”(Formative Influences)。之后,在威斯康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教师的教导下,贝克尔的相对主义史学思想逐渐萌发。
二、学术传承与写作——相对主义史学思想的萌芽
威斯康辛大学是贝克尔史学生涯的开端。1893 年,贝克尔从康奈尔大学转入该校④。1896 年,他升入研究生学习阶段,在特纳和哈斯金斯的指导下主修历史。
在威斯康辛大学,给贝克尔带来最大学术影响的当属特纳。特纳的课程不仅改变了贝克尔对历史的认知,还修正了他关于史学“客观性”的看法。他早先认为“客观”是指“完全的冷漠,一种僵硬的严肃态度或者说‘僵尸’(rigor mortis)精神”,这是之前从伯伦汉(Ernst Bernheim)⑤那里学到的。“比如说,它要求细心的历史学家在写作‘冷港战役’时,不要透露自己的父亲曾是格兰特的狂热支持者。”在特纳的课堂上,贝克尔意识到伯伦汉对“客观性”的理解“太泛化了”,“通常变得有害,成为替代思想性的最佳理由”。幸好特纳的言传身教赋予贝克尔新的体会。他对“客观”的理解由“僵尸”精神转变为“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怀有真诚的求知欲望”,“专注于一个单纯的为了解它而了解它的目的”[21]174-176。
贝克尔还从特纳那里学会区分历史事实和历史事实的用途[16]17。在贝克尔的记忆里,特纳在课上不止一次地提到“历史是人类的自我意识”。在特纳看来,“每一个时代都试图形成自己对过去的认识”,“但这并不意味着过去的真实事件会发生变化,只意味着我们对这些事实的理解发生了改变”。因此,“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便是从过去的角度认识当前社会,并赋予它新的思想和感情、新的渴望和能量”[22]。贝克尔延续了这一思想,在《超然与历史书写》中写道:“我们必须有一个过去,它是所有现在的产物。”贝克尔觉得这句话,“就像是说历史是人类的自我意识一样”。在文章发表后贝克尔写信给特纳说,“那句话在当时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但这些年肯定一直在我意识的‘边缘’发挥作用”[16]16。
特纳在1910 年的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年会上发表的主席演说,也启发了贝克尔对“舆论氛围”的思考。在演讲中,特纳深入剖析了时代精神对历史学家及其作品的影响[23]。之后,贝克尔在安排课程设计时提到,历史学者不仅要研究特定历史学家,借此说明不同时期主流历史研究的方法和目的,而且要展示历史研究如何回应不断变化的影响,这些影响先后塑造了欧洲的思想和历史[16]22-23。在征询特纳的意见后,贝克尔将这些思考写成《社会问题与思想对研究和写作的一些影响》(Some Aspects of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Problems and Ideas Upon the Study and Writing of History)。在这篇文章中,他从社会环境和学术背景等角度探讨了历史学家研究方法、研究题材的变化[24]。
哈斯金斯是另一位对贝克尔产生重大影响的威斯康辛大学教师,以研究中世纪史见长。贝克尔曾用调侃的语调回忆道:“那一年我还没有真正学历史,我只是受到感染,想学历史。这当然是特纳的错,而不是我自己的原因(顺便说一下,也是哈斯金斯的错……至于哈斯金斯,要说的还有很多)。”[21]164这是贝克尔对哈斯金斯的一次书面致谢。在给特纳的信中,他又一次表达了对哈斯金斯的感谢:“对不诚实的、次等的、没有意义的语言及没有逻辑的简单概括的恐惧……也是我从你和哈斯金斯那里学得到的。”[16]76
哈斯金斯还对贝克尔的《超然与历史书写》给出积极反馈,他赞同贝克尔提出的“不存在绝对超然”观点,并提醒这并不是放弃追求最大程度超然的理由。在信中,哈斯金斯同样讨论了历史研究的分析与综合,并指出综合过程中的主观因素较之分析过程要多[18]70。他还称在这篇文章中的“一两个地方发现了贝克尔在麦迪逊上学时就开始讨论的痕迹”,这说明哈斯金斯在贝克尔求学期间就关注到了他的相对主义史学思想。在哈斯金斯研究中世纪的名著《十二世纪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1927)中,哈斯金斯对中世纪“黑暗”性以及教会反科学性的否定也影响了贝克尔。后者将启蒙“哲学家”解释为“不是基督徒的基督徒”(Christians-not-Christian),这也是《十八世纪哲学家的天城》(The H eavenly C ity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Philosophers)的主题[25]。
1898 年,贝克尔申请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奖学金。在哥伦比亚大学,贝克尔经历了在威斯康辛大学同样的好运,接触到两个对他影响很大的人——詹姆斯·哈维·鲁滨逊和约翰·W.伯吉斯(John W.Burgess)。在全新的环境中,贝克尔进一步拓宽了学术视野,接触到了高度集中的思想资源,尤以鲁滨逊的影响为最。
鲁滨逊的18 世纪思想史课程,赋予了贝克尔对法国启蒙运动的更多了解和热情,并使他获得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鲁滨逊先在哈佛学习,在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影响下,他对哲学中的多元主义和实用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之后,鲁滨逊到德国弗赖堡大学跟随赫尔曼·冯·霍尔斯特(Hermann von Holst)学习。此时,正值卡尔·兰普莱希特(Karl Lamprecht)等人向兰克史学发起挑战,引发文化史大争论的时候。在这段时间里,鲁滨逊不可避免地受到争论的影响,开始反思科学主义史学的客观性,接受社会心理对个体心理的影响等观念[26]63-64。贝克尔在鲁滨逊的研讨班接收到了这些新知识,并将这些知识运用到该课程的课堂论文中,写了一篇关于重农主义的论文。正是在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中,他“对‘人们为什么会这么想’这类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7]。鲁滨逊对此评价道:“你在研讨课上的那些报告,显示了你的勤勉与洞察力,也充分证明你已经很好地掌握了史学研究方法。”[8]62这种对“运作中的智慧”现象或者“思维的运作方式”的探索,贯穿了贝克尔此后的学术研究。
除给贝克尔提供法国历史方面的知识外,鲁滨逊对“新史学”以及历史与记忆的理解也给了他很多宝贵的启发。鲁滨逊作为美国“新史学”的引领者,顺应了20 世纪初那种进步、务实的风气。他提倡历史学应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做出变革,要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充研究的方法,主张历史研究要为现实服务[28]。贝克尔的《论〈独立宣言〉政治思想史研究》(The D 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一书及《1776 年精神》一文便体现了“新史学”在选题、史料、方法上的这种风格。在《韦尔斯与“新史学”》一文中,贝克尔回忆了鲁滨逊反对脱离现实、专注考据的研究取向。在《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中,贝克尔也延续了这种讽刺“考据癖”的做法,说“认为事实一旦被充分确认就‘其义自现’,那纯属幻想”[29]207。
约翰·伯吉斯关于社会科学的跨学科方法以及“正在形成的历史”(History in the Making)这一概念对贝克尔的影响也很大。伯吉斯在莱比锡大学师从德国历史学派的大师威廉·罗雪尔(Wilhelm Roscher),从他那里学到了社会科学间的相互依赖性。伯吉斯在柏林大学师从约翰·G.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之后他将《政治学与比较宪法》(Political S cience a nd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题献给了导师。伯吉斯热衷于将哥伦比亚大学转变成德国式的研究和学术机构,通过引进德国的“习明纳尔”教学法,培养下一代历史学家掌握历史和政治科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在他看来,历史“作为人类精神理想的所有客观表现形式,包括语言、传统、文学、习俗、礼仪、法律、制度、观点和信仰”,是一个需要解释的未完成的故事,一直是“正在形成的”。在思考历史的意义和用途时,伯吉斯同样认为历史不仅仅是过去,而是人类成就的全部故事。任何希望在当前进行有效思考或采取有效行动的学者都必须利用这个故事[30]。伯吉斯的观点应和了特纳和伊利的见解,加深了贝克尔对跨学科方法的重视,加固了贝克尔对历史研究的主体性及历史学实用价值的理解。贝克尔评价伯吉斯的课程是“健全的政治学”,伯吉斯则称赞贝克尔是“一个能干、认真、勤奋的学者”,赞扬贝克尔在哥伦比亚的学习生涯取得“巨大的成功”[8]65。
自1894 年第一次正式接触历史学以来,贝克尔一直受教于史学大家。这无疑为贝克尔史学思想的形成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知识环境。首先,在特纳和哈斯金斯的影响下,贝克尔决心致力于历史研究,开始思考历史研究的主观因素以及历史实用主义。其次,伯吉斯的跨学科课程培养了贝克尔利用其他兄弟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自觉。他强调的“正在形成的历史”等观点给贝克尔留下了深刻记忆,并被纳入他的相对主义史学理论体系中。最后,鲁滨逊的研讨课展现了法国革命和欧洲思想史等内容,丰富了贝克尔的知识储备和历史研究方法。他关于“新史学”以及历史与记忆的见解,推动了贝克尔的史学相对主义思考。至此,贝克尔已经具备了形成相对主义史学思想的先决条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他将在学界氛围和时代背景的影响下逐渐深化自己的史学思想。
三、学术语境与历史语境——历史相对主义的深化
“转动一个门把有时候需要上百年,可是一旦门把转开了,它就带来巨幅的改变。”[31]欧洲历史意识觉醒于近代早期,随着历史意识的萌动和日臻成熟,人文主义思想家确立了一种观点,即必须依据事物的时间、地点和环境来研究事物,这构成了近代历史主义的早期背景。后经18、19 世纪德国哲学的洗礼,历史主义主张历史是一个过程,而每个历史阶段都是唯一的,必须从它自身的条件出发才能对其进行研究。从其具体观点可以看出,历史主义与历史相对主义有毋庸置疑的联系,历史主义自身包含有历史相对主义因素。同时在科学实证主义思潮和兰克客观主义史学的影响下,西方史学依然强调“客观事实”和历史的外在经验证据,相对主义受到有效的遏制。直到19 世纪末和20 世纪初,经过新康德主义者狄尔泰、新黑格尔主义者克罗齐等人的反拨和阐释,虽然否定了把历史学等同于自然科学的做法,但其唯心主义主观认识论的逻辑必然导致历史相对主义。无论是狄尔泰的“理解”,还是克罗齐的“顿悟”,都把历史真实性的科学检验方法排除在外。因此,在20 世纪早期,西方历史学家在唯心主义思潮和世界大战的严酷现实的双重冲击下,逐渐失去朴素时代的宁静信念,不再相信历史判断的确定性。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卡尔·贝克尔提出“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的见解,号召历史学家通过历史书写来指导人们如何利用历史。因而,贝克尔的历史相对主义思想既是历史主义危机的表现,也是一个真诚的历史学家清楚看到面临的困境,为捍卫历史学的价值和尊严而痛苦思考的结果。但与其导师不同,贝克尔并没有留学德国的经历,唯一一次欧洲之行只到了英国和法国[32]。所以,他的相对主义史学理论体系,不是历史主义的直接承继,而是美国历史学界关于历史知识问题探讨的阶段性成果。
在贝克尔史学思想产生和深化的过程中,历史学界广泛讨论了历史研究的性质及其作用。以美国历史协会的主席演说为例,许多历史学者都讨论过史学客观性、历史事实、历史学的实用价值等内容。其中,乔治·P.费舍尔(George P.Fisher,1898)指出了历史学家作为历史人物的裁判角色,亨利·C.李(Henry C.Lea,1903)考察了时代因素对历史学家的影响[33-34]。在他们之后的学者大都延续了这种思路,他们对史学客观性的怀疑,主要集中在历史学家的主观性上,一方面强调历史研究既要关注形成当时人活动基础的时代思想,另一方面关注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对其历史解释的限制⑥。贝克尔的相关文章或书信可以展现他对这些学术动态的关注。在1903 年美国历史协会年会上,贝克尔评价了李的演说,“李已经明确阐述了所有至关重要的历史观念,这些观念使得严谨的历史研究具备了无可替代的价值”[26]21。1917 年,贝克尔在读了乔治·林肯·伯尔的主席演说后,写信称赞他对历史的自由和历史学家的自由的区分,并提到自己在去年发表的一篇书评中也表达了这种区分[16]5-51。这些可以证明,贝克尔已经注意到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和历史研究的舆论氛围很长一段时间了。
历史学界对历史事实性质的分析也很早就开始了。协会的第一任主席安德鲁·D.怀特(Andrew D.White,1885)就提到,使一个事实变得空洞或意味深长的,是它与“历史演变的伟大脉络”之间的关系[35]。之后的协会主席大多不仅延续了这种解释,还提出了更深入的解释。大致可将他们的观点分为两类,一类关于历史事实的主体性,大多数学者都承认其研究过程存在事实选择和价值判断;另一类关于历史事实的变化,学者们普遍认同历史事实存在变化,并指出发生变化的原因是发现了新的事实或为满足不同时代的需要⑦。贝克尔对历史事实的研究可以看作是参与学术对话的具体实践。他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最早出现在《超然与历史书写》中,他说,历史的“事实”,“只是历史学家为了理解它而制造出来的心理意象或画面”[13]11。对此邓宁写信评价道:“你不仅说了很多我认为是深刻的事情,并且你说的方式给了我巨大的快乐。”[36]贝克尔对历史事实最深刻的研究,当属1926 年发表的《什么是历史事实?》一文。在美国历史协会年会上宣读后,贝克尔与费迪南· 谢维尔(Ferdinand Schevill)、麦克劳林等人就历史研究是否应该有一个预设的目的进行讨论[26]157-158。在与这些学者的交流中,贝克尔梳理了自己对历史事实的分析。
学者们还十分重视历史研究的实用价值。安德鲁·D.怀特率先在演说中提出利用历史的直接效用的必要性。这一呼吁在许多学者那里得到了回应,他们主张将历史研究作为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有效途径,或者将历史研究的成果运用于具体实践⑧。在贝克尔那里,历史研究的实用价值则是他一直以来的追求。1931 年12 月,贝克尔发表《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的演说后,威廉·E.多德(William E.Dodd)写信询问贝克尔,他演说的内核是否是“历史无用论”?对这一评论,贝克尔以“历史的作用是什么”这一问题加以回应:“即使没有什么是可以最终解决的,但努力解决它永远是必要和有用的。”“历史学家的职责之一就是,(借助历史作品)尽可能地使普通人的历史理解与实际发生的事情保持合理的和谐。”[16]156-158与学界的交流,不仅鼓舞了贝克尔长期以来对历史研究的主观成分的关注,还推动了他对这些主观成分的理论阐释与深化。相较于萌发阶段偏向分析历史学家的主体性、历史事实的主体性而言,这一时期他更为强调要正视这种主观性、主体性,并在对这种主观性、主体性的认知下去分析“舆论氛围”是如何影响历史写作的,以此扩大和丰富普通人的“似是而非的现在”,引导和纠正普通人在当下的行为。
除学术环境外,时代背景也给贝克尔带来了很大冲击,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次战争中,贝克尔扮演了宣传者的角色。他先后发表《门罗主义与战争》(The Monroe Doctrine and the War)、《德国企图分裂比利时》(German Attempts to Divide Belgium)、《美国的战争目标与和平计划》(America’s War Aims and Peace Program)等作品,向公众解释政府对战争的看法,宣扬威尔逊的“新世界秩序”。然而,战争没有给欧洲和世界带去美国式民主,关于战争罪行的争议和盟军秘密条约的揭露更是对贝克尔立场的讽刺。对于这个结果,贝克尔早先是怨恨威尔逊,认为后者将自己的利己主义弱点隐藏得太深了。但是逐渐地,他开始反省: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尤其是学了25 年历史的历史学家,仅对威尔逊所做的事情感到愤愤不平是没有用的。他应该努力去理解,在这样一场战争之后凡尔赛的和平正是人们所期望的,也应该明白在这样一场战争之后和平不可能是兄弟之爱的表达。这一体会使贝克尔明白战争或许不是人们真切想要的,只是人们为了实现目标或保护自己利益不受侵害的工具和手段。贝克尔意识到历史研究还需要一种“更微妙的心理学”[16]86-87。通过历史人物思考问题的方式而不是思考的问题,来分析那些决定历史人物行为的无意识动机,正是贝克尔对微妙心理学的实践,也是超越科学历史学的具体表现。这一方法使贝克尔将兴趣转移到影响历史进程的“人人”身上,增强了他对历史背后动因的关注,推动了他关于“舆论氛围”的思考。
在贝克尔成长和成名的阶段,相对主义已是一股渗透到许多领域的思潮,在历史学领域则牵涉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历史事实的主体性、历史研究的实用价值等问题,早已是一个引发诸多思考的话题。在与这些思考的对话中,贝克尔坚定了自己对历史研究的主观成分的阐释,梳理了他对历史事实的理解,构建了他关于相对主义思想的历史哲学表述。此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历也影响了他的历史理解,促使他关注历史背后的动因。他开始通过历史人物思考问题的方式,而不是思考的问题来剖析历史人物的心理状态以及当时的历史现状。这对于他后期提出“舆论氛围”“似是而非的现在”等理论概念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余论
2018 年4 月12—14 日,美国历史学协会举行了第111 届年会。会议主题为“历史的形式”(The Forms of History),即“历史以多种方式被认识、误解、书写、展现、传播、影响、分析、歌颂和教授”。在此次会议上,新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爱德华·艾文斯(Edward L.Ayers),发表了题为“每个人都是他/她自己的历史学家”(Everyone Their Own Historian)的演说。这与卡尔·贝克尔1931 年12 月发表的主席演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极为相似。艾尔斯认为,在贝克尔发表演说之时,美国史学已经初步完成职业化进程,他的演说无异于给了职业史学家当头一棒[37]。因此,许多史学家抨击贝克尔的相对主义史学,认为这种观点过于强调外部环境对历史学家的影响,鼓吹利用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损害了历史学的专业权威。许多人更是将贝克尔的历史相对主义视为绝对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在这些批评者看来,贝克尔预设了某种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即是说受制于历史学家的主观性与人类认知的局限性,历史研究者永远无法“重现过去的本来面目”。他们认为,得到历史学家共同赞赏的知识就是“超然”的。随着掌握的史料增多,历史学家会越来越接近真实的过去[38]。
事实上,这些都是对贝克尔的误解。贝克尔认可批评者们关于“重现客观历史的理想至少可以部分实现”的表述,他也确实强调任何特定时代的历史记录者、历史研究者,都受到他所处时代的“舆论氛围”的影响。但是值得说明的是,贝克尔虽然提出了“旧观点总被新观点所取代”的历史观,但他并没有将相对主义看成是固定不变和支配一切的[29]211。他强调的是,虽然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但毕竟是人类的理性发现了这种“舆论氛围”的影响,因而人类应该始终热爱真理并坚持追求真理[39]。他也“没有否认真理的存在或其可知性”,只是说不“存在一个永恒的、普遍有效的元标准”。他关注的是不同社会、时代和方法假设所采用的各种标准,而不是说没有标准[40]。不可否认的是,贝克尔的这种历史思想中蕴涵的这种实用主义和相对主义色彩,确实给美国史学职业化早期的历史研究者造成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动摇了历史学的专业权威。这应该算是史学职业化的非预期性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