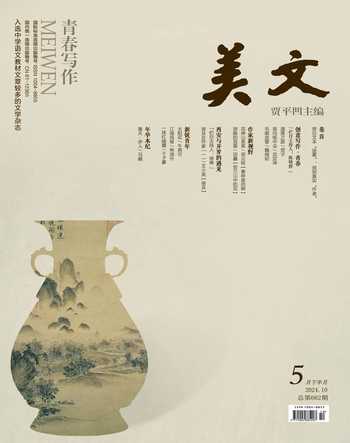消隐的苜蓿
田鑫
带着《贺兰山植物志》按图索骥在贺兰山寻找野生且开花的植物,约等于拿着通缉令在城市拥挤的人群中寻找通缉犯,这个比喻或许并不贴切,但却是我在山里寻找了一个夏天之后最切身的感受。
好在,寻找的路上,总有意外收获,比如发现了一些不在寻找之列,又很有代表性的植物。比如,苜蓿就是一例。当时,我正坐在拜寺口的一块石头上,对着一具岩羊的白骨发呆,眼前突然就出现了熟悉的画面:一株苜蓿,正迎风站立着。
它的茎斜生着,羽状的三出复叶均匀地镶嵌在微披柔毛的分枝上,螺旋状的荚果,有一种满满的收获感。最耀眼的属紫色的小花,正朝着太阳,看上去悠闲自得,似乎很享受这里。我猜想,这不是刻意种下去的,应该是很久之前遗落的一粒种子,在这里扎了根。
我是在六盘山腹地的一个小村庄里认识并熟悉苜蓿的,那里出门就是土地和大山,每家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苜蓿地,地里成片的紫花苜蓿,是养牲畜的保障,也是黄土高坡上献给自己的诗情画意。
我家的苜蓿地,在院子的东侧,一出门就可以躺在里面。苜蓿还没长高的时节,我经常会躺在苜蓿地里,看白云慢悠悠地从天空飘过,听虫子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也追着蝴蝶跑过。多年以后,我才确定,我曾在一块苜蓿地里拥有过不一样的童年。
在一生疼爱牲畜的祖父眼里,苜蓿是上好的饲料,不管是嫩草还是青储,牲口吃了苜蓿,一定会长膘。并且苜蓿喂养出来的牛,毛色光滑油亮,有绸缎的感觉。于是,割苜蓿就成为我回忆祖父的一个细节。
苜蓿刚露出地面时,我们会挎上篮子去掐苜蓿芽,为的是中午就着热馒头吃。吃过苜蓿芽后,很长一段时间,苜蓿就独自生长着,远远地看过去,一地的紫色碎花,煞是好看。不过,大人们不会去操心它的花是三瓣还是五瓣,他们只等着苜蓿成熟,割来给牲畜解馋,因为在此之前,牲畜们只能吃麦草的青储。
到了夏天,祖父喝过早上的罐罐茶之后,就带着镰刀,推着架子车朝苜蓿地里走。这时候,露水褪去,苜蓿变得柔和,喂给牲畜能吃出鲜嫩和清香。很快祖父就拉着半架子车的苜蓿回来了,我最怕跟祖父铡苜蓿,拿比我还高的铡刀,被我两只手死死攥住,使劲摁下去的时候,刀刃上就弥漫出一股清香。
割苜蓿,铡苜蓿,看牛吃苜蓿,成了我乡村记忆中最具体的细节。小时候,我原本以为祖父会割一辈子苜蓿,我也会一直在苜蓿地里摸爬滚打,谁知道祖父到了古稀之年的时候,我们家就不再养牛,苜蓿地后来变成了荒地,一地的碎花苜蓿就此消隐。
当我再次和一株苜蓿相遇时,才意识到,苜蓿这个意象已经在视野里消失很久了。现如今,祖父早已长眠于曾经种过苜蓿的那块地里,而成群的牛羊也从我的村庄消失。物是人非,叹息毫无意义,其实,我更为好奇的是,苜蓿消隐到了哪里?
苜蓿最早应该消隐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里有线索,王逸曰:“张骞周流绝域,始得大蒜、葡萄、苜蓿。”随后,它在中国落地生根,《史记》里说,汉朝时“离宫别观旁尽种葡萄、苜蓿极望”。一个“极望”,可见当时苜蓿的种植之广。在传入中国之前,苜蓿被古希腊人视为神圣的植物,用于祭祀和喂养马匹。而到来中国,它的命运发生了转变,从神圣之物变成亲民的植物。
要想在贺兰山寻找苜蓿的踪迹,马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贺兰山和马有着不解的渊源,它的得名就和马有关。唐朝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志》写道:“山多树林,青白望如驳马,北人呼驳为贺兰。”如果将马的踪迹置于贺兰山,能看到一条清晰的王朝更迭脉络:不管是春秋战国时期,活跃在贺兰山一带的游牧民族义渠戎,还是在贺兰山一带设置上定郡的秦人,抑或汉武帝时先后进行大规模的移民,都把贺兰山当作重要的游牧区与养马地。一直到清代,随着大量的移民来到宁夏,贺兰山周边才逐渐成为重要的农耕区,统治者最终放弃了持续在此地延续了千年的牧马业。
贺兰山已经见不到野马的影子,散养的马也早退出了贺兰山保护区,要想寻找马的踪迹,只能到岩画中去。在贺兰山数以万计的岩画中,马和鹿图案为主的可辨识度最高,最近几年,石嘴山市境内的贺兰山深处,还新发现了一幅古人驯马的岩画。画面上,马体形态趋向肥硕,形象逼真。磨刻和凿刻结合的制作手法之下,这匹风格粗犷,线条古朴流畅的骏马,让人浮想联翩。可惜,汉朝时才从西域引入中国的苜蓿,没有机会以线条的形式永久留在贺兰山。它们从落地那一天开始,经过一个漫长的生长期,现在,散落在东麓的苏峪口、黄旗沟,散落在西麓的哈拉乌北沟、北寺沟,成为贺兰山植物群中的隐者。
苜蓿曾长期隐匿在诗歌里,元代著名诗人马祖常的《灵州》一诗中:乍入西河地,归心见梦余。葡萄怜酒美,苜蓿趁田居。从诗中可见,汉朝时“离宫别观旁尽种”的葡萄和苜蓿,在贺兰山下落地生根。我见到的这一株,应该是它的后代,只不过它有些孤独,有风吹过来,它就随风起舞;开花的时候,它努力地为蜜蜂提供这蜜源;而更多的时候,它则隐士一样,躲在石头堆里看云卷云舒。苜蓿虽然不是贺兰山最耀眼的存在,但一定是最逍遥的隐者。它是孤独的制造者,也是孤独的享受者;它本身就很孤独,因为它是孤独本身。
其实,它最大的本事并不是孤独,美国著名诗人艾米莉·狄金森曾写道:造一个草原/要一株苜蓿加一只蜜蜂/一株苜蓿,一只蜂/再加一个梦。艾米莉·狄金森一生写过嶡草、鸢尾花、野蔷薇……但只有在写苜蓿的时候,它才写到要去造一个草原。是的,苜蓿是有这种能力的。作为可以改良土壤及作物育肥的植物,苜蓿将根扎在贺兰山的时候,它就把自己变成世界上最小面积的草原,它用碧绿而纤细的茎生出心形的叶子,用绿和紫色,为蜜蜂和蝴蝶指路。我不知道艾米莉·狄金森最后有没有用苜蓿种出一片草原,但是读到这首诗的时候,我的心里早就是一片苜蓿肥嫩油绿地开放了。
苜蓿从舌尖永久地隐匿了。我最喜欢的散文作家汪曾祺,写过一道美味叫草头,这是上海人的叫法,他们的吃法是“多放油,武火急炒,少滴一点高粱酒”。而六盘山区的人称其为苜蓿芽,吃法简单质朴:清水焯过之后,撒少许盐,倒少许油,搅拌过后就馒头吃。贺兰山上没有成片的苜蓿,我也早就错过了吃苜蓿芽的时候,不过上网搜索,竟然有储藏的苜蓿,赶紧下了一单,是春天采摘之后,冷冻的苜蓿芽。在按照乡下的做法烹制之前,我早早买好了热馒头,可是,一口塞进嘴里,却并不是童年的味道,我不知道是因为冷藏过程中味道受了影响,还是我的舌头已经忘了苜蓿最初的感觉,总之,网购的苜蓿芽,吃起来满是疑惑,并没有带我回到童年。后来,我在银川市区的某个餐厅的菜单上也看到过苜蓿,但被厨师告知,由于货源问题已经很久没做了。看来,苜蓿从舌尖上隐匿了。
作为多年生的草本植物,苜蓿属在贺兰山共有四姐妹:花苜蓿(野苜蓿)、紫花苜蓿、天蓝苜蓿和阿拉善苜蓿。花苜蓿(野苜蓿)分布于東麓苏峪口沟、黄旗沟;西麓南寺沟、镇木关沟。紫花苜蓿在东西两麓的一些沟谷、河床及路边可见;天蓝苜蓿则分布于东麓苏峪口沟、拜寺、黄旗沟和西麓的哈拉乌北沟。而以贺兰山的地名命名的阿拉善苜蓿,则彻底地消失了。作为贺兰山重要的优质牧草植物,为贺兰山山麓特有种,原本分布区极小,种群数量少,野外已很难见到,植物研究者经过数十年的寻找均未找到踪迹,不存在模式产地的植物标本,因此判断已处于灭绝状态。究其原因,《贺兰山植物志》中只有短短的一句话:由于城市建设和土地开垦。
因一株苜蓿,翻出了记忆里的苜蓿,以及隐匿在历史长河中的苜蓿。这外来之物,从最初的马饲料,到现在的药用植物和美味佳肴,从家乡最熟悉的植物到贺兰山上孤独的身影,它的转变,不仅仅是一种食物的演变,更是中华文化包容与融合的最好证明;不仅仅是一个游子对故乡的回味,更是一种对苜蓿身份的重新确认。其实,不管是隐匿在诗歌里,还是菜单上,在我寻找消隐的苜蓿的过程中,它早已经悄悄在我心里开了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