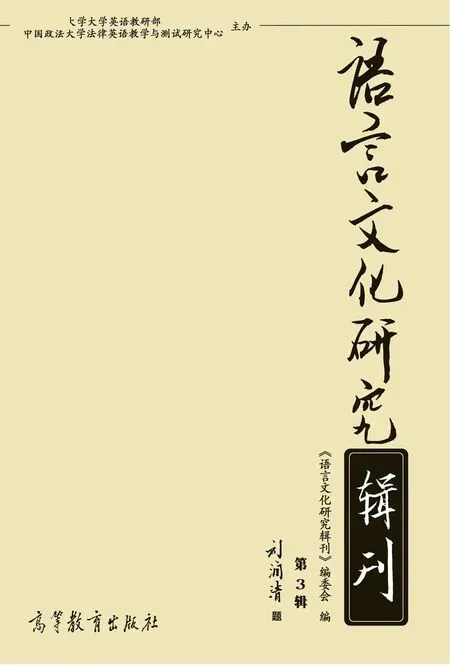科技外语事业半生缘
——李亚舒教授访谈录
李亚舒 姜育(中国科学院《中国科技翻译》编辑部,北京100864;首都师范大学大学英语教研部,北京100048)
科技外语事业半生缘
——李亚舒教授访谈录
李亚舒[1]姜育[2]
([1]中国科学院《中国科技翻译》编辑部,北京100864;[2]首都师范大学大学英语教研部,北京100048)
[编者按] 李亚舒,1936年生于湖北公安,祖籍湖南湘阴,中国科学院教授、科技翻译家、文学翻译家、楚国文化研究者、全国科技名词委员会新名词委员会理事、《中国科技翻译》期刊顾问。历任中国科学院外事局国际组织国际会议代理处长、外办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亚非拉美处处长、中国科学院国际学术交流中心翻译部主任、《中国科技翻译》期刊主编、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兼科技翻译委员会主任等职。李亚舒教授主要从事中外文化对比、翻译理论、翻译实践、翻译史、国际学术交流及管理研究等,尤其在科学翻译和应用翻译研究领域成就斐然,与黄忠廉、方梦之等创立科学翻译学、应用翻译学,并撰写相关著作。
李亚舒教授于解放初期考入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于1956年赴越南河内综合大学文学系学习,毕业后经历半年研究生学习,于1959年底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先后担任《亚非文献》法文和越文编辑、中国科学院外事局翻译、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项目官员、外交学院中国科学院外事干部培训班主任等工作,于80年代兼任《科技计划译丛》和《中国科技翻译》期刊常务副主编工作,并在该刊荣获“国际译联1990—1993年度最佳国家级翻译期刊奖”时,又于1993年获得中国科学院颁发的“突出贡献奖”。40多年来,李亚舒教授积极参加国内外学术活动,参团、组团或带团访问亚洲、欧洲、美洲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将这些经历很好地融入学术研究之中,先生先后翻译500余万字,发表论著150余篇(部),发表文学作品30余篇。
李亚舒教授的作品主要有译作、著述和文学创作三大类,其代表作品(不分时间先后)参见下表:

译著 著述 文学创作《那些富利的人们》 《印度科学技术的发展》 《鲜花》《越南的女儿》 《新加坡的科技发展与管理研究》 《爱情》《通往友邦之路》 《加强世界语实践与理论思维研究》 《一个美好的愿望》《海鸥》 《中国科技翻译学的科学内涵》 《诗怪胡春香》《从原子到生活》 《译海采珠·科学家谈翻译》 《从清水塘到中关村》《亨利六世(第三部)》 《中国科学翻译史》 《虎渡沙畔忆童年》《越南阮氏王朝社会经济史》 《科学翻译论著新萃》 《母亲微笑的记忆》《熄灯》 《新英汉缩略语大词典》 《赞芬芳桃李爱桃李芬芳》《晚秋时节》 《科学翻译学》 《我的领导和战友》《应用翻译学》
纵观李亚舒先生的学术历程,他历经祖国和留学期间的爱国文学创作,到越南、新加坡、印度的科学技术与管理的译介,由口笔译实践走向理论的思辨,最终走向科学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的学科构建,遵循着科学发展观和人类认识世界的思维规律,从感性思维走向理性思维,从实践上升到理论的修正和构建,体现了科学工作者的人文关怀和人文学者的科学精神,可谓中国科技外语工作者的辛勤园丁。
恰值李亚舒先生80寿辰临近,首都师范大学大学英语教研部于2014年11月27日邀请先生为全体教师做“为学”讲座,英国伦敦大学语言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大学英语教研部姜育老师借此机会,就李亚舒先生的半生科技外语情缘做了专题访谈。
姜育:李先生好,很高兴今天您能做客首都师范大学,刚才在讲座中您为我们讲解了翻译学研究、论文写作和发表的相关事宜,为青年教师又一次树立了翻译学研究的榜样。请允许我代表我的同事再次向您表示感谢。接下来我想对您就学习和翻译工作的心路历程做一次访谈,让我们青年教师有进一步认识您、了解您的机会。您是中国外语界的“老兵”,也是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培养出的知名学者。您能否谈谈求学经历对您为学与为人的影响,特别是当时北京大学的哪些人和事对您影响比较大,令您印象最为深刻?
李亚舒:当我在湖南长沙一中念高中时,我们的语文老师经常挽着学生的手在清水塘畔毛主席与杨开慧新婚驻地散步,特别是对那些发现有爱恋苗头的学生时,老师一手挽着一个,边走边讲着毛主席湘江游泳初到北京的故事,还提醒着我们这是毛主席走过的路,我们都觉得兴奋和自豪。毕业后,我和同学大多考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八大学院,来京后我们还会定期见面、聊天。我进入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学法语,当时我们系只有英语、法语和德语,系主任为冯至先生,法语老师有吴大元、罗大纲、齐香等名人,助教为桂裕芳。我记得齐香老师还非常漂亮,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上课时要化妆、擦上口红,让当时我们这些从小地方来的学生感到很惊奇。时常能听到王力、高名凯等名家的大班讲课,所有北京大学的这些老师,做学问都很严谨,北大提倡的科学与民主精神令我们终生受用。
姜育:离开北京大学后,怎样的契机让您选择赴越南河内综合大学文学系学习呢?在越南,您主要从事哪方面的学习和研究工作?
李亚舒:北京大学肄业时,我又学了几年的英文,不是从ABC开始,因为中学六年我都是学的英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年的这个情况,以前也有记者访问我,其实我的专业学习完全是根据组织需要。我个人很喜欢北京大学。印支战争结束后,毛泽东主席和胡志明主席发表了联合声明,中国派了很多专家去支援越南,能去外国留学,到哪个国家去都觉得很光荣,所以应该说留学是国家的需要。我们这一代人主要是国家安排出国培养,国家有需要,我就会服从国家安排。在越南大约三年多,即从1956年初到1959年底,主要从事越南语言和文学方面的学习研究。使馆当时很关注我们继续学习法文,要抓紧学习越南语言和文学。我们到那儿时,课堂上用的法文资料多,河内市面上也可以用法语交流,如采购,我们开始连一句越语都不会说,但可用法文跟他们交流,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是公共场所,如书店。使馆当时给我们专门聘请了法语老师,越语是一直跟着班上学的,而法语有单独老师上课。跟我一起去的还有北大同班同学,后来他们有的分配到外交部做翻译工作。
姜育:回国后,您到中国科学院从事与外语相关的翻译、编辑和行政工作,您能否谈谈外语相关工作的甘苦,也想与您分享一些文化与翻译相关工作的经验与教训。
李亚舒:曾有一段时期,提倡知识分子要做“驯服工具”。回国后,正是国家教育改革大转变的时期。一般来说,我们是分配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所以到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院当时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学部。当时,我们搞了一个刊物叫《亚非文献》,根据组织上安排,主要为社会科学学部服务,这个刊物是各种文字都可以出版,因为编辑部里面有几位很有经验,当过老师或做过相关编译工作,且都是从国外学习回来的。我之所以承担了里面的英语、越语和法语的编辑工作,主要是因为身边有老师可以请教。其中齐勤老师,她是我原来在北京大学的老师齐香先生的妹妹。齐勤先生把我也当学生一样,我可以随时请教她,我周围的一些老同事也是这样,把我看成是小弟弟一样。我们周围还有老翻译,像原来协和医院的强一宏老先生,新中国成立前做过多年翻译,搞外文资料很有经验,他的子女先后都参加了革命,后来有的在石景山钢铁公司当了处长,有的还当上了高工。所以,我觉得进入中国科学院不仅是工作,也是一个继续学习的机会。当然,我个人喜欢搞点写作,搞点创作,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受欢迎,都是要求一心搞外语、搞文献、搞资料。从事这些工作的女同志占多数,男同志年龄小,身体也好,所以常在第一线劳动,比方说在北京郊区植树造林,包括到长城脚下、居庸关前十三陵地区,我们在荒山上挖坑,然后种果树。
关于文化与翻译问题,我觉得搞外语的人都希望能看外文原版书,开始想翻译的念头很少,但社会有这个需要很普遍的情况是:你会的文字或知识,人家不懂,这样就可以选一些书来译。像我翻译的越南小说《熄灯》,作者吴必素是比较有声望的作家,且社会影响较大。还有诗歌,我当时也翻译了诗歌散文,主要是那些跟国家接近和拉近两国关系的,像建国十周年出版的一本书《越南的女儿》是我与当年北大同学一起翻译的诗文集,于1959年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是介绍越南人自己的抗美救国斗争,还有写两国友谊的《通往友邦之路》,这是在《世界文学》上发表的,后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
姜育:您早年翻译了不少文学类作品,如《越南的女儿》、《那些富利的人们》《通往友邦之路》《海鸥》《熄灯》等,后来转向科技翻译,如《印度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科技翻译学的科学内涵》《中国科学翻译史》《科技翻译论著新萃》《科学翻译学》《应用翻译学》等,您能否谈谈前后转变的契机与从事科技翻译的心路历程?
李亚舒:这个转变主要是因为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国家培养的,因为我上学领助学金,家里是不可能培养我成这样的,所以就一直有着一个观念:我是国家培养的人,要为社会干点实事。到了工作岗位以后,在中国科学院这个岗位,原来我想搞社会科学,但老同学在社会科学里面遇到许多困难,劝我打消搞文的念头。“文化大革命”之前是“四清”运动,就是下到农村去,先是去安徽合肥的肥东县,后来又到寿县,到了这两个地方都是进到公社,先是劳动,跟农民三同,就是同吃、同住、同劳动,“三同”时期也就是全国经济比较困难的时期。当时全国知识分子都一样,都要接受劳动改造,因为我年轻一点,所以劳动更多一些。1964年回京后,参加天安门广场检阅,曾专门接受了半年的军事训练。当时,我们是中国科学院的首都民兵师中国科学院民兵营的方阵队伍。在这种情况下,来中国科学院后,我们不是参加劳动,就是参加社会活动。所以,“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下农村时间比较长。1969年林彪的“一号”通令,大家都要疏散,接着是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大家都要下乡劳动,学生、知青也要上山下乡。所以,我在“五七干校”时间比较长。当时,中越联系比较多,胡志明健在,中越两国两党的关系都比较好,越南不断有代表团来中国,另外也还有其他国家代表团,如法国。越南华侨和海外华侨也会比较活跃地访问中国,由于外方代表频繁访问中科院,我也就接受了组织上的安排,更多地参与涉外任务,做翻译工作。所以,一年下来,在乡下劳动的时间一共也没几个月。另外,也由于劳动期间,因为下水沟挖污泥,得了膝关节炎,不能再参加当时的劳动,有一段时间就回北京了,承担了翻译、接待外宾的工作,参与这类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姜育:如此看来,您当时的转变与今天的知识分子有所不同。您曾任中国译协副会长兼科技翻译委员会主任、中国英汉语对比研究会副会长。自1980年代,中国南北有两大科技翻译平台,一个是方梦之教授主编的《上海科技翻译》,一个是您曾任主编、现任顾问的《中国科技翻译》,前者现如今已改称《上海翻译》。面对中国翻译研究现状,《上海科技翻译》改称《上海翻译》。为何《中国科技翻译》没有更动刊名呢?
李亚舒:刊物的名称当时是经过很多学者包括一些院士参与论证的,我们的局长崔泰山教授懂多门外语,本身是朝鲜族,母语是朝鲜语,汉语也相当好,日语水平也相当高,可以讲非常地道的日语。因为局长年轻时参加了抗日战争,爱国心很强。他夫人常沙娜是中央工艺美院院长,艺术细胞很强,因为她是著名学者、旅法归国的常书鸿先生(任敦煌研究所所长)的女儿。除了这样的背景,他曾担任郭沫若院长的秘书,他喜欢文化,字写得非常好。至今,我们刊物还在用他写的刊名题词,这是其一。其二就是一些学者一直认为,当国家落后时,科学技术就落后。科技的翻译也是一门学问,既是引进也是输出,如果没有一定知识水平的人,想把别人的东西翻译过来也是有困难的。所以,翻译不是一个仅母语好就行的问题。科技翻译是社会的实际需要,也是国家的现实需要。科学院是全国自然科学研究中心要率先实现科学技术的跨越发展。如果我们要把它变成社会科学的刊物,就不会放在中国科学院里了。中国科学院也很珍惜这个刊物品牌,《中国科技翻译》作为国家一级刊物,在翻译领域曾获得FIT①FIT系国际翻译家联盟(国际译联)的法文缩合词,即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 des Traducteurs。最佳国家级翻译期刊奖。正如大学英语教学部邱主任所讲,这个不是一个人的努力,是国家的声望,是很多作者和编辑的共同努力。当然获得的奖,拿到的奖状,是与我们编辑部中几个做实际工作比较多的主编、副主编和整个理事会的支持分不开的。当时,我们理事和编辑阵营中就包括了一些院士。
姜育:就目前而言,中国翻译学界紧跟国际译学大潮流,引进和融合了很多新的翻译理论。面对这一境况,您认为中国科技翻译研究在中国翻译研究及英汉语比较研究领域处于怎样的地位?中国科技翻译研究的前景如何?
李亚舒:我认为中国翻译研究和英汉对比研究都是向前发展的,这是因为我们国家有一批老前辈、老翻译家确实做了很多工作,有很多贡献,后来他们注重培养学生,所以接班人实力相当雄厚。拿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这个机构来说,创始人是刘重德教授,他是西南联大的毕业生,抗战的时候,他跟着北京大学先到了长沙,继而去昆明西南联大,当时穿着草鞋走了一个月。刘重德先生做了很多翻译和教学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长沙从教,在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离休。他觉得翻译研究不够具体,要培养接班人,英语、汉语各有特点,应该怎么去研究,所以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设立了三大研究板块:语言对比、文化比较和翻译研究,每个板块的学术委员会负责人都是学有所成的专家。历任会长都是国内外闻名的学者。刘重德是第一任会长,第二任会长是中国海洋大学的杨自俭,第三任会长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潘文国,第四任会长是清华大学罗选民,他同时兼任国内外多所院校特聘教授或刊物主编。就目前来看,接班人都是一代一代继承和发扬文化传统的。英汉语比较研究会成立20周年之际,我填了一首词《满江红》,在会上致辞时朗读了,后来印发了①该词参见《文化艺术报》,2014年9月10日第三版。学会的正副会长和理事都在会上写了许多诗词。1。很多年轻人说,怎么搞科技翻译的会写这个?有些年轻人不了解,我们原来的教育就是要求在学生阶段,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特别是,喜欢外语的人,母语基础一定要好。要是国学基础不好,外语再深学,很多时候都是有欠缺的。
姜育:近几年,政府倡导国学复兴和中国文化走出去。作为翻译界的资深专家,您如何看待中国母语者外译中国文化典籍这件事,特别是中国外语界要以中国少数民族典籍汉译本为原本从事外译工作?
李亚舒:我认为中国典籍翻译工作做得很好,国家现在有专款用于典籍外译,如南开大学王宏印等学者做了很多工作,出了书也开了多次研讨会。我个人认为,中国典籍应该包括兄弟民族的作品。因为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我们少数民族有的没有文字,有的有口述文学,还有的有文字,也没有很好的记载,所以是靠不同的人流传、记述下来的,如壮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的故事,是三天三夜都讲不完的。这些故事、长诗有的可以演唱,同时文学价值也比较高。这些你不能说不是中国文学,否则就等于否认我国自己的东西,我们子孙后代自己都不承认了,国人会说岂有此理?!因此,重视兄弟民族文学,这对于民族的团结,对于民族文化的发展,这都是很需要的且是相当必要的。
当然,我们不可能说让兄弟民族的语言得到普及,不能像有些国家可以有好多种官方语言,因为每个国家的历史状况、历史发展都不一样。所以,我认为任何排斥兄弟民族的语言或文学①此处的文学概念属大文学概念,包括民俗、文化、政治、经济、历史等的作品。的做法都是不理智的,也是绝不会允许的。此外,重视发展兄弟民族文学,还有现实意义。现在,国内外有疆独、藏独、台独等少数反动势力都在想方设法寻找各种机会来破坏中华民族的团结。如果文化部分我们可以把握,兄弟民族可以扬眉吐气,这样对中国的发展、中国国力的增强最有好处。因为我们的领袖和我们的人民也曾是被制压的人,看到别人犯过的错误,我们不能重蹈覆辙。
姜育:您跟黄忠廉和方梦之先生主编的《应用翻译学》,引导了中国翻译本土化的进程,您对《应用翻译学》是怎样评价的?对应用翻译学的发展态势持怎样的观点?
李亚舒:首先,我跟黄忠廉、孙秋花联袂发表了《方梦之应用翻译理论形成考》(见《上海翻译》2014年第4期),从其基点、支点、拐点和亮点四方面指出,方梦之是应用翻译研究的领军人物,因为多年来,他一直是应用翻译理论建设的实践者和倡导者。请有兴趣的读者阅读全文,这里不再重述。但是,我仍乐于回答你的提问,并想借此机会再说一点意见。方梦之先生是很值得我学习和尊敬的学者,他翻译过多种文献,俄语不错,后来转为英语。原来,我们都是做科技翻译的,所以他主编的期刊原名是《上海科技翻译》。后来,随着学习和理论的深入,翻译学出现两个趋势,一个偏向理论,一个侧重应用。大家都知道,2004年黄忠廉与李亚舒合著《科学翻译学》,已在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多次再版。我们在《科学翻译学》中提出“科学翻译”的定义,认为文学翻译之外的翻译研究都可归到这一范畴,包括语言、经济、法律等。现在的“应用翻译”与“科学翻译”的命题,没有明显壁垒,却有“殊途同归”之感,即将多年来科技翻译期刊的研究成果融于一体,建构了它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层次性。
我们谈应用翻译离不开方梦之先生,他是为中国应用翻译学的建立和翻译教材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人。第一次应用翻译研讨会于2003年在上海召开,第四届于2013年在西安召开,我已参加了四次,每次都看到了他的卓越贡献。第五届于2015年在上海召开。实际上,应用翻译学主张:翻译不能没有理论,但翻译不能没有实践。所谓实践就是应用的实践。实践理论提高了,升华了,就变成应用翻译学。这个提法也是跟国外接轨的,并不矛盾。更何况,《应用翻译学》第一部专著已经出版了,里面除了方梦之、黄忠廉和我本人在总论里提出这个框架,其他参与的学者基本上都是博士、博导、教授,这在该书序言中都做了清楚的交代。至于我参与的一点儿工作是微不足道的,主要是方先生和黄先生,他们把自己的学生和青年朋友都带进来,一起来丰富了这个学科,但还留有空间,还没有达到完善地步,这本书还有一些领域没有涉及。虽然已经约稿,但时间不等人。比如说,研究应用翻译学时还应该谈到与新世纪同步的生态翻译学,胡庚申先生从生态这个角度研究翻译学是很有见地的。作为学术来讲,他有自己的创新,还有天津理工大学的许建忠教授,他们在不同的方面发展了翻译的理论和实际运用。
《应用翻译学》这本书既符合现实需要,又有发展的空间。无论是典籍翻译,还是文化走出去的想法,如果没有理论指导,都是不行的。我们要把这个哲学思想、方法论,甚至是宗教的翻译,都可以有意义地树立,有导向地出些成果。这样对学生也有目标,对翻译对应用有引导。至于翻译什么,年轻人兴趣广泛,很有创造性,但为了早出创新人才、早出创新思想、早出创新成果,老中青相互学习,会增加一些优势的互补性。
姜育:最后,作为中国外语界核心期刊的资深编审、译者和研究者,您积累的经验和教训,能否给中青年学者分享一下?或者说您对中青年翻译研究者寄予怎样的厚望?
李亚舒:首先,在学术上,不能搞论资排辈,要提倡互为人师。我自己是边干边学,在包括有年轻人的帮助下一路走过来的。另外,青年译者要善于交朋友,善于发现朋友。年轻人敢想、敢说、敢做,是很有发展潜力的。但他们也要分清不同时期、不同单位和不同个人存在的实际困难或实际问题,或者说,在这个形势发展比较快的时候,对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要有所鉴别。要克服急躁情绪,不能浮躁,一个潜力巨大的年轻人要不断充实自己。应提倡多读书、读好书,要善于勤学苦练,要有信心坚持做一些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不要半途而废,中途放弃,因为持之以恒对我们来说才能出创新成果。一般来说,这也是规律。
目前,引进的学术思想很多,很需要像杨柳博士那样认真进行梳理,要有理性地接受或吸收。如果今天一个概念,明天又一个概念,就值得深入思考了。因为现在出现的很多概念的质量是有问题的。我们现在提出年轻人走出去,我认为是把中国的优秀文化带出去。如果我们不读书,不看报,不与时俱进,那我们怎么能把握好现在的形势,我们能担当什么继承和发扬的重任呢?我认为走出去就是继承和发展,也就是跟着祖国的前进而前进,跟着祖国的发展而发展。
我愿意跟年轻朋友们携手与时俱进,继续努力,继续学习。
谢谢大家!
李亚舒(1936—),男,湖南湘阴人,曾在北京大学、越南河内综合大学等校求学,中国译协副会长、中国英汉对比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科技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教授、《中国科技翻译》顾问。研究方向:中外文化对比、科学翻译史、科学翻译学、应用翻译学等。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52号《中国科技翻译》编辑部(100864)。Email: liyashu@cashq.ac.cn。
姜育(1977—),女,黑龙江哈尔滨人,英国杜伦大学语言学硕士、英国伦敦大学语言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大学英语教研部教师。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第二语言习得、语言教学等。联系地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05号首都师范大学大学英语教研部(100048)。Email: jiangyu@acecafe.com.cn。
——李振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