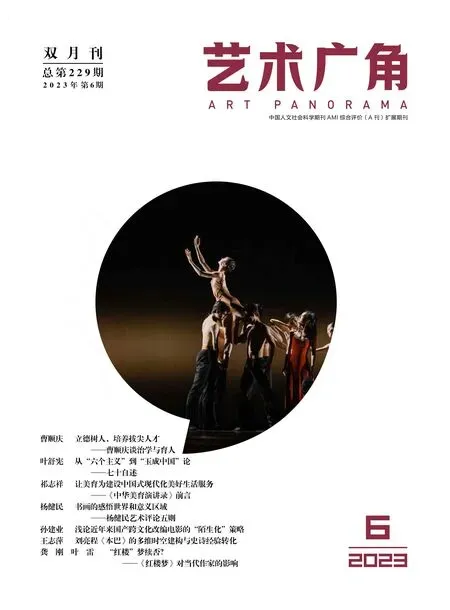《西游记》妖魔形象塑造的根源探究
汪平川
纵观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史,神魔小说作为一支风格独具的流派,与历史演义小说、人情讽刺小说鼎足而立。自明代中叶《西游记》《封神演义》问世以来,此类作品风行于世,获得了学者青睐和读者喜爱。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论是以某个历史事件或人物事迹为故事背景的史话类小说,还是以释道两教和民间神魔传说为叙事题材的佛道类小说,抑或是借幻讽世、针砭时弊的寓意讽刺类小说,或多或少都能从中找到这两部经典著作的影子。
作为明代神魔小说的巅峰之作,《西游记》在唐僧师徒的取经路上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妖魔体系,动则鱼虫鸟兽,静则花木器皿,世间万物皆可成妖成魔。他们有的是松、柏、桧、竹等植物扮妖,附庸风雅;有的是蝎子、蜈蚣、蜘蛛等小动物得道,兴妖作孽;有的是虎、狮、象、豹等猛兽成精,称王称霸;有的是神佛童仆、坐骑、豢养物等背主出逃,惹是生非;有的是天上星宿私下凡尘,为非作恶……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些妖魔中,除了少部分是自然界中的生物成妖,绝大多数都与神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鲁迅说,“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 页。。作品虽通篇讲述的是唐僧师徒斩妖除魔的神话故事,却处处弥散着人间烟火气,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吴承恩以志异的笔法勾勒出神佛与妖魔间复杂交错的关系,旨在对现实社会中丑恶现象进行审视。本文尝试聚焦《西游记》成书时期作者生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探究其塑造这些妖魔形象的根源。
一、研究背景及总论
神魔小说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六篇“明之神魔小说”:“且历来三教之争,都无解决,互相容受,乃曰‘同源’,所谓义利邪正善恶是非真妄诸端,皆混而又析之,统于二元,虽无专名,谓之神魔,盖可赅括矣。”[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年版,第111 页,第257 页。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他对此做了一番阐释:“在小说中所写的邪正,并非儒和佛,或道和佛,或儒释道和白莲教,单不过是含糊的彼此之争,我就总结起来给他们一个名目,叫神魔小说。”[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年版,第111 页,第257 页。
回顾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历程,神魔题材历来备受小说家的青睐。兴起于明代时期的神魔小说,继承了上古的神话传说、先秦两汉的谶纬之说、六朝的志怪小说、唐代的变文,以及宋元时期的说话艺术等众家之所长,在明代文坛异军突起,尤其在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到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盛极一时,在全社会掀起了一股创作热潮。继《三遂平妖传》首开先河,《西游记》《封神演义》《三宝太监西洋记》《镜花缘》等作品不断涌现,各个时期的作品数量多达80 余部。其中《西游记》和《封神演义》最负盛名,是中国古代幻想文学的登峰造极之作,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于神魔小说概念的厘定至今在学术界仍未取得统一意见,因此当前出现了多种称谓并存的局面,如“神怪小说”“神话小说”等。尽管如此,并未消减学者对该类作品的关注,尤其近二十年更是呈上升趋势,产生了大规模的评论文章。这些文章主要从小说史、专门论著和小说文本等方面进行探究。关于小说史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丰厚成果,林辰的《神怪小说史》[3]林辰:《神怪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胡胜的《明清神魔小说研究》[4]胡胜:《明清神魔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版。、邹壮云的《论明代神魔小说的发展历程》[5]邹壮云:《论明代神魔小说的发展历程》,《学术探索》2013 年第6 期。,分别对此类小说的发展历程、文化渊源等作了系统性论述,从中我们能一窥明清神魔小说的大致面貌。关于小说文体方面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冯汝常的博士论文《中国神魔小说文体研究》,文章选取题材的幻神特征、命意的主体转向、人物的行动者功能与结构的时空建构模式等作为分论题,以神魔小说作品为依托,从文体视角对神魔小说构成进行创新性理论探析。[6]冯汝常:《中国神魔小说文体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 年。关于具体小说文本的研究则呈现多点开花的局面,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西游记》《平妖传》《绿野仙踪》《封神演义》等几部家喻户晓的经典作品上。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和胡适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7]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书店,1980 年版。最受推崇,两位前贤的研究角度和方法亦被后继学者纷纷效仿。然而,这些研究尚有两点缺憾:其一,多数研究缺乏从宏观层面对明代神魔小说创作情况的系统剖析,只停留在针对具体作品解析的微观层面;其二,针对神魔小说的历史沿革及编创方式,虽个别文章稍有涉及,但总体上仍有较大局限性。
根据以往对《西游记》的研究来看,研究者普遍认可的是作者对妖魔形象的塑造绝非信手拈来,必定隐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时代意义。然而,目前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对反腐意义的挖掘还不够深入。因此,本文旨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作者塑造妖魔形象的根源进行研究,拓宽对文本思想内核的认知,深化对文本主题的解读,着力从新视角探究文本中蕴含的艺术成就。
二、文献综述
关于《西游记》妖魔形象塑造的研究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其中,东北师范大学齐晓芳的硕士论文《论〈西游记〉中与神佛有关的妖魔形象》,通过对妖魔形象的分类研究,探析了这些妖魔形象塑造的原因、意义及对《西游记》艺术成就的影响[1]齐晓芳:《论〈西游记〉中与神佛有关的妖魔形象》,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年。;唐艳华的《〈西游记〉中的神佛与妖魔关系之探析》,运用辩证统一的方法探讨了神佛与妖魔之间的复杂关系[2]唐艳华:《〈西游记〉中的神佛与妖魔关系之探析》,《新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 年第4 期。。此外,李丰霖的《〈西游记〉中塑造妖魔形象的艺术手法探究》[3]李丰霖:《〈西游记〉中塑造妖魔形象的艺术手法探究》,《产业与科技论坛》2012 年第17 期。、柯霁阳的《神魔世界里的人性探索——〈西游记〉主题新说》[4]柯霁阳:《神魔世界里的人性探索——〈西游记〉主题新说》,《名作欣赏》2017 年第7 期。、刘春霞的《浅析〈西游记〉小妖类别形象》[5]刘春霞:《浅析〈西游记〉小妖类别形象》,《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2 年第6 期。、樊文富的《从〈西游记〉孽畜的保护伞说开去》[6]樊文富:《从〈西游记〉孽畜的保护伞说开去》,《政工研究动态》2002 年第16 期。等论文,从多个维度和层面对妖魔形象塑造的艺术手法和现实意义进行了探讨。
关于《西游记》反腐方面的研究总体还不够充分,相关文献较为精短,尚未见到较为深入、完整的理论研究。多数论文以孙悟空为切入点进行正面阐述,如席金龙的《〈西游记〉中的反腐败意蕴解读》,指出作者成功塑造了一个反抗权威、蔑视皇权、爱憎分明的孙悟空形象,蕴含了鲜明的抗争性和反腐败特色[7]席金龙:《〈西游记〉中的反腐败意蕴解读》,《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 年第3 期。;徐绍华的《无欲则刚:〈西游记〉对反腐教育的启示》,揭露了天界、佛界、冥界、魔界、水界、人界中腐败现象无处不在,倡导世人学习信念坚定的唐僧、无欲则刚的八戒和打虎拍蝇的悟空[8]徐绍华:《无欲则刚:〈西游记〉对反腐教育的启示》,《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8 年第10 期。;叶青的《〈西游记〉反腐的深层意蕴》,指出《西游记》是一曲降妖伏魔反腐济民救世的史歌,妙趣横生的神话故事中闪烁着坚决反腐、铁腕治腐的思想光彩[9]叶青:《〈西游记〉反腐的深层意蕴》,《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 年增刊(增总第7 期)。。此外,部分研究者通过作品创作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生态,探寻蕴含在故事中的政治理念。例如,萨孟武所著《西游记与中国古代政治》[10]萨孟武:《西游记与中国古代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李燕翔的《细品〈西游记〉中的“廉政警示”》[11]李燕翔:《细品〈西游记〉中的“廉政警示”》,《党的生活(黑龙江)》2020 年第8 期。、王银宝的《〈西游记〉政治意蕴探微》[12]王银宝:《〈西游记〉政治意蕴探微》,《安徽文学》2015 年第2 期。、刘玲玲的《论〈西游记〉的政治悲剧内核》[13]刘玲玲:《论〈西游记〉的政治悲剧内核》,《淮海工学院学报》2017 年第3 期。,等等。
以上研究成果有两点不足:其一,关于妖魔形象塑造研究,探讨反腐意义的文章不多,而妖魔作为各种不法行为的主角,恰恰是现实社会中黑恶势力的化身;其二,在反腐意义方面,多数研究以孙悟空的正面形象作为切入点,且只停留在宏观层面,并未曾深入探索作者勾勒不同故事情节背后的深层含义。
三、时代背景与成书原因
小说是时代的镜子。米兰·昆德拉说:“小说是通过一些想象的人物对存在进行的思考。”[14]〔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年版,第136 页。通过探析《西游记》创作的时代背景,研究书中的隐喻和讽刺,我们能更深入地认识作者命辞遣意的内涵。《西游记》选择神魔作为抒情寄志的对象,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作者自身的喜好,也有社会思潮的影响,更为重要的原因则如胡胜在《明清神魔小说创作思想试论》中所言:
“借幻写真”所涉及的对象本是虚幻荒诞的世界,比起那些现实性作品来说,创作者下笔更为自由,殊少顾忌。不管出于哪一种原因,他们笔下的神魔世界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带有某些现实社会的影子。幻想的世界,总是某种现实的摹本。[1]胡胜:《明清神魔小说创作思想试论》,《辽宁大学学报》2000 年第5 期。因此在此类题材小说中,我们时常看到创作者通过个体形象的刻画,狠抽皇权贵族的丑恶嘴脸;通过故事情节的铺排,批判世风日下的社会现实;通过梦幻世界的描绘,抒发自己的雄心壮志或远大抱负。
1.寒门学子怀才不遇
吴承恩自幼是远近闻名的“神童”,天资聪慧,才情横溢,书法、绘画、围棋样样精通。据吴国荣《射阳先生存稿跋》记载,“射阳先生髫龄,即以文名于淮,投剌造庐乞言问字者恒相属”,“比长,读书目数行下,督学使者奇其文,谓汝忠一第如拾芥耳!”[2]苏兴:《吴承恩小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 年版,第12 页。然而,这样一位奋发上进的有志青年,科考之路却异常坎坷,屡次赴考均名落孙山,年过四十的他不得不向命运低头,放弃赶考,经友人举荐出任浙江长兴县丞。但是好景不长,有着雄心壮志的吴承恩无端入狱,几经辗转才摆脱冤狱、重获自由,补授为湖北蕲州任荆王府纪善。[3]王银宝:《〈西游记〉政治意蕴探微》,《安徽文学》2015 年第2 期。所幸在这期间,他创作了《西游记》这部鸿篇巨著。
弗洛伊德说过,幻想往往带有作家早年(特别是童年)的痕迹。[4]〔奥〕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论创造力与无意识》,孙恺祥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 年版,第44 页。尽管起源于隋代的封建科举制度饱受诟病,却一直沿用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才被停废。在这长达1298 年的岁月里,科举制度斩断了众多青年才子的梦想,吴承恩即深受其害。作为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满怀抱负却报国无门,反倒因自己“迂疏漫浪”的个性而遭人嘲讽。在其笔下,我们看到同样被众多规则束缚的孙悟空,宛如作者本人“一世才不见世用”的缩影。二人都是身怀绝学,却壮志未酬,纵使勉强挤进体制,尚未施展才华,就已饱受排挤、无端受难,在饱尝辛酸后,终于凭借恒心和毅力干出了一番大业绩。百炼成钢的孙悟空如愿入列仙班,命途多舛的吴承恩成就传世经典。借用孙悟空的形象,吴承恩悲吐广大寒门学子的苦闷心声,希冀借此唤起社会大众的觉醒。
2.宗教文化多元并存
在明朝时期,宗教文化得到破天荒的发展,统治者多数采取提倡保护和整顿限制兼容并蓄的政策,呈现以佛道为主、各种宗教多元并存的格局。尽管中后期,当朝统治者多数平庸怠惰,宗教保护政策大不如前,但仍以崇信佛教和道教为主,尤其是藏传佛教,比如宪宗佛道兼崇,武宗迷恋藏传佛教,世宗极度崇奉道教。[5]何孝荣:《论明朝宗教的特点》,《福建论坛》2014年第1 期。以儒、道、佛为主的三教融合日渐盛行,儒道互补,儒佛互证,以道释儒,以儒统道,三教合归儒,成为当时封建统治的思想根基。
反观《西游记》,徐扬尚指出,小说中划分的人界、仙界、佛界,相对应的恰是儒、道、释,它们有“相同的等级秩序、对等的价值尺度、相同的游戏规则、运作机制,从而表现出共同的本质特征”[6]徐扬尚:《明清经典小说重读——寻找失落的传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93 页。。在以皇权体系为模式构建的宫廷组织中,不仅人员配备和管理模式高度吻合,甚至连奉行的执政思想都是以儒家倡导的伦理纲常为主体的三教融合理念。不论是“佛”“圣”,还是“仙”,都是作者塑造的“理想人”状态,展现出思想认同、行动服从的姿态,恰是其内心希冀的和谐政治生态。
托名明代文学家李贽的《西游记》评点者在《批点西游记序》和第十三回总批中都云:“‘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一部《西游记》,只是如此,别无些子剩却矣。”[1]朱一玄、刘毓忱:《西游记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245 页,第223 页。而此评点本所署幔亭过客袁于令之《西游记题词》亦云:“言真不如言幻,言佛不如言魔。魔非他,即我也。我化为佛,未佛皆魔……摧挫之极,心性不惊。此《西游》之所以作也。”[2]朱一玄、刘毓忱:《西游记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245 页,第223 页。二者的论述皆阐释了《西游记》倡导修养心性以战胜自我心中魔障的禅意,这是向内的;向外,《西游记》亦通过取经团队的故事演绎了人生处世的现实,并结合现实寻求宗教意义上的自我完善。
四、思想启蒙与创作主旨
政治环境的变革,会引发各类社会思潮的冲突与博弈,并最终在艺术作品中得以体现。深受新思潮启蒙的吴承恩以贴近现实主义的价值观念,接纳世俗社会的理念信仰,从而将所思所想通过文字的渲染酣畅淋漓地表达出来。
1.人本主义思潮涌入
随着文艺复兴运动在西方世界的兴起,社会思潮也加快转型,开始倡导人是现实生活的创造者。随着地理大发现的帷幕徐徐拉开,西方列强将目光转向东方,纷纷利用坚船利炮叩响中国国门,除了资源掠夺和商品倾销,大量商人和传教士带着西方文化进入中国。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700多年前世界著名旅行家、商人马可·波罗亦曾到过吴承恩的家乡——中国淮安,传播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启蒙的新思想。[3]〔意〕马可·波罗(口述)、〔意〕鲁斯蒂谦诺(笔录):《马可·波罗游记》,余前帆译,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 年版,第317 页。可见,当时中国已成为世界新兴思潮的扩张地。
正值这个时期,吴承恩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小商人家庭,沉迹下僚,骥伏盐车,但其不拘小节的性格,有别于其他封建正统学者,愿意触碰那些通俗的小说、戏曲等市井文学,自小喜爱《酉阳杂俎》《百怪录》等狐妖猴精、神仙鬼怪之类的野史小说。而他居住的淮安河下恰是当时淮安最繁华之地,是文人墨客、达官显贵、富商巨贾交游活动的宝地。笼罩在压抑沉闷、腐朽保守、孤寂冷漠的氛围里,人本主义思潮的涌入犹如一股清流浸润着吴承恩的心灵,使其拿起艺术之笔雕琢出那些恶贯满盈的妖魔,借“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反对神权,反对专制”的观念来完成情感的宣泄。
2.阳明心学思潮勃兴
明代中期,程朱理学虽仍占据主导地位,但以王阳明(1472—1529)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从民间入手改善社会生态,确立民间社会的道德信仰,以“良知说”来“觉民行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心学体系,成为明代中叶以后最重要的学术流派。现存最早的百回本《西游记》刊本——金陵世德堂梓行的《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成书于万历二十年(1592),此刊本问世前的那个时期(即嘉靖后期至万历初年间),正是王阳明心学兴盛发展并广泛传播的关键时期。[4]薛梅:《心学视野下的〈西游记〉研究——〈西游记〉与阳明心学之关系研究述评》,《明清小说研究》2009 年第2 期。在这种观点交锋和思潮激荡的大背景下,王阳明的“豪杰之气”为当时思想界注入了新动能,推动了思辨精神和理想主义情怀进入新境界,引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启蒙思潮的走向。
崇尚自由的吴承恩怀有理想主义和思辨精神,很容易受到心学思潮的影响而释放天性、纵情其中。在早些年考证《西游记》作者时,宋克夫从吴承恩与心学人物的交游记录切入,印证了《西游记》与心学思潮间的客观联系。[1]宋克夫:《吴承恩与明代心学思潮及〈西游记〉的著作权问题》,《湖北大学学报》1996 年第1 期。其后,又以收录于《吴承恩诗文集》的诗篇《赠张乐一》作为佐证,证实了《西游记》的主题思想与阳明心学所倡导“反对主体放纵、要求人格自我完善”的主张相一致。[2]薛梅、宋克夫:《吴承恩著〈西游记〉新证》,《明清小说研究》2004 年第2期。沈承庆认为,“从摄魔以‘明心’与摄魔以‘还理’的区别,以及原‘叙’‘还理以归之太初’的性质判断,其与明代内阁首辅李春芳的‘心学’思想相吻合”[3]沈承庆:《话说吴承恩——〈西游记〉作者问题揭秘》,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 年版,第227 页。,而李春芳就是心学门人。毛晓阳则将《西游记》的“心性修持”观与王畿的“性命合一”论进行对比,推断《西游记》的创作或校改是由一位熟知王畿思想或与王畿有亲近关系的人完成的。[4]毛晓阳:《修心与修命——〈西游记〉“心性修持观”与王畿“性命合一论”比较》,《福州师专学报》2001 年第3 期。而王畿是王阳明的嫡传弟子,吴承恩曾在淮安的龙溪书院读过书,这是宣扬“王学”的地方,此书院就是以“王学”代表人物王畿(号龙溪)的名号命名的。
此外,很多论述也指出《西游记》的创作主旨在于人格的自我完善。比如,宋克夫认为,“作者通过孙悟空形象所表明的《西游记》的主体主旨,就在于高度弘扬了主体人格的同时,又要求实现人格的自我完善。这一思想显然来自于‘明代心学’思潮”[5]宋克夫、韩晓:《心学与文学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88 页,第89 页。。又比如,张书绅在《新说西游记总批》中所述:“《西游记》是把《大学》诚意正心,克己明德之要,竭力备细,写了一尽,明显易见,确然可据。不过借取经一事,以寓其意耳。”刘一明《西游原旨读法》也说:“《西游》即孔子穷理尽性至命之学。”[6]宋克夫、韩晓:《心学与文学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88 页,第89 页。二者提及的“诚意正心”“克己明德”“穷理尽性”,无不指向人格的自我完善。而前文提过的“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和“王门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7](明)王守仁:《传习录》下卷,《王阳明全集》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版,第82 页。更是如出一辙,足以见得《西游记》的创作主旨和心学思潮的联系。
五、政治演化与官场讽刺
作为守成之君,明代中后期的皇帝们大多久居深宫,骄奢淫逸的宫廷生活使他们逐渐褪去祖辈们朝乾夕惕、励精图治的品质,对百姓疾苦漠然置之。加之僵化冗沉的选才机制和丧失锐气的官场士人,助长了官场“负能量”的传播,为封建王朝的轰然崩塌埋下了祸根。
1.封建统治腐朽没落
吴承恩生活的那个时期,是明王朝历史上最昏暗、最混乱的年代。当朝皇帝忠奸不分、荒废朝政,权奸宦官、贪官污吏及宗教等势力把持朝政、祸国殃民。内阁、六部和宦官等多股势力分廷抗衡[8]徐祖澜:《法社会学视野下的明代行政法与吏治腐败研究》,《广西社会科学》2011 年第10 期。,皇帝纵然可以一言九鼎定生杀,但在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前皇权亦被无限削弱。上层阶级生活穷奢极侈、横征苛敛,下层社会则哀鸿遍野、饿殍满地,甚至还曾出现“人吃人”的社会悲剧。据明史记载,正德六年(1511)吴承恩家乡淮安便出现过因闹饥荒而人们相食的惨况。[9](清)张廷玉:《武宗传》,《明史》卷16,中华书局,1974 年版,第204 页。统治阶级对底层百姓的剥削和压迫,最终导致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层出不穷。
动荡的社会、萧条的经济、腐朽的官府、苦难的百姓……在作者眼中,统治阶级中达官显宦、权奸贪吏、土豪劣绅和道士妖人正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遂成为其口诛笔伐的讽喻对象。《西游记》描述了唐僧师徒途经诸国皆腐败混乱,有“大小人家买卖难,十门九户俱啼哭”[1](明)吴承恩:《西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1138 页,第814 页。的天竺国凤仙郡,有“文也不贤,武也不良,国君也不是有道”[2](明)吴承恩:《西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1138 页,第814 页。的祭赛国,有国王为了治病杀小儿取心肝的比丘国……吴承恩在《禹鼎志序》中说:“不专明鬼,实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3]刘荫柏:《西游记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版,第70 页。从中便可看出作者对现实社会的极度愤懑。
《西游记》中妖魔的行为特征与明代时期的真实案例间具有较高相似度。第一类“掌公权以谋私利”,如太上老君身旁的金炉童子、银炉童子和文殊菩萨的坐骑青毛狮子奉旨下界却忘记初衷的行为,类似于明廷六部因当朝皇帝包庇纵容而普遍存在的集体贪腐现象;观音菩萨莲花池里的金鱼、东来佛祖面前司磬的黄眉童儿和太阴星君广寒宫捣玄霜仙药的玉兔,借私自临凡冒名顶替、窃取不法利益的行为,类似于明代西南地区土官袭替制度下较为猖獗的“冒袭”现象。第二类“趣相投以恶共济”,如文殊菩萨的坐骑青狮、普贤菩萨的坐骑白象和如来佛祖的舅辈至亲大鹏同流合污,以及东极妙岩宫太乙救苦天尊的胯下坐骑九头狮子伙同其他六只狮子盘踞名山的群魔聚首行为,类似于明廷官吏常以派系、朋党等形式抱团牟利的现象;观音禅寺的金池长老与黑熊精沆瀣一气,以及土地山神为背主下界的金炉童子和银炉童子“轮流当值”的人妖同道行为,类似于明代社会游民秘密结社并与官府相互勾连的现象。第三类“挟天子以令诸侯”,如南极老人星的坐骑白鹿进献女色、裹挟君王的行为,类似于明代扬州地区相当盛行的“养瘦马”风俗(即养女宠);西海龙王敖闰收留鼍龙却随意安置、不管不问,以及托塔李天王收留义女金鼻白毛老鼠精却失于管教的养虎为患行为,类似于那些受情感因素影响所引发的“寄生性寻租”现象。
从现实意义上可以说,《西游记》是一部反腐题材的经典力作,作者笔下刻画的妖魔即是影射潜藏于封建政体的黑恶势力,其强烈抨击的社会之“恶”即封建君主专制下官僚系统的乱象丛生。作者运用象征、比喻、拟人、反讽等艺术手法,巧妙地将弥散于封建政体中的各种歪风嵌入到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故事情节中,将现实案例以艺术的形式展现在读者面前。
2.畸形体制与士人群像
明代中后期,朝廷选才机制日益僵化,当朝皇帝随心所欲,将个人喜好凌驾于制度之上,致使宦官专权和阁臣秉政的现象屡见不鲜。比如:
嘉靖皇帝宠信方士,“青词宰相”严嵩曲意逢迎而得以飞黄腾达,气焰不可一世;万历皇帝沉溺于财色不能自拔,以内阁首辅沈一贯为首形成了一个浙党集团,盘根错节,牢不可破;天启皇帝喜欢木匠,阉党魏忠贤专横跋扈;仅崇祯皇帝一朝,“帝在位十七年,刑部易尚书十七人,吏部易尚书十三人,兵部易尚书十四人”。[4]孟森:《明清史讲义》第2 编第6 章,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6 年版,第414 页。
从大臣频繁更换便可看出明末皇帝选人用人的随意性。为了保住权位,各级臣僚党同伐异、狼狈为奸,附庸在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中以求相互庇护,以各种社会关系为基础结成利益共同体,就连曾享有“封建吏治去污剂”美誉的御史巡按制度,此时也黯然失色,巡按流于形式,“所荐者大贪大恶,而其所劾者小食小过”[5]王春瑜:《中国反贪史》第2 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899 页。。
《西游记》第十七回中,黑熊精盗取袈裟,阻扰唐僧西行,终被观音菩萨以其“一念之差”谋生贪念为由收为守山大神;第二十七回中,白骨精先后化作小姑娘、老太婆和老大爷,施计强行掳走唐僧,孙悟空慧眼识破并将其乱棍打死,却因唐僧肉眼凡胎不识妖精而含冤被逐;第四十回中,红孩儿踞守火云洞,想食唐僧肉,放纵小妖,奴役山神、土地,最终却被观音菩萨收为善财童子……尽管中国禅宗自古讲究“顿悟”,“悟到了便得道,悟不到便亦凡”[1]张执中:《“重复”主题下的“对体”与“轴心”——论〈西游记〉中的黑熊精形象来源及其文化内涵》,《安徽文学》2016 年第7 期。,但是这种未多加考察、就地授予仙职的做法,难免被人质疑众仙选拔的随意性,与皇帝全凭喜好操弄臣僚命运的官场乱象有异曲同工之妙。
混乱的官场生态预示着封建专制终将走向没落。恩格斯曾说:“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种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233 页。市民阶级早已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官场秩序嗤之以鼻,但是朝廷中士大夫们却迂腐守旧,对底层市民的看法不屑一顾。因此,在作者笔下有这么一群妖魔,有神佛的童子、坐骑、豢养物或亲戚,也有下凡星宿被点化为仙,都与神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他们身上,我们仿佛看到了那些与官场密不可分的、不仅失去应有的锐气还助纣为孽的士人群像。
妖魔个个法力高强、兵器精良、人脉宽广,所怀绝技完全不在悟空之下。他们的下界动机不尽相同,有的是奉旨下界,有的是替天行道,有的是迷失自我,有的是怀恨前仇,有的是遗忘初心,还有的是受情欲所困,但无论妖魔因何动机下界,均与神佛的家法不严、管教缺位脱不了干系。他们的最终归宿可分为四类,分别是带回天庭、擒回待审、戴罪立功和皈依佛门,均在神佛的庇护下保住了性命。作者以精妙的笔法塑造了生动饱满的妖魔形象,通过众妖魔设置重重关卡的情节设计和“九九八十一难”的艺术呈现,谱写了一曲宣扬正义、惩治邪恶的壮丽诗篇。
六、经济发展与市民意识
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重农抑商的社会格局加快演变,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商业的繁荣,深受儒学熏陶的进步人士带头公开肯定“商”的价值,商人开始活跃于社会的各个阶层。然而,商品经济带来的市场繁荣,在缺乏约束的封建礼教下,致使奢靡歪风滋生蔓延,反倒激起了底层民众的愤慨。
1.商贸经济与贪风盛行
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发展,明代中国迅速跃居为“世界工厂”,棉布、蚕丝、铁锅、瓷器等商品远销世界各国。生产方式的变革引起观念的更新,刺激了整个社会奢欲的膨胀,社会上刮起一股攀比之风。“正德以前风俗醇厚”[3](明)伍袁萃撰、(明)贺灿然评正:《漫录评正》卷3,胡文焕主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 年版,第70 页。,“万历以后迄于天崇,民多世富,其奢侈乃日甚一日焉”[4]陈学文:《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324 页。,“风俗自淳而趋于薄也,犹江河之走下,而不可返也”[5](明)范濂:《云间据目抄》卷2,钱泳、黄汉、尹元炜、牛应之主编:《笔记小说大观》第13 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 年版,第110 页。。蓝东兴在《论明朝中后期贪污受贿问题》一文中说:“匡世济民的使命感和清正廉明的人生信条全都淹没。”[6]蓝东兴:《论明朝中后期贪污受贿问题》,《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 年第4 期。本应严肃的官场在歪风邪气的侵蚀下逐步演变为权力变现的商场,大小官吏亦沦为庸俗的商人。
在《西游记》中,吴承恩描绘了这样一个充满现实人情世故的西方极乐世界。唐僧师徒路遇的大鹏金翅雕乃如来佛祖的舅辈至亲,尽管犯下滔天罪孽,如来却未予惩戒,反倒许诺“我管四大部洲,无数众生瞻仰,凡做好事,我教他先祭汝口”[1](明)吴承恩:《西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1022 页,第1278 页。。当师徒历尽万苦艰辛抵达灵山,对于两位尊者因未收贿赂而传无字经书,如来非但没有惩治,反而辩称:
他两个问你要人事之事,我已知矣。但只是经不可以轻传,亦不可以空取。向时众比丘圣僧下山,曾将此经在舍卫国赵长者家与他诵了一遍,保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脱,只讨得他三斗三升米粒黄金、白银,我还说他们忒卖贱了,教后代儿孙没钱使用。你如今空手来取,是以传了白本。白本者,乃无字真经,倒也是好的。因你那东土众生,愚迷不误,只可以此传之耳。[2](明)吴承恩:《西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1022 页,第1278 页。作者通过如来佛祖、大鹏金翅雕和阿傩、伽叶的形象塑造,以及取经的庄严被矮化为一桩桩买卖的情节设计,深刻揭露在腐朽歪风侵扰下被异化的官场生态。
2.市场需求与精神寄托
从接受学的角度来说,明代神魔小说之所以繁荣发展,离不开商业化的背景。自《三遂平妖传》问世,明代神魔小说就散发出愈发浓郁的商业气息和市民气息,很快成为书坊竞相追逐的娇宠。而小说的传播尤其是长篇小说的传播,不同于口耳相传、手抄相传的诗歌、散文,它必须依赖较为发达的出版业,对小说进行批量印刷才能实现大规模的传播和接受。明代嘉靖、万历开始,书坊业异常繁荣,以江南最为发达,主要包括江苏的南京、常州、苏州,浙江的杭州、湖州,福建的建阳等。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以刻书为生的书坊主根据市场需求开始主导小说的创作和刊刻,情节离奇、吸人眼球的神魔小说便是其不二之选。
正如陈文新在《明代文学与明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一文中指出的,万历至崇祯年间,章回体小说的创作迎来了活跃期,各类小说纷纷面世,商业化和文人化成为明代白话小说的两股主要推动力量。[3]陈文新:《明代文学与明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文艺研究》2013 年第10 期。书商的积极参与,推动神魔小说的大众化传播,既促进了神魔小说的消费和接受,也激发了当时文人的创作热情,而读者的追捧又刺激了书坊主扩大再生产。
明末由儒学衍生的程朱理学日渐背离其真髓而失去活力,明显呈现衰颓之势,成为社会进步和民心拢聚的羁绊。商品经济发展和心学思潮盛行促使思想束缚的逐步舒张,提高了个性化情趣的认可度,持续促进了文学的发展。面对封建统治阶层一边施以刚性的强制手段、一边辅以柔性的文化奴役的残酷现实,底层民众希冀借助一种近乎完美的大同世界幻想来实现自我的精神满足,而孙悟空便是他们这种“自我陶醉”得以宣泄的寄托。赵明政在《孙悟空是“新兴市民”的典型形象吗?》一文中指出:
孙悟空大闹天宫无疑是中国历史大小数百次农民猛烈冲击封建政权和封建秩序的伟大斗争的集中和概括。他敢于向一切神佛宣战,踏倒一切神权,要求彻底推翻玉帝的统治。如同历代封建统治者污蔑农民起义是“妖民作乱”一样,象征人间皇帝的玉帝也称孙悟空的造反行动是“妖猴作乱”,这是极其明显的象征和暗示。[4]赵明政:《孙悟空是“新兴市民”的典型形象吗?——与朱彤同志商榷》,《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78 年第3 期。赵文的论述清晰地证明了孙悟空这个“妖猴”及其群猴的形象塑造,体现的是明代市民意识的崛起,充当的是底层民众反抗封建皇权的精神寄托。
早在百回本《西游记》诞生前,就已出现了许多以唐僧取经为背景创作的故事、戏曲、杂剧、小说等。底层民众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将他们的反抗意识附着于孙悟空的形象之上,再通过对妖魔形象的塑造来凸显孙悟空的智慧与果敢,进而满足他们推翻腐朽政权、打倒黑恶势力的幻想。那些社会底层民众的肺腑心声,在与权力的交锋与博弈中趋向多元,成为作者创作的生动素材,促使其以幻化的写作手法将现实社会虚化为缥缈的神话世界,并希冀在普罗大众中产生情感共鸣。
七、结语
综上所述,深入探究《西游记》作者塑造妖魔形象的根源可以发现,书中故事的情节铺排与人物的奇妙遭遇皆是现实社会的缩影,作者旨在借神魔说事,以梦幻离奇、瑰丽神秘的神话世界隐射人类社会的丑恶现实,以唐僧西行途中遭遇的妖魔形象讽刺和抨击那些隐藏于封建政体的黑恶势力。通过聚焦《西游记》成书时期吴承恩生活的特殊社会环境,我们知道因为有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才激发出他无限的创作灵感,最终成就了这部气势恢宏的巨著。在时代背景方面,他的坎坷经历和多元宗教文化的时代特色,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契机;在思想启蒙方面,人本主义和阳明心学思潮的强劲推力,帮助他确立了创作主旨;在政治演化方面,腐朽的封建统治、僵化的选才机制及丧失锐气的官场士人,成为他的抨击对象;在经济发展方面,商贸经济的发展、商业化传播对市场需求的刺激,以及文化思潮带动的市民意识崛起,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一生命运多舛的吴承恩,用数十年的惨淡功名换取了这部传世巨著,把他对统治阶层的愤懑及对底层民众的同情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从而在普罗大众中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