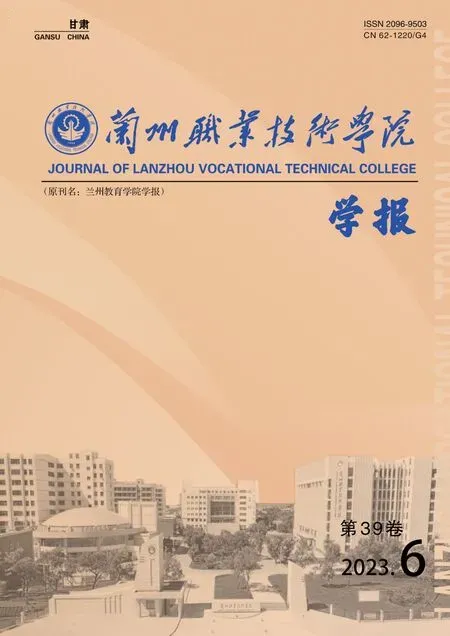软弱者和反抗者的交织
——《家》与《寒夜》人物形象分析
刘介华
(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基础教学部, 江苏 徐州 221011)
巴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从20世纪跨入21世纪的文学大师。他的作品影响了整整几代人,无论是其处女作《灭亡》,还是后来的“激流三部曲”的《家》和《寒夜》,又或是后来的《随想录》,无不渗透着作者对以往生活的回忆,体现着作者对社会的深层思考,从而唤醒当时的青年。从《灭亡》中的杜大心到《家》里的觉新、觉慧,再到《雾》里的周如水,最后到《寒夜》里的汪文宣,沿着这一创作轨迹,我们不难发现巴金先生所擅长的是对知识分子的塑造。在塑造这些知识分子的过程中,巴金先生又集中塑造了两类突出的形象:一类是以觉新、汪文宣为代表的软弱者、忍耐者,他们虽然接受了许多新思想,但还是成为了旧社会的牺牲者;一类是以觉慧、曾树生为代表的反抗者,他们想摆脱家庭的束缚,成为了走出家庭、迈进社会的反抗者。正是因为有这两类形象的鲜明对比,才使得当时的社会青年有了对封建礼教、国统区黑暗社会的深刻认知,鼓舞更多的青年人走出家庭的牢笼,走进更广阔的社会。巴金先生是那个时代用作品影响青年一代的启蒙者之一。
一、以觉新、汪文宣为代表的软弱者
(一)软弱者形象分析
觉新是作者在《家》中描写最深刻、着墨最多的一个人物,也是作者在众多软弱者形象中刻画最生动的一个。觉新作为封建大家庭的长房长孙,从小受到封建大家庭礼教的毒害与束缚,在他的潜意识里他的所作所为、一言一行都要符合他作为长房长孙的身份。面对高老太爷的意愿,他不敢也不能反抗,只能一如既往地顺从,放弃继续学习的机会到实业公司去做事,和他不爱的瑞珏结婚。这些都反映了他的性格特征——软弱,对任何事情都是服从、顺从,无力甚至是不敢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不仅自己顺从,还影响和带动其他人跟他一起顺从,这就是封建礼教长期毒害的结果。他的身上已然看不到青年该有的精神状态。在他的意识当中,顺从长辈的意志就是天经地义,忤逆长辈的意愿就是大逆不道。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无论怎么反抗也没有什么结果,于是他选择了放弃——用软弱、顺从牺牲了自己想要追求的事业、爱情和自己认为的一切美好事物。这就是中国旧式青年惨痛的悲剧和寂寞如死灰般的人生[1]!
自从巴金先生形象地刻画了觉新这个软弱者之后,他又塑造了一群软弱者形象,如《家》中的枚少爷、《雾》中的周如水,以及《寒夜》中的汪文宣。
跟觉新一样,汪文宣也是一家之主,曾经也对生活充满梦想,但是最终被社会的“寒夜”所吞噬,在黑暗的国统区一步一步地走向毁灭。社会动乱、工作、生活以及身体疾病等各方面的压力同时向汪文宣袭来,他落入了社会乞食者的队伍。他从内心深处开始诅咒这个可恶的世界,并痛恨这个世界的不公——“别人可以升官发财,而我们却要奉公守法”[2]69。虽然有着对社会的诸多埋怨,但为了生活,心地善良而又软弱无能的他只能将这种苦楚往肚子里咽,并对自己说:“为了生活,我只有忍受。”[2]78但是他的一味忍让、屈从并没有换来别人的同情,反而更使他感受到来自领导、同事的无情和冷血,“周主任的表情和吴科长的眼光似乎在鞭策他走向着‘死’”[2]79。在面对国民党粉饰太平生活的丑恶嘴脸时,汪文宣被他们的谎言气到吐血,却只能将这种情绪表现为“低声抱怨”“无声的抗议”。在内心深处他对黑暗社会、国民党统治是憎恶与仇恨的,然而他又无力抵抗,只能默默承受社会对他的种种压迫、冷酷和无情。在这样令人窒息的社会和工作环境中,他只能用痛苦折磨自己的心,“我也会说谎了”,说着违心的话,干着违心的事。本身就脆弱、不堪一击的他只能选择忍辱负重、懦弱苟安。
在工作中不遂心,在社会中看不到光明,在家庭生活中也不如意,所有这一切对他来说是那么痛苦、那么煎熬。汪文宣孝顺母亲,关心妻子。在面对妻子和自己的母亲水火不相容的情感冲突时,他夹在两者之间无力回旋,只能自怨自艾。毫无反抗能力的他被冷酷的现实一步步逼上了绝境,在他撒手人寰的时候,他愤懑地向社会反问:“我做了什么错事呢?我一个安分的老好人,为什么我该受这惩罚?”[2]125
(二)软弱者形象形成的原因
从《家》《寒夜》中我们看到了封建家庭的软弱者觉新与深受社会、家庭、工作三重压力,而懦弱苟安的知识分子汪文宣。虽然他们生活的年代和社会环境不同,但是他们的结局如出一辙,汪文宣“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四十年代的觉新性格的翻版,也是对觉新形象中年情怀的继续探索”[3]。是什么原因使他们成为了软弱者呢?
1.罪恶的社会制度是他们悲剧产生的根本原因
觉新生活在中国旧式的封建大家庭中,靠的是祖上的资产,不必为了生活而到处奔波。由于父亲过早去世,作为长房长孙的他不得不成为高家的第三代顶梁柱,挑起这“半死不活”的封建家庭的重担,不仅要处理家庭的种种琐事,还要像傀儡似的做着别人要求他做的事。他的内心有一百个不愿意,但是又不能不做。他没有选择的权利与自由,这一切的罪恶都来源于封建制度,来源于封建礼教对青年的束缚。
《寒夜》中的汪文宣不是封建大家庭中的大少爷,只是一个在黑暗的国统区忍受着来自社会、工作、生活三重重压的小知识分子。年轻时的汪文宣可不是这般模样,他曾经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有志青年,读大学时就有了创办乡村教育之理想,大胆地与曾树生自由恋爱、结合。但是当他们一家三口逃到重庆之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以前对自由、爱情、理想的美好憧憬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现实生活的重重压力。一家三代只能住在破烂不堪的用板壁隔开的昏暗的陋室之中。为了赚取微薄的收入,汪文宣每天干着重复单调的工作,校对着纠缠不清的译文,小心翼翼地周旋于领导、同事之间,忍气吞声、懦弱苟安。他有多厌恶、多憎恨国统区的黑暗,内心深处就有多痛苦、多矛盾、多煎熬。无论是觉新还是汪文宣,他们的软弱都是被这罪恶的社会制度一步步“逼”出来的,只不过汪文宣与大少爷觉新相比,他面对三种苦痛时无疑要比觉新更无助、更彷徨、更绝望。
2.性格软弱是他们悲剧产生的主要原因
经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之后,一批批青年想要从封建的思想牢笼中挣脱出来,接受新世界、新思想所带来的馈赠。生活在上世纪20年代的觉新、上世纪40年代的汪文宣也不例外,但他们虽然接受了新思想,最终却没能走出旧世界,而是成为了软弱者,其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性格的软弱。为了承担长房长孙的义务,为了能够撑起庞大的封建家族,觉新先是放弃了去国外深造的机会;后又放弃了与自己情投意合、青梅竹马的表妹结合的机会,任人摆布地接受长辈安排的婚姻;为了避免所谓的“血光之灾”,听从了长辈的意愿而葬送了妻子的性命,又因为自己的软弱致使表妹忧郁死去。在一次次面对各种选择时,他总是一味地妥协、顺从、忍让,殊不知一次次的妥协、顺从、忍让换来的是自己的“人生苦难”,最终使自己走向毁灭。
汪文宣是可悲的甚至是可怜的,“老好人”的形象最终也没有使他得到社会的眷顾。在工作中,对于工作的不满,既不敢诉之于言,也不敢形之于色,只是在心里默默自语和承受[2]11。不论是看到上级领导的目光还是听到吴科长无意哼出来的声音,都让他觉得是在警告或者在责怪自己,这就导致了他在领导、同事面前总是小心翼翼,生怕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只能在内心深处默默承受、煎熬。在家庭中,既不能给曾树生家庭的温暖,又没有能力解决婆媳之间的矛盾,使得这对婆媳的关系日益紧张,最终落得两边都不讨好。甚至在曾树生跟别的男人去兰州之后,他依旧只报喜不报忧,自己病情加重时,也善意地编织谎言隐瞒自己的妻子。应该说他的软弱性格是造成他悲剧的最主要原因。
软弱已成为这两个人物共同的代名词,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用麻木自欺、软弱退让当挡箭牌。即使他们内心有欲望和要求时,也从不敢期望,不敢采取任何的措施和行动去捍卫和争取,只能眼睁睁地一次次错失“良机”。他们永远没有改变自己现状的勇气和行动,更谈不上反抗。
二、以觉慧、曾树生为代表的反抗者
(一)反抗者形象分析
《家》中不光有封建家庭的软弱者和牺牲者觉新,还有一个反抗者觉慧。他的出现无疑给当时的青年带来了希望和出路。觉慧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具备了先进青年的许多特点,时常与青年们一起讨论时事政治,热衷于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用实际行动来批判自己痛恨的黑暗社会现实。在封建大家庭中,只有他一人孤身奋战,敢于做“冒天下之大不韪之事”——爱上并追求婢女鸣凤。尤其是在小说的最后,随着高太爷的死亡,这个象征封建礼教的大家庭也随之崩塌、瓦解,这使得觉慧又做出一个大胆举动——不同意将要分娩的瑞钰搬出去,想要帮助觉新改变一味委曲求全的个性。这些都表现出他与封建家庭、势力作斗争的勇气和反抗精神。正是因为有了觉慧的敢作敢为,才能凸显出觉新的软弱、觉民的勇敢。觉慧有些时候也会表现出一些软弱性,这是由于从小到大生活在封建大家庭中,不可避免受封建思想的影响而导致的。当鸣凤被送去做冯乐山的姨太太时,他没有上去劝说更没有阻止,反而为自己找了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掩饰自己内心的软弱。鸣凤投水自尽后,他才深刻意识到自己的软弱与幼稚,痛恨自己“把她抛弃了”,对觉民说:“我害了她。我的确没有胆量……我从前责备大哥你没有胆量,现在我才晓得我跟你们一样。我们都没有胆量。我也恨我自己!”[4]正是鸣凤的死给了觉慧当头一棒,驱除了他内心的软弱,让他勇敢地选择摆脱封建家庭的束缚,毅然决然地站到封建家庭的对立面,走向外面更为广阔的新世界。
在《寒夜》中也有一位反抗者曾树生,她虽是女性,却表现出不输于男性的反抗精神。与巴金笔下的其他女性不同,她有独立的人格、经济意识,敢于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选择出逃,虽然最终没能完全地独立,但这种行为在当时女性抗争的道路上已成功跨出了一大步,尤其是与自己的丈夫相比,更显出她的勇敢。
曾树生已经摆脱了封建思想的枷锁,具有了五四新女性意识,她与汪文宣一样接受过高等教育,同时也追求个性解放、人生价值。因为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他们自由恋爱、成家。当这些理想落实到现实中,成了“水中捞月”时,曾树生没有像汪文宣那样被社会、工作、家庭折磨得一味妥协,她还勇于出逃、敢于反抗,哪怕最后出逃没有成功不得不归来,但出逃本身就是一种对自己命运的反抗。与觉慧相比,她的反抗更像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她的反抗一是对长期以来处于男权压迫下女性屈从地位的反抗;二是对长期以来传统的伦理制度下,女性未作为与男性同等的“人”的反抗。令人欣慰的是曾树生走出家门成为社会职业女性,从家庭中挣脱出来获得了一定的人身自由,有了一定的自我选择空间,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的社会价值。
(二)反抗者形象形成的原因
1.时代的孕育和呼唤造就了反抗者的“出走”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一个动荡的时代,社会的剧烈变化引发了社会思想的裂变。随着五四运动的到来,西方民主思想的快速传播给广大的中国青年带来了猛烈的思想冲击。他们开始逐步认识到中国几千年来封建制度的种种罪恶,而家族制度又是束缚自由、扼杀人性的“万恶之首”。在这个时代大背景下,社会上崛起了一批青年,要从封建的思想牢笼中挣脱出来,去寻找独立、自由的新生活。觉慧和其他的年轻人一样接触到这种新思潮,被这种新思想所鼓舞。觉慧的离家出走绝不是偶然,而是必然,是时代的呼唤使他走上了义无反顾的反抗之路,这也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真实写照。
和上世纪20年代的“反抗者”相比,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反抗者则在深度和广度上更进了一步。他们大都是出现在社会转型、时代动荡的时期,在新时代个性解放的旗帜召唤下,他们勇敢地走出旧家庭,寻找自己的理想。反抗的大军中不光有男性的身影,还有女性的光芒。曾树生就是从反抗队伍中走出的女性代表。五四运动举起了反封建礼教的大旗,压抑了几千年的女性意识也慢慢觉醒。经过接近三十年的发展,女性的反抗意识日益增强,受过新思想教育的曾树生就是在这个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作为一个接受过个性解放思想影响的新女性,尽管做的是在别人眼中被视为“花瓶”的工作,但在曾树生自己心中却认为是对自己独立人格的一种自我证明,证明自己在社会中具有独立的个体地位。无论是在小说的开篇还是在汪文宣患病的时候,她想离开这个家的想法从未改变。她不想像汪文宣似地挣扎在生存的边缘,想要在生存之上找到生活的意义、价值,想活得痛快一些,作为独立的个体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2.反抗——反抗者骨子里的“基因”
觉慧是一个受五四初期民主主义思想影响的封建大家族反抗者形象,他的反抗性格是在见证封建大家庭如何残害青年的过程中一步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开始觉慧是通过参加学生请愿活动来表达自己的反抗意识的,但那时他的反抗意识并不是很明显。后来鸣凤的投湖使他看清了封建制度对妇女的戕害,他的反抗意识发展成了一种反抗行为。他勇敢地与封建势力进行斗争,继续参加进步活动,宣传新思想,从行动上支持二哥逃婚,在家族内声讨长辈们所谓的“捉鬼”行为。他反抗意识坚决、行动坚定,最终这两件与封建家族正面交锋的事情都取得了胜利。这显然是与觉慧本身的反抗意识分不开的。最终将觉慧的反抗行为推向极致的是大嫂瑞珏的死。在后来的一次次事件中,他没有妥协退让,而是不屈服、不动摇,勇敢地站出来反抗封建礼教、封建势力。可以说,他是高家唯一一个敢于反抗的人。
巴金的作品中,还塑造有如琴、鸣凤等许多女性形象,但只有曾树生完成了女性命运的抗争,这和她的反抗性格是分不开的。自从一家三口来到重庆,曾树生与汪文宣的理想在现实面前破灭后,为了不依附家庭、丈夫,她找了一份银行“花瓶”的工作,尽管有时也会有抱怨,但是她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尊严和人格独立。在家庭生活中,她始终把自己当作是一个“人”,一个独立的个体。她秉持着“我是我”的信条,为了实现对独立生活理想、自由的追求,最终毅然决然地脱离了死气沉沉的家庭的束缚,去勇敢地找寻幸福、创造幸福。不管实现与否,追求幸福是每个人的权利,曾树生的反抗行为是与她追求独立、自由、平等的性格分不开的。
三、结语
在那个激情动荡的时代,巴金先生站在时代的前沿,创作出两类鲜活的人物形象:软弱者、反抗者。软弱者的形成有社会及自身性格的原因,值得欣慰的是,更多的青年从反抗者身上感受到了对新文化、新生力量的呼唤,同时也反映出作家对时代的思考、回答——旧的在灭亡,新的在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