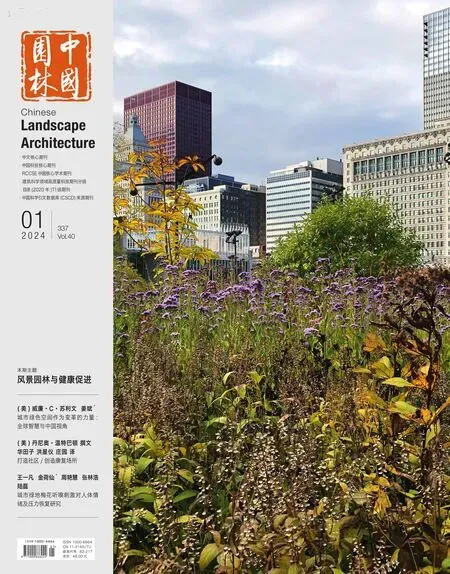探索景观触媒效应下城市后工业景观设计推动山地城市更新的途径
王 哲 朱 捷
1 城市更新背景下的后工业景观现状与问题
自“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以来①,城市更新被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并逐渐成为中国城市存量提升阶段下,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法[1]。对于许多老工业城市而言,成群成片占据旧城发展空间的老旧厂区见证了城市历史,铭刻了时代记忆,成为城市更新的主要抓手之一②。如何对其中有遗产价值的区域、地段、片段进行保护性发展与可持续利用,使之满足城市的多方面需要,是当前该领域的热点议题[2]。基于长期且广泛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后工业景观(又称“工业遗产景观”)设计已逐渐成为实现工业遗存保护与利用的重要范式[3]7-21[4],其高品质绿色空间改造、城市工业“伤疤”修复、历史文化印记保存、新城市活力空间创造、文旅及创意产业植入等作用日益凸显,体现出有益于旧城片区更新的复合价值。
目前后工业景观的相关研究多源于实践总结,可归纳为以下方面:基于生态修复的景观生态学应用[5-7];基于文脉保护的工业遗产更新设计[8-9];基于艺术化表现的景观改造设计[10-11];基于公共空间转化的场地资源开发与注入[12-13];基于遗产群与城市关系分析的总体优化与保护利用[14-15];以及基于更新驱动的工业区再生[16-17]等。总体而言,当前后工业景观的更新内容多关注建筑空间、场地设施等的改造利用和绿色空间的转化,而关于景观对周边城市空间所发挥的渐进式影响的讨论略有不足,无法发挥后工业景观对城市发展的持续影响;研究及实践多是“就地而论”,普遍针对某一局部个体、场地或片段,丧失了从全局视角关联和“活化”众多工业遗产进而促进片区整体性更新发展的契机,难免造成遗产的“破碎”与景观的“同质”。虽有部分学者以城市设计的方式统筹分散的工业遗址并进行整体保护利用与绿色空间系统构建,或以大型城市事件引导工业地区遗产转型发展,更有德国鲁尔区“工业遗产之路”和“工业自然之路”的典型范例,但研究多聚焦于遗产保护、生态环境与产业经济等单一层面,难以实现对场地景观复合潜质的开发。在该种情形下,针对山地工业城市老旧城区内成群成片、特征显著的城市后工业景观,本文的研究需要拓展新的思路,从全局视角探讨通过其整体、持续、多维的更新设计促进山地城市有机更新的有效途径。
2 景观触媒的理念方法
2.1 景观触媒及景观触媒效应
“触媒”(catalyst)原指以小剂量的物质实现化学反应速率增大的现象。20世纪末,韦恩·奥图(Wayne Attoe)和唐·洛干(Donn Logan)在著作中引申出“城市触媒”(urban catalyst)的概念,指代能够引发周边城市空间的连锁反应,正面影响其后续建设活动,进而加快城市改变速度的媒介[18]。“景观触媒”脱胎于城市触媒理念,即将价值多元、效益综合、动态持续、弹性灵活的景观作为触媒体的一种城市建设思考与探索[19]。相较于建筑单体触媒,景观触媒不仅仅是随着距离增加而逐渐衰减的“原点”与“孤岛”。如以库哈斯(Rem Koolhaas)为代表的部分学者提出将自然与人工耦合的“虚体空间”作为城市演变的布局框架[20],构造建筑、景观与自然环境有机融合的“嵌合体”的城市建设思路。基于此,景观触媒可以通过景观与景观之间、景观与周边环境之间的关联协同与相互作用,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由触媒单体的低级模式向供给能量传递与扩散的触媒“网络”的高级模式转变。景观触媒效应即高质量、特质性的景观,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利用引领性的多元景观要素由内而外地“刺激”周围城市空间的变革,由点及面地“引导”城市片区的后续发展,进而不断形成与原触媒相互作用的新触媒,并在城市景观触媒网络框架中,通过景观触媒点间的连锁反应,由浅及深地渐进式推动城市建设或更新[19,21]。
2.2 城市更新背景下后工业景观与景观触媒的契合性
尼尔·柯克伍德(Niall Kirkwood)在其专著《Manufactured Sites》中认为后工业景观是科学与艺术、技术与设计、保护与利用创造性融合的结果,并归纳其构成包含了大规模工业生产遗留的基础设施、工业遗址和散落在周边城市空间中与工业生产相关的“残余空间”(drosscape)[22],其具有丰富多样的景观资源;同时,各时期生产活动对场地自然环境的改造,既创造出各类堆场、蓄水池等具有地景潜质的特色空间,产生了一个个“宏伟”的工业“巨构”,亦记述了一段城市历史,描绘了一系列工业人文场景,因此多数价值较高的遗迹本身便是凸显城市意象的文化景观。另外,工业厂房多是具有大跨度框架结构的宽敞空间,生产设施本身也具备一定观赏性,因此其改造成本普遍较低、空间组织灵活、拆改较为便捷容易。由此可见,后工业景观所在的废弃地因其类型与资源多样、形象鲜明、改造便捷等特点,成为城市更新中独特的“空间资源”[23]。而“城市后工业景观”作为诸多分布在城市中心区的特殊类型之一[3]39,在遗产价值得以保护与传承的同时,也需要承担旧城空间结构优化、品质提升等复兴责任,因此在突出的区位优势下具备了成为触媒体的潜力。
后工业景观设计并不意味着对场地进行单纯地、完全地、永久地景观化改造,它既是应对老旧厂区复杂的再生问题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更新背景下部分厂区和地段的活化利用结果与改造设计的阶段性成果,强调兼容性地、有选择地、持续性地实践思考。而景观触媒所蕴含的系统观、特色观、虚实观、体验观、多维观、动态观和过程观等思想观念[24],可以为后工业景观设计注入灵感。它强调将原本简单的场地空间设计转换为对景观触媒效应的思考,即从城市整体视角系统地选择、识别、统筹、协调散布的各类型“潜质空间”;凸显和延续各个后工业景观独特的资源特色与多义的文化内涵;加强厂房、设施内外空间的紧密互动;丰富人文氛围浓郁的“工业自然”体验;保护遗产价值的同时,触发后工业景观在城市复杂环境中的多方面触媒潜力;灵活调整景观的形式、功能和触媒的作用方向及强度;利用设计“过程”持续刺激和应对场地的发展与周边环境的变化,从而更有效地激发其对旧城片区更新的推动作用。
3 城市后工业景观触媒的特质
3.1 工业生产历史造就的多元价值
城市后工业景观是工业大规模生产停止后,在时间与自然作用下不断演变的“历史对象”和具有“光复”意味的景观化状态[25],蕴含如下不同于一般遗产景观的多元价值。1)生态:自然过程影响下,工业废弃地上的野性景观[12];2)审美:“废墟审美”与工业“大机器”下,破败连续的“崇高”景象[18];3)历史:多次技术与设备革新后,多个历史层积在场地空间中的组合与拼贴;4)社会:行为、记忆、情感累积下,工业企业的时代生活体现;5)科技:大规模机械化生产中,大机器的生产体系与工艺流程。这些特征既是景观资源及遗产价值评价的指标依据,亦是高质量景观中需要着重保护和呈现的重要特质。
3.2 价值外溢形成的触媒综合潜质
在城市更新的语境下,后工业景观具备价值外溢的特点[26]。依托所在的区域位置及城市环境,后工业景观由自身的资源特征“引申”出生态系统价值、形象展示价值、人文体验价值、社会情感价值、游憩功能价值、科普教育价值、旅游开发价值、文化产业价值等“潜在”内容,使城市后工业景观具备了生态环境优化、工业意象展示、历史文脉彰显、功能活力注入和产业开发运营5个方面的综合潜质(图1)。这些潜质随着景观品质的提高可以被触发形成促进周边发展的多维触媒潜力(图2)。

图1 城市后工业景观的综合潜质

图2 城市后工业景观的多维复合潜质激发触媒潜力
3.3 聚散与更迭导致的层级组合关系
对于工业产业类型丰富、体系完善的老工业城市而言,多层级、多类型的后工业景观群在城市空间中呈现“元-园-组-廊”的组合关系(图3)。1)单元:后工业景观因生产程序的内在逻辑,其保护与利用应打破“精英”的单体设施模式,表现为“连续”的景观单元(如生产、生产服务、公共活动、交通运输、生活配套等)。2)景园:厂区内集群型景观单元由生产体系串联,在规划后转变为填充型、并置型、紧临型或包容型的遗址公园、博览园、体育公园、创意产业园、科技产业园、艺术园区、行政办公区及商业街区等;孤立在城市空间中的“残余”景观单元在更新中被改造为嵌入型小游园、城市广场、口袋公园、博物馆、艺术馆、会所或工作坊等。3)群组:众多生产关系紧密的工业企业以某一个骨干产业或先行的重要厂区为核心,在城市工业片区范围内集聚[27],停产废弃后,由空间联系紧密、生产与服务类型多样的多个“景园”组成景观群组。4)廊道:临近的工业集聚区借助重要的生产资料运输线或城市带状空间连接,沿历史发展脉络与工业生产结构,可以在中观尺度串联为融入城市空间的景观廊道。这种层级组合关系使得成群的后工业景观能够更好地发挥遗产的“关联价值”和景观的协同作用,并完善城市开放空间体系,为景观触媒“网络”框架的构建奠定基础。

图3 城市后工业景观组合嵌套关系模式
4 山地城市中的城市后工业景观
4.1 山地城市后工业景观的显著特征
1)融入城市山水的连续结构。
山地城市复杂的地形地貌描摹出城市山水相依的独特自然风景。以资源或运输为选址依据的工业企业,多沿山顺水而建,形成景山、沿山、靠山或傍水、邻水等山水位置关系。同时,成片的工业景观由山地城市的多种自然走廊串联,描摹出山环、山倚、水绕、水穿的镶嵌结构。融入城市山水的后工业景观不仅展现了独特的景观画面与城市画卷,亦因此表现出较强的生态敏感性与生态系统重要性。并且受早期不合理规划的影响,发展空间严重受限的山地旧城区多缺乏大型绿地斑块及连接绿地斑块的绿楔,所以城市后工业景观所承担的绿网结构优化任务格外艰巨。
2)融合山地地形的魅力景象。
山地城市起伏多变的地形地貌、自然蜿蜒的柔性界面、内外向型空间交替的感知变化、婉转曲折的山水形态特征,以及俯仰上下的视线关系,赋予工业厂区以更加丰富、立体的大地景观、复式空间和序列感知。如多重台地、屋顶退台、半山蓄水池、多层架空的灰色空间、融入地形起伏的桁架连廊、依山而建的外向型巨大设施,以及俯瞰城市的高地平台等,均镌刻进了山地城市的景观基因之中。它们经过艺术造景、视廊组织、序列联动和形态重塑后,成为独特的城市意象,但同时也增加了工业“废墟”意象组织、协调与塑造的复杂性。
3)承载地域山水的文化景观。
工业生产与山居活动使工业景观之中许多具有可识别性的场地环境、山水形胜等“定向”(orientation)空间,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与人文情感,在不经意间既产生了许多迥异于平原城市的个性场所,如沿山阶梯间歇平台上的乘凉角(鹅岭二厂)、复式廊架下的学习室(重钢),以及穿山的货轨隧洞(大冶铁矿)等;也衍生出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山水寓意,如“铜海飞烟”的臆想与美誉(铜绿山古矿场遗址);还诞生出了与山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习俗、历史记忆、建造技艺等有形、无形的文化产物和时移世易的企业文化、时代精神等文化内涵,使生活在企业社区和厂区聚落的亲历者对场地产生深刻的文化“认同”(identification)。然而,这些文化要素随着时光的消融逐渐被稀释,继而变得难以感知。
4)承载丰富人居活动的场地。
后工业景观除了生产工艺系统及关键设施外,其他建构筑物多呈现出简约的时代形象、模数化的框架结构和开敞的厂房空间,具有极强的可塑性;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建筑外部空间及运输场地,如站台、连廊、码头、铁路等,亦是可以灵活改造、弹性布局的景观要素;顺应复杂地形而形成的复式空间,更为新功能的融入与新活动的发生提供了舞台。山地城市往往能够孕育出特殊的生活习惯、出行方式,有助于在后工业场地上还原和打造出一系列迥异于平原城市的独特场景。但山地中的坡、坎、崖等地形也分隔或围合出许多不易被利用的消极空间,并阻断了场地间的连接;同时,沿等高线布局的大面积厂区大院不可避免地限制了城市的竖向交通,其所处的山地位置亦有可能降低场地的可达性。
5)嵌合城市组团的景观格局。
山地城市受自然条件的约束,往往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多中心组团式发展模式[28]。而近代以来建设发展的许多传统型山地工业城市以重要工业企业为中心进行城市组团建设(如黄石中心城区、攀枝花等),或在数十年的城市扩张中将诸多工业企业融入组团中心(如重庆主城区、贵阳等),在区域视角下构成工业群与多城市中心组团嵌合的格局,造成旧城片区中成群废弃厂区占据本就不充裕的城市重要发展空间的现象。该格局下城市后工业景观的区位优势更为明显,因工业类型、生产技术、山水关系等方面的不同,群组之间也表现出了较强的景观异质性。但也正因为这种组团嵌套关系,城市后工业景观承担着更为巨大的更新压力。
4.2 山地城市后工业景观设计的关键
较之平原城市,山地城市的后工业景观因“山水相依”“魅力显著”“人文孕育”“场地丰富”“组团嵌套”等显著特征,无疑能对场地及周边城市空间的品质提升产生巨大影响。然而,格外脆弱的生态环境及更为突出的生态系统重要性、更加复杂的意象组织、逐渐消逝的文化内涵、更难以利用的消极空间及紧迫的交通问题、更为沉重的城市更新压力亦成为不容忽视的规划设计难点。因此,山地城市后工业景观的设计既需要把握住显著特征带来的机遇,辨识融入山地地形的景观资源特征,挖掘嵌合山水城境的综合潜质,也需要着力解决其存在的突出问题,从多个维度有效提质景观,为城市的有机更新奠定扎实的基础。
5 激发后工业景观触媒效应的山地城市更新途径
山地城市后工业景观触媒效应的激发需要以上位规划和发展目标为基础,将景观触媒的作用机制与景观“元-园-组-廊”的层级结构对应,结合山地城市后工业景观的显著特征和设计关键,由点及面、由内而外、由低级向高级逐层引发触媒效应。其途径可归纳为潜质挖掘、组织架构、影响提升、连锁反应、链式延展和整体调控6个步骤(图4)。

图4 山地城市后工业景观触媒效应的激发
5.1 鉴识:评价多维触媒潜质,发掘重要激活对象
后工业景观自身的资源特色及融合了山水-城境的场地周边环境为其触媒点的筛选与多维潜质的识别提供了可靠来源。因此,触媒潜质的分析需要建立从自身特质到外部区位的综合评价体系。自身特质方面,通过明晰各场地的工业自然再野化程度(生态价值)、立体复式工业“废墟”的美景度(艺术价值)、历史层积及文化内涵等的深厚度(历史价值)、时代生活的社会影响力(社会价值),以及生产建造技术及设施工艺等的创造力与先进度(科技价值),甄别场地优于其他城市空间的特色所在;外部区位方面,通过选取生态系统功能重要性、潜在生态廊道重要性、山城景观美景度、山城景观可视性、城市文态值、组团中心度、区位优势度及所处地段的可利用度(包含尺度规模)等区域性指标,并借助城市开元数据、GIS空间信息分析功能,揭示各场地在区位中的生态系统重要性、山水-工业景观意象的展示力、历史文化氛围浓郁度、人居活动的服务力和综合业态开发的优势度,从而判断场地更新利用的优先级与复合发展的适宜方向。综合分析结果与用地规划,初步厘清各老旧厂区、大院等触媒点的触媒等级划分、现阶段改造定位(以绿色空间转化、工业形象展示、历史文化彰显、功能活力提升或产业产品策划运营为主)与更新建设时序(图5)。需要注意的是,部分污染严重的重要触媒点应优先进行棕地治理,暂缓其活化利用;无论触媒等级的高低,高遗产价值的景观均应在前期进行生态修复,并在更新过程中整体采用保护为主、价值延续、弹性灵活、轻量适宜的“保护性发展”措施。

图5 途径Ⅰ——鉴识
5.2 布局:统筹遗产资源格局,规划景观单元结构
不同于自然山水型或城市“补遗”型景观空间,城市后工业景观需要以遗产“完整性”(integrity)与“原真性”(authenticity)保护为前提③。因此,针对不同触媒点,景观设计需要优先明晰场地中保护、更新及再生的遗产片段。首先,设计团队应组织专家评委和职工居民详细筛选场地环境、意象感知、工业建构筑物及设施、生产生活场所和生产系统等内容,评价其景观生境、审美、历史、社会、科技等价值,发掘较为典型的个体及组合;其次,为维持后工业景观生产单元的连续性,需进一步分析要素价值在空间中的聚集度,叠加出后工业景观的遗产保护格局;最后,将该保护格局与场地空间的使用价值分区相结合,判断遗产景观资源的适应性分布。在此基础上,场地中景观的组织布局可利用“单元”布局模式[29],以单元主体部分在遗产保护格局中的等级为依据,将各单元所在区域划分为核心保护(高资源特色)、适宜改造(中资源特色)和创意再生(低资源特色)3类,并据此识别和保护场地中遗产景观的基础骨架,规划场地整体的空间形态(如填充型、并置型等);以生产体系的“可阅读性”为依据,对单元(主要指主体部分位于核心保护与适宜改造区域的单元)生产工艺流程结构中的“精英”及一般内容分别进行保留修复与改造利用,对结构以外的一般个体进行清理拆除;以资源的适应性分布为依据,通过分析各景观单元的资源特色和适宜的转化利用方式,重新组织场地整体景色与功能分区架构(图6)。

图6 途径Ⅱ——布局
5.3 增效:提升特质景观品质,增强景园触媒影响
亟待激活的触媒点应依托场地的单元布景,针对后工业景观自身的特征优势与现状问题,因地制宜、对症下药,既要避免大拆大建,协调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又要弹性、有效、合理地设计构思特征各异的空间及场景。因此,设计者可以利用倾斜摄影技术与信息采集结果,全方位掌握场地的三维空间及其对应的多元数据,继而以遗产价值的传承与转化为目标,从多个方面综合性提升景观品质,进而增强“景园”对周围城市空间的触媒影响(图7)。

图7 途径Ⅲ——增效
1)融绿造境:高生态潜质触媒点的绿色空间转化是对山地城市生态环境的有益补偿。设计需着重识别存在土壤污染、生态脆弱和地质不稳定等情况的单元,并对其实施针对性的污染治理、修复维护与空间管控;合理利用地形条件,将部分工业设施(如工业蓄水池、蒸发井、屋顶平台、水罐等)与场地中的山水景观要素(如错落台地、汇水径流、坑洼等)改造为绿色基础设施;统筹区域中不同坡度、生态梯度等情况下自然演替形成的动植物群落,并将之合理运用于多种类型绿色空间的景园生境营造之中,预留充分的自然恢复空间,以期尽可能顺应自然过程,实现场地的再野化设计;整合场地及场地周边的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景观要素,串联形成结构合理、类型丰富的生态格局,重建场地健康优美的生态环境。
2)意象摹景:后工业景观设计需要尊重原有空间形态与场地肌理,将起伏的地形和山水要素同工业“废墟”进行整体的设计构思,描绘单元景色各异的大地景观,并通过对比衬托、特征凸显等方式强化特色鲜明的工业“大机器”,使地景与设施交相辉映,共同呈现单元景观的场地形象;利用山形-构筑的立面轮廓重塑、远近高低的画面描摹、层次丰富的绿景连接等手法,打造单元及景园内外多样立体的景观界面;运用隐喻象征、形态塑造、环境融入、植被掩映、节点互望等方式,添置极具工业特色与技术美感的公共艺术设施,深入刻画立体地形与工业连廊交错的复式空间,组织虚实结合、高低错落、步移景异的特色景观序列,创意性地设计出自然野性与工业秩序浑然一体的标志、节点和路径等意象要素。
3)文史点题:挖掘各单元景观的时代经历、历史事件,并将之与生产工艺流程相结合,规划文史题材丰富的人文体验路线;充分利用山水寓意、建设布局、厂房结构、老旧材质、典型设备、文化符号、宣传大字、板报涂鸦和残破立面等要素,通过新旧要素在空间中的并置、转置与介置(文化“三置论”方法)[30],锚固历史信息,使之在当前场地上形成新的“复写”;尊重山城原住民及职工的生产生活记忆,将时代精神、生活习俗、企业文化等要素以年代壁画、互动装置、生产生活场景等表现方式融入对应的活动场地之中,以期再现历史情境、增强场所认同、加深寓教于乐的人文体验,从而实现文化内涵的存续与传播。
4)活力焕发:针对场地中诸多的消极空间,对其中无法利用的部分进行绿景重塑,并如俄勒冈城威拉米特瀑布上的造纸厂一般,营造悬空的廊道以连接陡坡、崖壁之上的厂房设施与宏伟的自然风景,构建山地特色步行游憩体系。与此同时,建构筑物及设施可根据自身的现状条件,局部拆墙去顶,化封闭厂房为开放空间,使之紧密连接周边场地与原本消极的空间,共同营造地域化、多样化、可变化的多层立体活动空间体系,为“正式”活动的复合化与“非正式”活动的正当化奠定场地基础。为改善山地城市片区交通状况,应尝试打开厂区部分封闭的边界,拓宽并修补厂区主路,加强内外道路的连接,将部分内部园路融入城市交通,增强园区与周边城市的交通衔接。为重新激活废弃场地,根据组团的功能布局与触媒点的基础定位,可策划特色鲜明的周期性文化艺术及系列主题活动,补足各单元的次级主题功能,为后工业景观注入新的活力,如东郊记忆的多元文艺(音乐、戏剧等)主题、鹅岭二厂的城市“无界创意”主题、北仓文创园的城市“文化图书馆”主题等。同时,可进一步组织与单元空间相协调且符合场地特征与遗产价值的全周期、多样化主题事件与活动,吸引山城居民和外来游客参观游玩,使景园成为老旧城区的新型活力中心。
5)经营策划:为打破仅以建筑空间作为产业发展载体的壁垒,运用“聚”“留”“引”的空间组织方式[31],将产业由建筑空间向山地后工业景观的多样复式空间蔓延,并通过原厂房设施结构的再利用,设计临时性、可移动的建构筑物及城市家具。继而根据转型需要,场地可以运用自身历史文化、景观意象、主题活动等资源优势,生动诠释“工业遗产+”的发展模式,发展适宜的文化产业,开展工业旅游,开发主题式“快闪”商业活动,打造过硬的拳头产品与鲜活的品牌IP;并基于活动与事件的策划,在景园中发展服务、零售、商务、文化和体育等轻量化经济,结合景观空间灵活打造相关的沉浸式系列消费场景与全景式场景体验序列,以期为下岗职工提供再就业机会的同时,发展成为城园呼应的城市新型产业关键点。
5.4 协同:加强地段内外互动,激发群组效应共振
景观触媒效应的有效激发,不仅在于景观自身的成功,亦在于触媒作用向周围城市空间的“传递”[19]。首先,基于国内外长期的实践不难发现,许多优质的城市后工业景观项目在改造利用后可以与临近的空间及界面产生“刺激”作用,如巴塞罗那于1992年因“奥运村”的更新建设,带动了街区立面整治和临近城市空间的功能转型。因此,城市后工业景观可以沿城市道路与山水绿廊将绿色空间向城市延展;通过协调内外空间形象并组织视线互望来借助景园的独特意象提升周边风貌;在邻近空间中添置文化设施并营造多义场所,以此增强人文氛围;无界融合城园空间,使景园更好地带动邻近界面的功能转型;呼应内外服务产业与消费场景,从而达到景观触媒点与城市交织融合、相互“渗透”的目的。
其次,我国早期城市空间中的许多工业遗产呈现出生产-生活服务的空间集聚现象[27],使得在以生产区为核心的一定范围内分布了许多居住、运输、办公和娱乐等服务性设施及场地。以华新水泥博物园为例,在原厂区提质改造过程中,有许多如老码头、引水设施、仓储厂房、职工俱乐部、职工宿舍和红旗桥社区等具备一定价值的建构筑物、工业设施与残余景观散布遗留在周边城市空间之中。它们在博物园吸引力提升后,受更新的“带动”作用,也获得了改造提质的机会,成为增量片区生态节点、增添多样工业特色意象、营造工业历史人文场域、完善服务配套及城市功能,以及发展文旅关联业态(如特色旅宿、文娱、购物、交通、研教等)与链条化产业及产品的重要空间载体。同时,附近许多“失落”的城市开放空间和服务设施等在后工业景观触媒的影响下,可以打造出具有复合功能的各级邻里中心,并与那些残余景观一并成为新的触媒,继而提升区域整体空间品质。
再次,在发展空间有限的山地组团中,城市后工业景观“群组”的多点联动作用格外重要。各触媒点(包含新触媒点)可以综合考虑触媒等级、属性、规模及服务半径等因素,协调发挥“群组”内各个触媒点的特质性触媒效应,通过恢复绿景充足、功能健全的山水生态,凸显各具特色、错落连贯的山城意象,展现氛围浓郁、叙事连续的旧城人文片区,渲染场景营城、功能互补的活力画面,促进片区集群联动、产城相宜的结构升级,进而形成群组内各个触媒点之间的多元效应“共振”。
最后,为彰显群组景观的异质性,促进组团的错位发展,后工业景观组群应突出强化组团的资源特色及整体的触媒优势,调整各组团中景观的整体倾向、复合比重和具体内容,促进后工业群组与城市组团的良性发展,最终实现城市后工业景观“群组”触媒效应的协同作用(图8)。

图8 途径Ⅳ——协同
5.5 连通:编织景观触媒廊道,引发链式连锁反应
沿铁路线及河道滨水区进行空间重建的旧城工业区更新已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开实践,较为典型的有巴黎“小腰带”铁路、巴塞罗那水岸和上海杨浦滨江南段等案例。沿山顺水的诸多城市后工业景观除依托铁路-河道外,亦可以由山水自然走廊串联,其上星罗棋布的铁路站、工厂、社区、桥梁、隧洞、港口、码头等工业遗迹所在场地可以作为景观廊道设计的关键节点,通过与周边山体、密林、台地、径流、水口、岛碛和湿地等自然风景交织,使城市后工业景观从厂区大院向城市带状虚体空间不断延展,形成城市后工业景观廊道。例如黄石主城的工业遗产片区,可以沿“长江-铁路”运输线规划工业景观带,沿“两山一湖”的山体及岸线打造矿冶“废墟”与自然风景相间的城市绿廊,沿城市带状绿地形成连接景观带与绿廊的绿楔。在此基础上,原本布景化、片段化的景观触媒“原点”转变为连续化、整体化的景观触媒廊道,在形成触媒“链式连锁反应”、扩大触媒影响范围与影响力的同时,完善结构,重构健康健全的旧城绿底;连城融景,塑造个性鲜明的城市形象;古今荟萃,展现守正创新的文脉气韵;整合功能,提高适宜情境变化的城市弹性;突出优势,引发全域产业升级发展(图9)。

图9 途径Ⅴ——连通
5.6 调控:引导触媒动态调整,构建多方运营系统
旧城片区中成群的城市后工业景观设计不应是一挥而就地绘制如画的“蓝图”,而是不断动态调整、渐进式引导触媒效应持续发挥的设计过程。这要求规划设计针对不同阶段的发展战略,对各个场地提出阶段性的目标,并以较低廉的成本,较迅速地达到空间的临时性使用目的;结合场地发展规模与触媒正负向效应的反馈,调整触媒的作用方向与强度;根据正向触媒的联动,制定当前旧城片区的阶段性营销策略,以期不断引导城市空间进行功能服务提升和设施配套建设。受山地城市景观的复杂性影响,后工业景观的成果检验与方案调整必须合理借助技术工具,如其动态调控可借助“数字孪生”系统,更快速、准确地分析山地城市后工业景观的现状及问题,更及时、精细地修正和调整鉴识、布景、增效、协同、连通和调控的全实施路径。该系统平台可交由政府部门(如工业遗产中心等)进行对接和维护,通过集中投资、租赁、广告、售卖、设施控制等一站式服务,在加强政府、企业、居民、游客多方参与的基础上,合理调配各方的“权、责、利”划分,以期推进产城融合和发展红利共享,落实城市后工业景观的管理和持续运营(图10)。本研究希望以景观触媒的理论方法,利用山地城市后工业景观的更新活化,更科学、有效地推动城市沿着生态功能健全、山城形象凸显、文化氛围浓厚、功能活力焕发和文旅业态兴旺的方向持续更新。

图10 途径Ⅵ——调控
注:文中图片均由作者绘制。
注释:
①202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愿景目标建议》首次提出“需进一步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统筹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动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和品质提升”。
②20 世纪50 年代,西方发达国家针对“解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和城市中心衰退问题,开始城市更新的实践;2020年“十四五”规划纲要中针对城市更新行动,提出“改造提升老旧小区、老旧厂区、老旧街区和城中村等存量片区功能”的要求。
③“完整性”(integrity)与“原真性”(authenticity)是世界文化遗产领域的核心原则,均在《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中得以体现。本文工业遗产的“原真性”指遗产形态、设计、材质、位置、环境等的“真实”状态;“完整性”指遗产区域历史层积、生产工艺、生态系统等的“完整”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