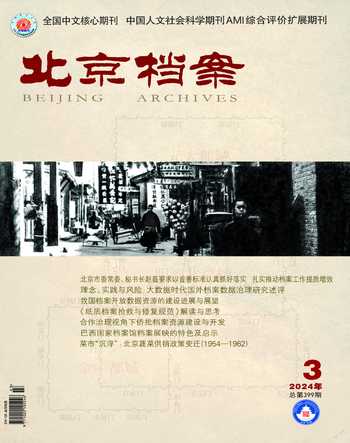基于短视频媒介的数字档案资源开发:动因、关联与取向
王喜凤 李佳男
摘要:短视频媒介的出场进一步改变了信息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从短视频媒介的视角思考如何进行数字档案资源开发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论文从政策支持、技术赋能、理念转向方面分析了基于短视频媒介的数字档案开发的动因;从主体、资源、受众视角阐述了短视频媒介与数字档案资源开发的内在关联;从重视现存资源的叙事开发、加强对现有成果的二次开发、探索线上线下的联动开发角度论述了基于短视频媒介的数字档案资源开发取向。
关键词:短视频媒介 文化传播 数字档案资源 档案资源开发
媒介革命改变了信息生产与传播的全过程,现今移动短视频崛起的背后,同样也蕴含着深刻的价值理念,“短视频的兴起不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必然结果,也并不仅仅指代一种新的传播形态的诞生,或者一种可视化共享交往行为的出现,而应该把它掀起的后媒体浪潮看成是一个新的信息时代——轻传播纪元来临的标志”[1]。这一改变势必会影响信息生产与传播的链条。基于此,数字档案资源的开发与传播则需要充分结合这一变化进行探索和思考。
一部分档案机构已经注意到短视频对档案传播的重要价值。据统计,目前经过认证的档案局(馆)官方抖音号共47个。但这些档案局(馆)类抖音号普遍存在“内容缺乏规划、互动不足、影响力有限等问题”[2]。这说明仅仅开通和入驻平台意义不大,应着力从短视频媒介的思维角度创新数字档案资源开发方式,拓展档案资源传播路径,扩大档案文化影響力,提升社会整体档案意识。
一、基于短视频媒介的数字档案资源开发的动因分析
短视频已成为当前媒体传播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档案资源开发与短视频媒介的结合是政策支持、技术赋能、理念转向推动下的必然趋势。
(一)政策支持
2020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国家鼓励档案馆开发利用馆藏档案,通过开展专题展览、公益讲座、媒体宣传等活动,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档案部门应主动从多途径、多维度、多层次开展数字档案资源开发利用和传播。现今许多政务主流媒体十分注重使用微博、微信、短视频等新兴媒体形态,《人民日报》构建了“两微两端”全媒体传播矩阵,“央视新闻”“平安北京”等账号在新媒体平台的影响力也日益彰显。《“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指出“通过展览陈列、新媒体传播、编研出版、影视制作、公益讲座等方式,不断推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档案文化精品”“推进数字化、网络化宣介展示”[3],档案部门应因时而动,思考数字档案资源开发利用如何适应新兴媒体的内容生产和传播特点,利用短视频这类新兴媒体传播好数字档案资源中蕴藏的优秀文化。
(二)技术赋能
以往数字档案资源开发模式往往依托传统媒介展开,思维受到一定的局限,传播效果有限,开发效能较低。现今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和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丰富了档案资源开发的视角。AI技术为我们开发视频类档案资源提高了效率、丰富了内容、创新了形式,如央视新闻推出的大型融媒体AI修复节目《彩绘中国·觉醒》,首次使用4K+ AI上色修复了“五四运动”现场画面,成果以短视频形式在微博、抖音播出,让百年前的“五四运动”视频档案以一种崭新的方式生动地再现。近些年,在语义层面实现档案馆藏的整合和互操作慢慢成为研究热点。多媒体资源语义互操作带来的不仅仅是检索上的便利,多媒体档案信息内容的提取与分析描述、不同媒体类型档案信息之间的语义关联设计等技术更为数字档案资源跨媒体开发和集成知识服务创造了良好的条件。[4]新兴技术使高效开发数字档案资源成为可能,高效的内容生产借助短视频传播能使数字档案资源传播效能实现质的提升。
(三)理念转向
“我们进入了媒体‘宰制时代”,“视觉优先”理念推进“视觉革命”,现代传媒发展推动人类从“读”时代进入“看”时代,[5]人类愈加注重视听感官的满足,“视觉文化”成为主流,许多学者也在积极倡导数字档案资源的“可视化”叙事服务。有学者把短视频媒体的崛起看作一个新的传播时代来临的标志,进入了以时长短、视角小、内容薄、轻松化、碎片化为话语表征的“轻传播”历史阶段。[6]学者将“轻量化传播”引入档案学研究,认为档案信息轻量化传播方式愈来愈能适应社会需求,满足受众审美需求的同时,多元化、多角度、多层次地传播档案信息。[7]“移动短视频作为媒介技术与视觉文化联姻的最新形态,具有典型的视觉中心主义特征”[8],自然也成为现今“视觉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数字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短视频的结合则是在“视觉文化”和“轻传播”理念转向下的应然态势。
二、短视频媒介与数字档案资源开发的内在关联
短视频媒介与数字档案资源开发的内在关联表现在,档案馆的文化传播需求与短视频媒介强大的传播能力相契合;数字档案资源的数字叙事需求与短视频现代传媒特征相契合;数字档案资源开发的受众需求与短视频便捷的传播路径相契合。
(一)主体:文化传播需求与强大传播能力契合
档案具有文化功能,档案馆需要积极履行文化职能,积极开展档案文化服务,做好档案文化传播。但当前档案馆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存在资源缺位问题,接受公共文化服务的用户数量偏低,亟须丰富档案公共文化服务形式,拓展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的受众。[9]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网络视频用户规模为10.44亿,占网民整体的96.8%;短视频用户规模为10.26亿,占网民整体的95.2%”[10]。可见,短视频媒介对于文化传播的贡献日益凸显,其传播能力与文化传播需求相契合。档案馆可以借助短视频媒介强大的传播能力,开发与新传播形态相适应的档案文化精品,大力促进档案文化传播。
(二)资源:数字叙事需求与现代传媒特征契合
档案叙事的记录媒介从档案文本到档案影像再到数字档案,在数字时代出现了“口语文化的回归、读写文化的延续与视觉文化的强化的情境”。多种媒介文化交融汇聚,但“视觉文化仍是数字档案时代最为突出的文化倾向”[11]。冯惠玲在研究中总结了传统叙事到数字叙事的转变,认为“数字叙事多层、多维、多媒介、网状、开放等特点赋予叙事很多新的可能”[12]。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兴的现代传媒具有鲜明的视觉文化的气质与特征,也逐渐成为媒体融合布局中的重要部分。数字叙事转变下的档案叙事需求与短视频媒介的现代传媒特征相契合,两者结合可以丰富档案叙事内容,全方位、多维度、立体化地传播档案文化。
(三)用户:利用主体需求与便捷传播路径契合
移动互联网的产生与发展,影响并塑造着用户的阅读习惯。档案移动服务主要通过手机短信、网站、移动APP等开展,国家档案局于2019年发布《档案移动服务平台建设指南》指导档案部门开展档案移动服务,但当前档案移动服务仍旧存在不足,对用户的需求关注不够,应及时为用户提供与其利用需求相匹配的档案服务。[13]如今像短视频之类的碎片化资讯获取方式和社交方式越来越受到人们欢迎,各大短视频平台也在近几年的发展中积累了大量的用户。短视频媒介所具有的便捷的传播路径与数字档案资源利用需求相契合,因此,档案馆作为移动服务主体应改变服务方式和策略,充分考虑档案移动服务用户的需求,利用短视频媒介促进档案文化传播。
三、基于短视频媒介的数字档案资源开发取向
基于短视频媒介的数字档案资源开发,需要重视现存资源的叙事开发、加强对现有成果的二次开发以及探索线上线下的联动开发。
(一)重视现存资源的叙事开发
冯惠玲论述数字记忆的叙事时,提出了“故事数据化”和“数据故事化”两方面内容,主张一方面将用于叙事的多媒体记忆资源进行结构化处理,包括元数据著录、建立数据关联等,从而实现网状关联和智能检索,使其价值得以提升和活化;另一方面将数据还原或关联至特定场景,并以叙述方式呈现。[14]
基于短视频媒介的现存数字档案资源叙事开发,与许多学者论述的过程并无二致,只是需要针对短视频媒介时长短、视角小、内容薄、轻松化、碎片化的特点,进行特色化的叙事开发。例如,国家档案局在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媒体中心合作,隆重推出了百集微纪录片《红色档案——走进中央档案馆》,精选中央档案馆大量馆藏珍贵档案,生动讲述档案背后的人物和故事。每个视频长度基本在七分半左右,涉及“领袖的致敬”“革命的爱情”等视角,在国家档案局微信公众号以及央视新闻抖音号上同步播出,效果不同凡响。
(二)加强对现有成果的二次开发
传统的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模式中已积累大量编研成果,有文字、图片和视频等,民间也有大量珍贵档案资源有待进一步挖掘。基于短视频媒介的数字档案资源开发,要充分利用好现有编研成果,加强对现有成果的二次开发。
一是长视频的精简化开发。传统的档案纪录片往往篇幅较长,很难吸引观众,所以可将一些长篇的档案纪录片精简化,制作成类似于纪录片解说形式的档案短视频,投放在短视频媒介平台上。部分用户在看到短视频后,会对其背后的“长视频”产生兴趣,此时可以引导用户关注更多档案开发成果。
二是短视频的整合化开发。整合或征集社会大众感兴趣的档案短视频资源,将其按主题、人物等分类方法整合,形成系列档案短视频合集。例如,由国家档案局与多个单位共同指导,环球网、中国网信网、中华英烈网和相关地方网信办主办,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快手、B站等单位协办的第二届“追寻先烈足迹”短视频征集展示活动,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主题,面向檔案馆、革命博物馆、纪念馆、革命旧址等场馆,各地重点新闻网站和主要短视频平台,以及广大网民广泛征集短视频作品。此类活动活化了红色档案资源,形成了品牌,具有很好的教育意义和示范意义。
三是文字编研成果的可视化开发。传统的档案信息资源从叙事视角已经形成了大量的“档案故事”,可在其基础之上进行可视化的二次开发。例如,中国档案资讯网“档案文化”专栏下设“红色记忆”“人物纵横”“珍档秘闻”等栏目,可以在这些现有资源成果基础上将其可视化开发为档案短视频,积极推动数字档案资源服务向可视化叙事方向发展。
(三)探索线上线下的联动开发
传统档案开发成果的重要展现形式之一是举办专题展览,根据调研,[15]2018—2020年,全国各级综合档案馆举办档案展览3155、2841、2618个,分别接待486.0万、788.2万、501.9万人次参观展览。平均每个综合档案馆每年所举办的档案展览分别只有1.03个、0.85个、0.78个。实际到馆接受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的用户数量偏低,需借助其他载体和形式扩大档案文化传播效应。
对于基于短视频媒介的数字档案资源开发,可以探索线上线下的联动开发模式,在线上引导用户参观线下展览,在线下积累用户关注线上平台。档案馆的线上短视频平台可以实时发布线下展览等活动的相关内容前瞻,包括馆内值得用户欣赏的馆藏珍品或开发成果;线下展览也可以利用开发好的档案短视频资源及其合集举办专题展览,丰富档案展览的内涵和形式。
线上线下的联动开发可以促进档案馆成为地方文旅融合的重要支点。各地档案馆蕴藏着不同特色的档案资源,例如长三角地区拥有“党的诞生地”“红船精神”等多个与众不同的红色文化品牌和丰富的红色档案资源,整合利用这些红色档案资源进行短视频形式的开发并通过短视频媒介发布,可以拓宽红色文化品牌营销渠道,[16]在线上实现观众的引流,让线上“观众”变为线下“游客”,在线上线下的联动中推动地方文旅融合的发展。
四、结语
“必须视档案为主动的而非被动的,必须视档案馆为权力的场所而非权力的记录者。档案不仅仅记录文化行为,也从事文化行为。”[17]面对短视频媒介对文化传播领域造成的冲击,档案部门需要更加主动地融入新的媒介传播格局,积极“从事文化行为”,深入挖掘档案价值,探索基于短视频媒介的数字档案资源开发新模式,丰富档案记忆展演形式,传播优秀档案文化,提高社会档案意识。
注释及参考文献:
[1][6]林克勤.轻传播:短视频引领的后媒体浪潮[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10):12-18.
[2]彭忱.档案部门短视频运营现状与对策研究[J].北京档案,2022(10):39-40;42.
[3]中办国办印发《“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J].中国档案,2021(6):18-23.
[4]吕元智.面向资源架构的数字档案资源跨媒体整合研究[J].档案学研究,2016(4):91-96.
[5]丁华东.档案与社会记忆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8-29,312-314.
[7]邢变变,党少彬.档案信息轻量化传播的应然态势及实现路径[J].档案学通讯,2020(4):65-70.
[8]林峰.移动短视频:视觉文化表征、意识形态图式与未来发展图景[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6):144-149.
[9]周林兴.论档案馆的文化治理研究[J].档案学研究,2020(1):73-78.
[10]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J].国家图书馆学刊,2023(5):13.
[11]杨光,奕窕.记录媒介演进与档案历史叙事的变迁[J].档案学通讯,2019(4):19-27.
[12][14]冯惠玲.数字人文视角下的数字记忆——兼议数字记忆的方法特点[J].数字人文研究,2021(1):87-95.
[13]吕元智.基于场景的个性化档案移动服务模式探究[J].档案学通讯,2019(5):43-49.
[15]此部分数据来自国家档案局2018—2020年公布的全国档案主管部门和档案馆基本情况摘要(https://www.saac.gov.cn/daj/zhdt/lmlist.shtml)。
[16]党宁,楼瑾瑾,许鑫.颂红色华章:文旅融合对上海红色文化品牌的提升[J].图书馆论坛,2020(10):14-23.
[17]库克,李音.铭记未来——档案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作用[J].档案学通讯,2002(2):74-78.
作者单位:1.洛阳理工学院档案馆 2.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