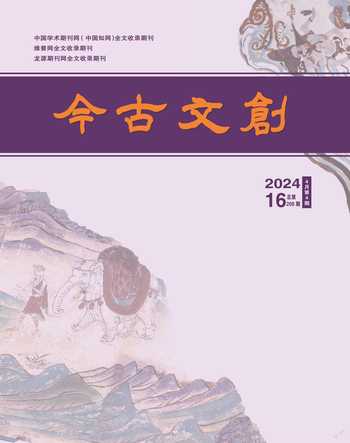“志道据德, 依仁游艺”:钱穆《论语新解》对孔子进学梯径与修养境界的新阐释
李珊
【摘要】作为儒家学派创始人的孔子,不仅是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还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孔门弟子中贤人众多,人才济济,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孔子提出的进学梯径和修养境界有着密切的关系。钱穆在其《论语新解》中,与理学家的解释相反,他认为孔子的进学梯径是“游艺”→“依仁”→“据德”→“志道”。同时,他还将孔子进学的四个阶段与孔子自身所谈到的修养境界进行了对比性阐释,深化和拓展了孔子的教育理念。这种解释不仅契合孔子通过人事达于天道,最终实现“天人合一”境界的思想旨趣,还深刻体现了儒家“下学而上达”“内在而超越”的人文精神。
【关键词】孔子;钱穆;《论语新解》;进学梯径;修养境界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16-0076-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16.023
孔子生前即被视为“天纵之圣”[1]2490,去世后被历代帝王不断地追封谥号,明世宗尊其为“至圣先师”。作为一名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在《论语·述而》篇谈到了他的成学理念:“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1]2481与理学家所解释的进学顺序相反,钱穆主张孔子的进学路径是沿着反方向展开的,即“游艺”→“依仁”→“据德”→“志道”。钱穆还将这四个阶段与孔子在《论语·为政》篇谈到个人的修养境界,即“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1]2461存在着密切的对应关系。本文以钱穆《论语新解》中对孔子进学梯径和修养境界的对比性阐发为基础,尝试揭橥孔子的修身理念,探讨其成学之方与教育理念。
一、“游于艺”与“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
(一)“游于艺”是进学之基
钱穆首先将“游”解释为“游泳”,“艺”解释为“六艺”,并认为“艺”是“人生所需”,突出了其在成学之路的重要性。然后用“人之习于艺,如鱼在水”的形容来描述在学习中一种悠然舒适的心理状态,这与朱熹解释的“涵泳从容,忽不自知其入于圣贤之域”[2]的意思相似,都强调快乐学习的态度和方式。最后阐释了“游艺”的意义,“不仅可以成才,亦所以进德”,将外在的学习与内心的情感愉悦联系在一起,内外贯通之后,就能达到“自强不息欲罢不能之境,夫然后学之与道与我,浑然而为一”[3]144。
钱穆认为进学梯径应该首先“游于艺”,而非“志于道”,“苟单一先提志道大题目,使学者失其依据,无所游泳,亦其病”[3]158,所以必须先学习基本的知识和技能奠定基础。子夏也说:“君子学以致其道”[1]2531,“学”是基础,“道”是目的,通过学习来达到“道”。据此,钱穆解释为“非学无以明道,亦无以尽道之蕴而通其变化。学者侈言道而疏于学,则道不自至,又何从明而尽之?”[3]153由此可知,朱熹所将“游于艺”排在末位的次序显然是不合理的。
钱穆还将《中庸》蕴含的儒学修身思想融入了对孔子进学梯径的解释之中。如根据《中庸》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1]1625的修身理念,钱穆提出了“性即是一自然,一切道从性而生”[4],他认为性是道的来源,所以进学梯径也应该从养护本性为起点。虽然人的性情天生相近,却能通过后天的教育产生差异,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1]2524。钱穆从而提出“性情”的涵养离不开于“六艺”的教化。例如诗教能修身养性,“诗本性情,其言易知,吟咏之间抑扬反复,感人易入。故学者之能起发其心志而不能自已者,每于诗得之。”[3]194这就是说,“游艺”不仅是涵养性情的方法和手段,也是进学的基础。
(二)“游于艺”与“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的关系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据此,钱穆将孔子的进学之路分为五个阶段,对应“游艺”“依仁”“据德”和“志道”的进学梯径,如他说:“此章乃孔子自述其一生学之所至,其与年俱进之阶程有如此。学者固当循此努力,日就月将,以希优入于圣域。”[3]26
“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是孔子进学的第一阶段,对应“游于艺”。“十有五而志于学”,是通过学习“六艺”和其他知识技能来涵养性情,促进内在修养,比如钱穆说:“樂者……可以养人之性情,而荡涤其邪秽,消融其渣滓学者之所以至于义精仁熟而和顺于道德者,每于乐得之。”[3]194“三十而立”是在前面“志于学”的基础上,已经学“礼”有所成,因为孔子言“不学礼,无以立”[1]1522,钱穆解释说“学者之能卓然自立,不为事物所摇夺者,每于礼得之”[3]194。同时,钱穆又在此基础上,对“礼”的内涵做了进一步的扩充,指出“礼之本即仁”[3]49,而且“仁”与“礼”不可分离,两者是“相反相成”的关系,学“礼”的根本在于求“仁”。钱穆认为这一阶段是处于“游于艺”的基础上,继而追求“仁”的进路。
二、“依于仁”与“四十而不惑”
(一)“依于仁”是进学之本
钱穆将“依”解释为“不违”,“仁”解释为“人与人相处之道”。朱熹认为“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2]50这种解释将“仁”视为一种天理本体,使其具有了形而上的超越性内涵,赋予了其在儒家道统之学的核心地位。但钱穆将“仁”阐释为人最真挚朴实的感情,重新构建成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道德准则,消解了“仁”的形而上学的意义,具体解释为“仁道”和“仁心”,并且提出了“人道必本于人心”的新创见。由此,钱穆用“心”作为连接“道”与“性”之间的关键,如他说“孔门论学,主要在人心,归本于人之性情。”[3]22如此一来,就突出了“心”的核心地位。
钱穆认为“仁”不仅是进学的根本,还是“人生一切可久可大之道之所本”。他在《里仁》篇解释说:“桃杏之核亦称仁,桃杏皆从此核生长,一切人事可久可大者,皆从此心生长,故此心亦称仁。若失去此心,将如失去生命之根核。”[3]77在钱穆看来,“仁”如同果实的种子是一切人事的根本,“仁心”是道德情感和行为的本源。正如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1]2466钱穆解释为“仁乃人与人间之真情厚意。由此而求表达,于是有礼乐。若人心中无此一番真情厚意,则礼乐无可用。”[3]48如果没有“仁”,那么礼乐都将失去了意义;如果不能做到“依于仁”,那么基础阶段的“游艺”也只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二)“依于仁”与“四十而不惑”的关系
“四十而不惑”是孔子进学的第二阶段,对应“依于仁”。钱穆解释在此阶段“必能对外界一切言论事变,明到深处,究竟处,与其相互会通处,而皆无可疑,则不仅有立有守,又能知之明而居之安”[3]24,此为“不惑”。子曰:“知者不惑。”[1]2491智者不为外物所惑,心中亦无迷乱,可谓“知之明”。钱穆对“仁者安仁,知者利仁”[1]2471解释说“利仁者,心知仁之为利思欲有之”[3]77,智者知道“仁”有利才行仁,但“仁者安居仁道”不具有功利性,显然境界更优。孟子说“仁,人之安宅也”[1]2721,钱穆同样以“长居久安之家”的形容来比喻“仁”,“心安于仁”则“自然安适”,可谓“居之安”。可知此阶段孔子已经在“三十而立”学礼有成,“有立有守”的基础上,从“知”转向“仁”的路径,此心已经安于“仁”,达到了“依于仁”的境界。
三、“据于德”与“五十而知天命”
(一)“据于德”是进学之重
钱穆将“据”的含义解释为“固执坚守”,对于“德”,他主要从发源和性质两方面进行了具体阐发。从发源的方面来讲,钱穆认为“一切行为发源于己之性,归宿到自己心上,便完成为己之德。故中国人又常称‘德性”;从性质的方面来讲,钱穆言“德者,心之最真实,最可凭,而又不可掩。故虽蕴于一心,而实为一切人事之枢机。”[3]20由此可见,钱穆对“德”的阐发处处以“心”为重要的基点,还将其与“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中的“性”“道”的概念连接起来,使之成了一个前后连贯的逻辑整体。对其与“性”和“道”的关系,钱穆分析说:“道行而成,形于外,回到人心,则谓之德。德是行道而有得于己之謂,故可合称‘道德。天赋称性,由性发为行为,由行而有得于己谓之德。故可合称‘德性。”[4]165“据于德”是进学的重点。“德”在进学中占据着关键的位置,如钱穆所说“弟子为学,当重德行。若一意于书籍文字,则有文灭其质之弊。”[3]8
(二)“据于德”与“五十而知天命”的关系
“五十而知天命”是孔子进学的第三阶段,对应“据于德”。钱穆追溯到与人相关的主体上,强调个体的责任,将这里的“天命”解释为“人生一切当然之道义与职责”,并将常人难以“守道尽职”原因归于“其义难知”。孔子在此阶段已经知晓了常人所不能知晓的“天命”,“至于不惑之极,自信极真极坚”[3]24,如孔子说过“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1]2721钱穆认为“命”具有可知性,又与“仁道本于仁心”相结合,构建出了行道的方法,“命,在外所不可知,在我所必当然。命原于天,仁本于心。人能知命依仁,则群道自无不利。”[3]206孔子在此阶段已经在“知命依仁”的基础上,知晓了上天赋予自己的“道义职责”之后,主动去担当应有的职责,提高自己的德性。可知此阶段是修德的步骤,即“据于德”。
四、“志于道”与“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
不逾矩”
(一)“志于道”是进学之极
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成学理念中,“道”是人终其一生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和道德准则,在四者中处于最重要的位置,也是孔门进学的最高级别。钱穆指出了“志”与“学”的相承关系,强调了“学”的重要性,解释为“志者,心所欲往,一心常在此目辩上而向之趋赴之谓。故有志必有学,志学相因而起。”[3]23“道”,是具有超越性的形而上的终极理想,也是儒家先贤穷其一生追求的目标,具体分为“天道”和“人道”。但是“天道”与“人道”不是分离割裂的,《中庸》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钱穆言:“人性赋于天,由此而行之之谓道。故人道亦即是天道。若违逆于人性,则决然不是道。”[5]所以人道与天道是内在一致的。
(二)“志于道”与“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关系
“六十而耳顺”是孔子进学的第四阶段。“耳顺者,一切听入于耳,不复感其于我有不顺,于道有所不顺。”[3]25孔子在此阶段,一切听到的都能够明白贯通,不会再感到违逆“心”和“道”。“明其所以然则耳顺,一切不惑其有所违逆,于是而可以施教,可以为治,可以立己而立人,达己而达人”[3]25,这说明已经做到了“忠恕之道”,也就是“仁道”。钱穆言:“然则天命之终极,岂非仍是此道之大行?”这里的“道”是“仁道”,也是“人道”,于是钱穆继续解释“故人道之端,要在能反求诸己。忠恕之极,即是明诚之极,天人一贯,而弘道则在己。”[3]25与《中庸》的“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1]1632不谋而合。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是最高的阶段。钱穆指出“学问至此境界,即己心,即道义,内外合一。我之所为,莫非天命之极则矣。”[3]25天固有的“仁心”与后天修养的“德行”打通后,通达“人道”与“天道”之后,学问将臻于化境,实现了“理智与情感合一,道德与艺术合一,人生与文学合一。”[3]68所以钱穆评价孔子为“圣人之学,到此境界,斯其人格之崇高伟大拟于天,而其学亦无可再进矣。”[3]25孔子在此阶段已经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即他所说的“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1]2513
五、结语
综而论之,钱穆认为“游于艺”“依于仁”“据于德”和“志于道”四者依次递进,构成了孔子完整的进学梯径。在成学的四步驟中,“艺”即是“六艺”的知识和技能,“游艺”就是以“诗书礼乐”的教化功能来陶冶性情,是进学的基础;“仁”不仅是先天所具有的德性,还是所有道德规范的总纲,而“依仁”就是在陶冶性情的基础上正心诚意,是进学的根本;“德”是后天的言行修养之所得,也是“道”的具体体现,而“据德”就是在正心的基础上践履道德规范有所得,是进学的重点;“道”是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终极理想和最高目标,“志道”是通过对仁和德的践履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是进学的最终鹄的。
由此,钱穆通过其在《论语新解》中对孔子进学之路独具特色的阐发,提出了“游艺”“依仁”“据德”和“志道”的进学次序,实现了个人进学梯径的层层递进与贯通。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钱穆还将孔子的成学四步骤与孔子谈到的人格修养境界,即“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做了详细的对照性阐发。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就是以知识为基础涵养性情的阶段,即“游艺”,此时学礼已有所成,开始通过“克己复礼”的方式去追求“仁”。“四十而不惑”,正是孔子从知者的“知之明”转为仁者的“居之安”,从上一阶段的追求“仁”已经切实达到了“依仁”。“五十而知天命”,说明孔子已经从“知命依仁”进入担当“道义职责”的地步,提高对德目的追求,此阶段进入了“据德”。“六十而耳顺”是孔子“明道而行道”,“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则是孔子“下学而上达”,最终实现了“天人合一”的修养境界,即“志道”。
钱穆在其《论语新解》中对孔子进学梯径和修养境界的对照性阐发,不仅契合孔子通过人事达于天道,最终实现“天人合一”境界的思想旨趣,还深刻体现了儒家“下学而上达”“内在而超越”的人文精神。这种新的阐发,不仅为当代有识之士实现德性化育指明了方向,而且为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循序渐进的有效路径,进而有利于当代社会教育理念的改革、创新与发展。
参考文献:
[1](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625-2721.
[2](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50-91.
[3]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3-388.
[4]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中华文化十二讲[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18-165.
[5]钱穆.中国文化丛谈[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101.